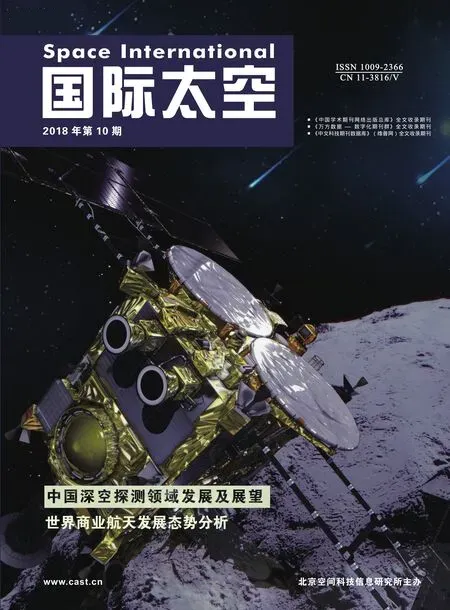外空資源所有權法律問題探析
湯耀琪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
伴隨著外空領域的科技革新,不乏資本雄厚、技術發達的國外私人實體將其商業發展戰略瞄準外空資源的開發、利用領域。科技之革新必然伴隨法律之革新,美國、盧森堡為保障其國內私人實體在外空領域獲取的自然資源,隨之出臺了涉及“外空資源所有權歸屬”的法律,進一步將關于外空資源所有權的法律問題推向了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基于此,針對外空資源所有權問題進行全方位的法律解析,并提出立足于國情的法律建議,對我國航天事業的穩健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 美國、盧森堡立法概況
美國一些資本雄厚的商業公司,如行星資源(Planetary Resources)、深空工業(Deep Space Industry)、月球快車(Moon Express)等公司制定了針對外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計劃,以進一步占有外空資源。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盧森堡以國家立法的形式賦予其私人實體在外空領域取得的自然資源以所有權,給予其“權屬的法律確定力”。2015年11月2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外空商業發射競爭法》(公法:114-90),第四部分即是《2015外空資源開發和利用法》。該法案的第三個條款(Sec.51303:“小行星資源和外空資源的權利”)賦予了“美國公民”對其所開采的外空資源包括所有權在內的占有、運輸、使用和出售等各項權利,為私人實體進行外空天體采礦提供了法律支持。與美國相似,盧森堡國會于2017年7月13日通過了專門的《探索與利用空間資源法》,該法案第一條即確立“外空資源可以據為己有”。美國、盧森堡兩國的做法引發了國際社會關于外空資源所有權的熱烈討論,兩國行為亦遭到來自國際社會的質疑與非議。
2 適用原則與立法效力問題
“不得據為己有”原則的適用范圍
依據素有“外空憲法”之稱的1967年《外空條約》第2條規定:“外層空間,包括月球與其他天體在內,不得由國家以主權主張或以使用或占領之方法,或以任何其他方法據為己有。”該條即“不得據為己有”原則的由來。依據該項原則,國家不得依據主權以任何形式對外層空間主張所有權。其所禁止的主體是國家,并沒有禁止自然人、法人等私人實體“據為己有”。所禁止的對象是“外層空間,包括月球與其他天體”,并未明確規定至“外空資源”。而美國《2015年外空資源探索和利用法》規定:“本章中參與小行星資源或外空資源商業獲取的美國公民,根據可適用的法律,包括美國的國際義務,對所獲得的任何小行星資源或外空資源享有權利,包括占有、擁有、運輸、使用和出售小行星資源或外空資源。”其賦予外空資源排他性所有權的主體是美國公民,對象是外空資源。由于“不得據為己有”原則的適用主體和適用對象仍存在爭議,因而很難得出美國、盧森堡賦予其私人實體主張外空自然資源所有權的立法行為違反了國際法的結論。
與“允許因科研目的占有外空資源”的理論歧義
1967年《外空條約》第二條與1979年《月球協定》確立的允許因科研目的占有外空資源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理論歧義。《月球協定》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締約各國為促進本協定各項規定的實施而進行科學研究時,應有權在月球上采集并移走礦物和其他物質的標本。發動采集此類標本的締約各國可保留其處置權,并可為科學目的而使用這些標本。”依據該項條款,當國家在外空進行諸如勘探、開發外空資源的科學活動時,國家可保留并處置其采集的外空資源。這種保留并處置外空資源的權利與《外空條約》規定的“不得據為己有”實則是相違背的。1969年美國“阿波羅”飛船登月,當時科考小隊從月球上帶回了一些礦石等資源,美國法律明確規定“阿波羅”任務取回樣品的屬性是財產。現今的外空資源開發、利用諸多是以科考、調研的名義進行的,那么若是一切對外空資源的占有活動被定性為“科學目的”即可被認定為合法,那么未來勢必引發名義上是“為人類利益的科學研究活動”,實為航天大國之間對外空資源的“掠奪戰”。
“為全人類謀福利”原則的適用問題
《外空條約》第一條規定:“探測及使用外空,包括月球與其他天體,應為所有各國之福利及利益而為之,不論其經濟或科學發展程度如何,并應為屬于全體人類之事。”該項條款給予所有探索、利用外空資源的活動一項先決性、限制性條件,即外空自然資源的開采是為了所有國家的利益而開展的,同時所有國家皆應從這些活動中獲益,即“為全人類謀福利”原則。然而,現行國際空間法律制度并沒有確立與該原則相對應的具體制度,從而該條所設立的限制實際上是一項道義上的限制。“為全人類謀福利”原則與《外空條約》中的其他原則相比,約束力較弱,更像是一種愿景的表述,其宣示的意義大于其實際的約束力。因此,很難說美國、盧森堡的立法行為違反了“為全人類謀福利”原則。
“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的適用問題
《月球協定》第十一條規定:“月球及其自然資源均為全體人類的共同財產。”國際海洋法領域中亦有類似的“人類共同繼承財產”概念。關于“人類共同繼承財產”是否構成國際習慣而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問題,筆者持否定態度。國際習慣的構成需要具備兩個因素:心理因素與實踐因素,即法律確信與通例。以美國為代表的航天大國并不主張外空資源是“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目前僅17個《月球協定》的締約國承認并接受該原則,這就表明,此概念并沒有在外空領域得到國際社會的確認,因此法律確信這一條件并不具備。至于通例因素,無論是在聯合國大會第2749號決議通過之后,還是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之后,國際社會均未能夠就實施“人類共同繼承財產”法律制度形成反復多次、前后一致的實踐,從而該原則并不具備通例要素。因此,此概念不構成國際習慣,因而并不適用于國際空間法領域。
國內立法的效力問題
關于一國以國內立法的方式確立外層空間資源的所有權歸屬是否有效的問題:首先,財產確權屬于私法上的概念,而不是國際法的概念。所以一國政府有權規定外空資源的歸屬,因為這是國家立法主權的體現。問題的關鍵是立法行為本身是否符合其國際義務。其實,國內法的效力問題與本文所探討的美國、盧森堡的相關立法是否違反國際法,實則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依據前文所述,美國立法規定私人實體對外空資源主張排他性所有權并不違反1967年《外空條約》的“不得據為己有”原則,因而其并未違反國際義務。國家有權通過國內立法為國內私人實體確定外空資源的排他性所有權,但是國際層面對該國內立法的效力并不一定會給予認可,除非國家間互相認可、贊同。
3 完善外空資源所有權法律制度的建議
我國應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出發制作航天發展戰略規劃,國際層面當致力于推動國際組織協同各國彌補原有國際條約的不足,同時引導建立多邊合作的外空資源開發、利用國際機制,國內層面應積極引導、修正、完善國內立法,為我國對外空資源的探索、利用活動提供法律支持。
明確“不得據為己有原則”的內涵
我國對外空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同于美國以私人實體為主導地位推動外空資源的商業開發,我國絕大多數面向外空領域的勘探、開發活動都是由國家主導的。各國對外空資源的占有畢竟是有限的,先來者必定會限制后來者(技術不成熟的一方)的參與,后來者則應盡量延緩和限制先來者的開發活動。倘若一味地肯定一國可以通過國內法規定外空資源的權利歸屬,肯定披以“外空科考、調研”外衣的外空資源開采活動均為合法,則勢必造成不可遏制的針對外空資源占有的“競賽”。
與此同時,眼下我國應順應外空資源勘探、開發的國際趨勢,擺出積極的應對姿態,致力于推動國際組織協同各國彌補原有國際條約的不足。“不得據為己有”原則的適用仍存爭議,我國作為負責任的航天大國,應主動扛起制度革新的旗幟,積極推動條約的補正。筆者認為,可依據《外空條約》第六條:“非政府實體與政府機構的活動均等同視作國家活動,并由締約國承擔國家責任”,將禁止的主體從國家延伸至非政府實體(私人實體)。同時,禁止對象中的“外空天體”應當擴大解釋為包含“外空天體”中蘊含的“外層空間資源”,使得《外空條約》 得以發揮其真正效用。同時,針對《月球協定》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允許以科研目的占有外空資源”的規則予以進一步的完善和細化。
堅守“國家自由探測外空”規則
如若過分強調外空資源的共有屬性,必然打消國家及私人實體對外層空間采取進一步探索、利用、開發的積極性,甚至影響到人類進一步邁向外空的發展進程。美國、盧森堡的立法形式雖然很可能造成具有超強航天實力的少數私人實體攫取了本應用于“為全人類謀福利”的巨大外空自然資源的這種少數人壟斷多數資源的現象,但是如若缺乏法律的確定性保障,面對需要大量資金、技術支持的外空采礦活動,即便是有國家力量的支撐,私人實體也未必能得到有效健全的發展。
我國應堅守《月球協定》確立的關于“國家自由探測外空”規則,結合《月球協定》第十一條第五款的規定:“待到對外空資源的開發、利用切實可行時,國際社會即應當建立相應的國際制度對此進行指引。”支持、引導建立起自由但存在限度的外空資源探索、開發機制。縱觀人類目前對于外空資源的開發、利用,主要由美國、俄羅斯、中國等科研儲備實力較大的航天大國進行的,大多數國家仍未積累其相應的科研實力進行外層空間領域的資源開發活動,目前將利益的天平適當偏向于正在進行外空資源開發的,并為其投入較多人力、物力資源的技術發達國家,以此平衡國家、私人實體與國際社會的利益是符合實質正義要求的,也是符合我國航天利益需求的。
構建外空資源管理國際制度
我國在致力于推動國際組織彌補原有國際條約的不足的同時,更應引導建立多邊合作的外空資源開發、利用國際機制。
針對國際外空資源管理機構的權能,首先必須明確登記制度和公示制度。對外層空間自然資源開展開發、利用活動的,無論是國家,還是私人實體,都應在國際外空資源管理機構進行相應的登記,登記內容應當極為詳盡,涉及到開發、利用的天體位置、使用的科學技術以及預期的收益等。在進行相應登記以后,進行合理天數的公示,以便于利益相關國得知有效信息,在有效異議時間內支持他國或者私人實體提出異議,將國家間、私人實體間、國家與私人實體間的矛盾現行解決,促進國際溝通與交流。此外,必須明晰收費制度。對于進行外空資源開發、利用的國家和私人實體,國際外空資源管理機構應有權對其征收一定的費用。國際外空資源管理機構的成員來源必須兼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既包括航天科學技術水平領先的國家,也包括落后的國家,充分兼顧各方利益。因此,無論是航天技術水平領先國,或是尚沒有能力進行外空資源開發、利用的國家,都應當有資格進入國際外空資源管理機構參與國際外空資源的決策事項。該機構可仿效聯合國,建立大會和理事會。
補充、完善相關國內立法
與此同時,我國應當緊密結合國家航天戰略規劃,制定關于外空自然資源開發的整體應對戰略,補充、修正、完善相關的國內立法。縱觀我國空間立法的現狀,我國目前針對外層空間的專門立法還處于空白狀態,并未形成完善的綜合性立法。僅有的一些法律法規的層次也較低,主要是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目前,《航天法》草案的立法工作正在抓緊推進中,立法必須在不違背我國國際義務的前提下有效保障到我國的外空利益,為我國航天事業的穩步、扎實發展提供更為穩固的法律奠基。關于立法的內容,筆者建議,首先,應當載明外空資源的重要地位,確立積極的外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戰略,堅守“國家自由探測外空”規則,明確外空、外空天體及外空資源屬性的界定問題。其次,明確“不得據為己有”原則的同時,在立法中賦予我們國家及私人主體針對外空資源可行使除所有權以外的使用權、收益權等權能,并且針對外空探索、利用的技術革新而產生的知識產權及其轉移、轉讓問題規定專章立法保護,為我國進一步開發、利用外空資源,提供強有力的國家立法支撐。此外,確定我國統一管理空間活動的行政機構,明確其行政地位與權能,為解決日后的空間活動糾紛提供爭端解決機構。
4 結語
人類之于外空資源開發、利用的腳步已經邁向歷史的新征程,國際航天大國之間有關外空資源開發、利用競賽的號角已經吹響,因此,加快推出一套體系健全的綜合性空間國內立法,洞悉國際法律規則、掌控國際輿論從而為我國進行外空資源勘探、開發、利用贏得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實乃必須之舉。與此同時,積極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勇于、敢于、積極肩負起“負責任的航天大國”的職責,致力于外層空間國際合作長期可持續性發展,為維護國家乃至全人類共同利益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