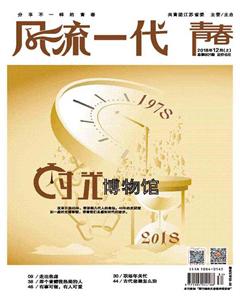保障和自由,哪個更靠譜
耶雅億
我研究生畢業之后,進入上海的一家外企工作,不久與大學男友分手。原本等著婚訊的家人坐不住了,開始催婚,帶我見各種相親對象。沒想到,一座大山攔在面前:男方收入都沒我高。
母親說:“我收入比你爸高,男低女高怎么了?”
我父親這代,最好的婚姻是“組織介紹”。父親從醫學院畢業,分配到了我市最大的醫院。上世紀80年代初期,醫院對醫護人員要求嚴格,為了讓年輕的住院醫生24小時專心工作,定下了住院醫師不許談戀愛的規矩。在做住院醫生的三年內,如果有人戀愛且被院方知曉,輕則受責備勒令分手,重則處分開除。然而,愛情總是悄然滋生的。年輕的醫生、護士天天在一起工作,難免日久生情……“三年不許戀愛”的禁令下,仍然有許多顆心靈碰撞在一起。
在外科護士中,有一位護士吸引了我父親的眼睛。她美麗有氣質,即使是為病人擦身子、倒便盆,仍然充滿一種優雅的氣息,用父親后來的話來說:“你媽就是到街上要飯,也是優雅的……”
在長期的工作接觸中,他們漸漸發生了感情,然而院規如山,他們嚴格遵守著“發乎情,止乎禮”。
三年后,父親結束了住院醫生的考核,與我母親正式開始戀愛。但是按著院規,年輕的醫生、護士一定要住在醫院里,所以,他們仍是各住各的宿舍,只在晚飯后,向值班醫生打過報告的情況下,才能溜出去小聚片時。父親常常在處方后面給母親寫詩,偷偷塞給她,母親常常臉上帶著幸福的紅暈。
他們要領證結婚了,必須要有一位“介紹人”在場,因為在當時大多數人的觀念中“自由戀愛”是不靠譜的,有介紹人保證才可以。于是,我母親科室的護士長充當了介紹人的角色,在拍結婚照的時候,就坐在我母親身邊。
結婚后,我父親在專業上更加刻苦。30歲時,他就成為醫院中最年輕的主治醫師,很快成為外科“一把刀”。但是在38歲的時候,他突發腦溢血,因為搶救及時,命保住了,卻留下了手顫抖、腳不穩的后遺癥,便調到后勤科室工作。
母親說:“他這么個愛上手術臺的人再也不能拿刀,心里已經很痛苦了,我必須安慰鼓勵他。”本來就不善言辭的父親,在這些滄桑磨礪之后,更沉默寡言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多地做家務、管孩子,在妻子下了夜班之后給她按摩酸疼的肩膀……
所以,父母一直認為收入不應是兩個人婚姻中的障礙,而我一個不在“組織”中工作、生活的當代青年,只能一再跟他們說:“你們那年代不買房、不還貸,你們不懂得我的壓力呀———我不要找個帶我飛的,但也不能找拖后腿的啊!”

父母輩始終不太能理解,遵循市場規律生活的我們,到底面臨著怎樣的生活壓力。他們介紹的對象首要的標準是“老實、可靠”,他們覺得“錢少事就少”,婚姻就穩定,難道不是好事么?我無法向他們說明,他們的觀念和經驗已經無法適應今天的生活情境,錢少不代表事就少,事少不代表婚姻就穩定,當然我目前拒絕他們的理由“對方收入沒我高”也不是絕對的,最主要是我沒有看到那些相親對象的前景和提升的潛力。
有一次,父母帶我去他們以前工作的醫院玩,說:“我們曾在這里相遇、相識,曾在這里結婚、生子……”
我聽著他們的故事,心里百般滋味,婚姻不易卻值得,但我已沒法像他們一樣擁有“組織”的保障,我們的保障與自己的工作能力緊密掛鉤,所以我們的愛情與婚姻也面臨著多種考驗。我有時候羨慕父母輩,有時候也慶幸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選擇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