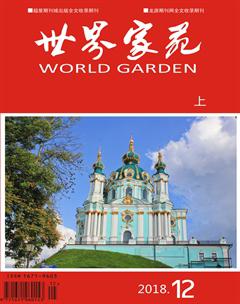淺論《雷雨》的神秘命運色彩
張然朔
命運恰似個調皮且令人討厭的孩子,將每個人玩弄于股掌之間,每個人都拼命想逃出這個怪圈,而始終沒能如愿,只如一朵鮮花被雷雨摧殘的不成樣子,漸漸凋零,就如同死去了一般。曹禺的《雷雨》具有濃郁的神秘色彩,這種神秘色彩似乎是故意渲染,其實是與劇中人物命運緊密相關的。關鍵字:《雷雨》;神秘命運;色彩;正文:
每個人都是命運的犧牲品,所有人都為著自己作反抗,而這一切在三十年前的那個秘密里,都顯得蒼白無力,最終有人死去,有人怎么也躲不過命運給他們開的玩笑!
曹禺是帶著哲學的思考來創作他的劇作的,他不停地在尋找“人究竟該怎么活著?為什么活者?應該走怎樣的人生道路?”,人應該怎樣做,生活才更美好?曹禺說他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東撞西撞,在尋找著生活的道路。……甚至對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面找出一條路來。“他在《雷雨·序》中說《雷雨》的創作“是情感釀成對宇宙間許多神秘事物的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他所指的“神秘事物”到底是什么?這部杰作真正震撼人心的是什么?探究《雷雨》中的序幕和尾聲、人物看似偶然卻是必然的悲劇命運的根源、“天”和“雷雨”意象、作者的世界觀是揭示《雷雨》這部杰作神秘性的關鍵所在。
一
序幕和尾聲帶有濃郁的神秘色彩。這是一個“冬天”(象征冷靜與理智)的下午,“臘月三十,一位面色蒼白、神情沉靜而憂郁的老人,來到十年前是自己的家(罪惡的)而十年后是教堂的醫院(懺悔和被拯救的)來看望自己兩個瘋了的妻子,教堂醫院的舊式家具籠罩的神秘色彩、兩尼姑平和而安靜的神態、小姐弟兩人要講笑話的歡樂氣氛和對兩個瘋子的好奇心態,加上遠處教堂傳來的合唱彌撒聲和大提琴聲,這幅圖畫給人神秘,令人好奇,令人深思。曹禺把這樣一幅圖畫安排在冬天,是有他的深刻寓意的。他把劇情發展的四幕劇的時間安排在一個夏天郁熱的早晨到雷雨的夜間,因為他對夏天的感覺是:“在夏天,炎熱高高升起,天空郁結成一塊燒紅了的鐵,人們會時常不由自己地,更歸回原始的野蠻的路,流著血,不是恨,便是愛,不是愛,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極端,要如電如雷地轟轟地燒一場,中間不容易有一條折衷的路。”
人在欲望無法控制時,正像夏天的高溫燒灼著身心,那原始的蠻力便容易爆發,人會失去理智地跳入欲望這口殘忍的井。而冬天是與夏天相對應的季節,它給人的感覺是萬物冷峻而靜穆,人類清醒而理智。尾聲中,外面一片白雪,世界一片潔凈,當觀眾回味全劇,此時的周樸園在這樣的環境里,在大年三十這中國人準備合家團圓共慶新年的日子里,守著兩個瘋了的妻子,承受著失去三個兒子的痛苦。如果不是他的罪過,這兩個女人不會瘋;如果不是他的罪過,他的兒子們還在,他也該有如這姐弟倆般大小的孫子孫女了。而今天,這個懺悔的基督徒獨自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不能不令觀眾深思,不能不給觀眾心靈的震撼:周樸園的人生結局為什么這樣慘?是誰釀成了這一家庭悲劇?人到底該怎樣生活才會有美滿的結局?
序幕和尾聲中的周樸園才真正認識到自己那么強大的威權卻連自己的命運都不能主宰,這具有強烈的反諷意味。在拜金主義的作弄下,他分不清人是怎么一回事。他對自己同類的殘忍和冷酷的情感來自哪里呢?又會給他們帶來什么呢?他沒想到自己“有秩序”的家庭會毀于一旦,沒想到年輕時的威權到老來卻是這般脆弱,更是沒想到伴隨他余生的是兩個瘋了的女人。這不是報應是什么?
二
《雷雨》以其世俗和宗教的雙重特性,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曹禺的劇作不僅在當時成為各大劇團競相上演的對象,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世俗——宗教儀式的雙重功能,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國家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保留劇目,他長期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這是中國戲劇界的最高殊榮,他的《雷雨》上演就成為一種類似于馬丁·艾斯林所說的“國家的儀式”。
祭典,是宗教儀式的中心,是一種敬神的行為,后來變成娛人的時候,這種祭典就轉化為一種象征,悲劇英雄的犧牲,引起觀眾的“憐憫”和“恐懼”,以使這種情感得到“凈化”。戲劇家常常將主人公的“祭典”當做戲劇的高潮來處理,給人以一種生命的莊嚴和死亡的崇高的美感。英國原型理論家鮑特金指出,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之所以具有永久不衰的魅力是“因為劇中潛伏著幾乎同人類本身一樣古老的犧牲儀式的中心主題”。在戲劇世界中,祭典是和神話相聯系的,喬治·湯姆森在《希臘悲劇詩人與雅典》一書中說:“神話被創造于儀式之中。當一個神話用詩句來加以朗誦時也就是一種帶有祭祀性質的演說活動。”也就是說,戲劇的形式和神話祭祀的表現方式有一致之處。
結束語
我們總是不能明白,時間是以怎樣的姿態行走。恍然一夢浮生,多少念念不忘的記憶正顯得你所憶甚少。有時時間以一種爆發姿態出現,像有人撕裂了堅冰將那底下的生命拿給你看——日月飛逝,我們的血肉里在呼喊在奔走。又或者只是那么一個細微的片段,讓你恍惚想起從前有過類似的畫面類似的氣息類似的觸碰。心在歡暢地呼吸,你卻在流淚。空間的距離并不可怕;它甚至可以因情緒而不存在。真正有威力的是時間,它將人磨成你再也無從辨認的模樣。周樸園愛的是三十年前美麗動人的魯侍萍,是他一去不返的青春熱血。然而現實殘酷地打碎他渴望溫暖的幻象,曾經的苦痛穿越歲月呼喊焦灼在面前。他的人生才是一場悲劇——一場無法被救贖的悲劇。大雨交加的深夜里他們的呼喊聲像要穿透靈魂,穿破那個時代最無助最空洞的絕望。不難想象他也曾懷著滿腔熱血信誓旦旦地要改造這個舊世界;然而重門雕花背后深鎖的是一代代人的靈魂。
參考文獻
[1]高浦棠.“升到上帝的座”上重新審讀曹禺的《雷雨》——《雷雨》本源真詮[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5):41-49.
[2]高浦棠.命運·天意·上帝——《雷雨》的神秘主義思想本體破譯[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3):85-90.
[3]冒鍵.一個永遠“神秘的誘惑”——論《雷雨》的神話意識與現代性焦慮[J].江蘇社會科學,2008(04):224-228.
[4]高浦棠.命運·天意·上帝——《雷雨》的神秘主義思想本體破譯[A].陜西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陜西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04年學術年會論文集[C].陜西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04:9.
[5]陳國華.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臘悲劇對《雷雨》的神秘命運色彩影響探微[J].名作欣賞,2009(12):64-66.
(作者單位:山東省濰坊第一中學高71級2部16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