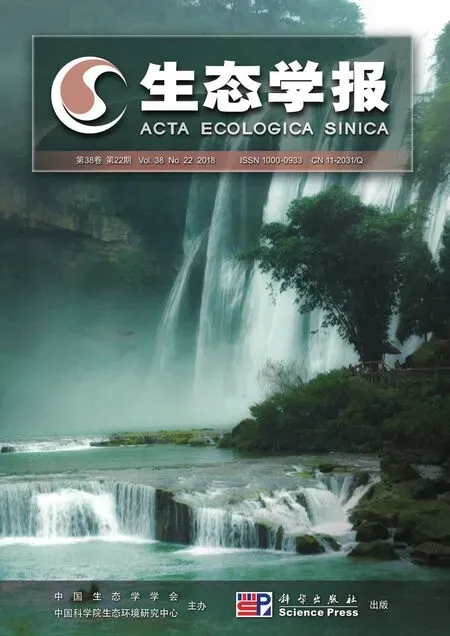基于高通量測序的兩種高寒草甸土壤原核生物群落特征研究
盧 慧,趙 珩,盛玉鈺,叢 微,王秀磊,李迪強(qiáng),張于光,*
1 中央民族大學(xué)生命與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院,北京 100081 2 中國林業(yè)科學(xué)研究院森林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保護(hù)研究所,國家林業(yè)局森林生態(tài)環(huán)境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北京 100091
土壤微生物參與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各種重要的生態(tài)功能,是評價(jià)生態(tài)系統(tǒng)各種地下生態(tài)與生物地球化學(xué)循環(huán)過程對環(huán)境變化的響應(yīng)的一個(gè)重要指標(biāo)[1],近年來,已有研究報(bào)導(dǎo)了不同環(huán)境下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組成,有學(xué)者認(rèn)為微生物群落的控制因子會(huì)隨著研究尺度的不同而發(fā)生改變[2]。Zhang等[3]發(fā)現(xiàn)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分布受到緯度梯度的影響,而更多的研究認(rèn)為微生物多樣性沿海拔梯度的變化不同[4- 5],pH[6]、土壤養(yǎng)分[7]、土壤溫度[8]或其他因子也可能是影響微生物群落組成的主要因子。
氣候變化對各種生物都會(huì)產(chǎn)生很大影響[9]。由于高海拔和極端的氣候條件,青藏高原是生態(tài)脆弱地區(qū),極易受到環(huán)境干擾[4]。高寒沼澤化草甸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一種草甸與沼澤之間的過渡植被類型,面積為4.9×104km2,是青藏高原分布面積較廣的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一[10]。受到氣候暖干化的影響,多年凍土出現(xiàn)退化,使得土壤表層含水量下降,植物群落隨之發(fā)生變化,從而由高寒沼澤化草甸演替為高寒草甸[11]。有學(xué)者認(rèn)為,植物演替會(huì)對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顯著影響,甚至還會(hu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土壤碳、氮含量的動(dòng)態(tài)變化[12]。因此,作為青藏高原獨(dú)有的高寒草甸生態(tài)系統(tǒng),研究氣候變化對土壤原核生物的影響及其響應(yīng)是十分必要的,對研究該區(qū)域獨(dú)特的微生物地理區(qū)系和預(yù)測全球環(huán)境變化的影響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關(guān)于高寒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研究多集中于植被覆蓋度[13]、植物群落結(jié)構(gòu)[14]、植物第一性生產(chǎn)力[15-16]、土壤碳循環(huán)或氮循環(huán)[17-18]等方面,而對草甸生態(tài)系統(tǒng)土壤微生物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分子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高通量測序技術(shù)作為研究微生物群落組成的有效手段,已被廣泛應(yīng)用于微生物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中,它可以通過對從土壤中提取的微生物總DNA進(jìn)行測序和比較分析,快速的對微生物進(jìn)行有效鑒定[19]。目前,由于受到研究技術(shù)和分析方法的局限,大部分的微生物多樣性研究都集中在物種的多樣性和豐富度等方面,沒有考慮微生物物種或種群間的相互作用,而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Molecular Ecological Networks)分析方法[20]的構(gòu)建為預(yù)測微生物群落組成和多樣性對各種環(huán)境變化的可能響應(yīng)提供了新的機(jī)遇。本研究以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區(qū)高寒沼澤化草甸和高寒草甸的土壤樣品為研究對象,通過Illumina Miseq高通量測序和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相結(jié)合,分析不同高寒草甸類型土壤原核生物群落組成和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特征,并探討影響原核生物群落組成的主要環(huán)境影響因子。
1 研究方法
1.1 取樣方法
選擇青海省三江源地區(qū)的高寒沼澤化草甸(Alpine swamp meadow,簡稱ASM,34°22′15″N, 97°56′57″E,海拔4480 m)和高寒草甸(Alpine meadow,簡稱AM,35°24′28″N, 99°21′6″E,海拔4140 m)為研究對象,各設(shè)立一塊樣地。每塊樣地的坡度、坡向、人為干擾情況盡可能一致。為了在考慮空間異質(zhì)性的同時(shí)降低實(shí)際地形的取樣難度,我們采樣時(shí)對巢式取樣的方法進(jìn)行了簡化,進(jìn)行了“L”形取樣[21]。即在每塊樣地設(shè)立1個(gè)200 m×200 m的網(wǎng)格,以網(wǎng)格內(nèi)任意一個(gè)角為起點(diǎn),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距離分別為10,20,50,100 m和200 m處設(shè)置1 m×1 m的樣方,每塊樣地內(nèi)設(shè)立10個(gè)1 m×1 m樣方,共20個(gè)樣方。在每個(gè)1 m×1 m的樣方內(nèi)采用對角線取樣法采集土壤樣品,取樣深度為0—10 cm,混合后過篩,分成2份,1份低溫保存用于土壤理化性質(zhì)分析,1份-80℃保存用于DNA提取。同時(shí)記錄采樣地點(diǎn)經(jīng)緯度、地形等。
1.2 土壤理化性質(zhì)和植物多樣性測定
在每個(gè)樣方中,調(diào)查植物種類、多度、高度、蓋度等指標(biāo),計(jì)算重要值。物種多樣性的測定采用物種豐富度指數(shù)和香農(nóng)多樣性指數(shù)來表征。

1.3 高通量測序
土壤DNA的提取主要參考Zhou等[23]的方法進(jìn)行。利用土壤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MP Biomedical, Carlsbad,CA)先粗提土壤樣品DNA,然后利用0.5%的低熔點(diǎn)的瓊脂糖凝膠對樣品DNA進(jìn)行純化,利用NanoDrop ND- 1000分光光度計(jì)(Nanodrop Inc)檢測樣品DNA純度,若A260nm/280nm>1.80,A260nm/230nm>1.70則表明樣品DNA符合要求。最后,利用FlUOstar Optima(BMG Labtechm Jena,Germany)方法對純化后的DNA進(jìn)行定量。
以樣品DNA為模板,根據(jù)16S rRNA的V4高變區(qū)設(shè)計(jì)引物,其正向引物為5′-GTGCCAGCMGCCGCGG TAA- 3′ (515F),反向引物為5′-GGACTACHVGGGTWTCTAAT- 3′ (806R)[24],在PCR反應(yīng)體系中進(jìn)行擴(kuò)增。PCR反應(yīng)體系參照Ding等[8]的方法。將600 μL的混合液放入Illumina Miseq(Illumina,San Diego,CA)平臺(tái)(2×150個(gè)序列讀長)進(jìn)行測序。
原始序列根據(jù)Barcode區(qū)分不同的樣本序列,利用FLASH算法[25]處理原始序列的前末端和后末端,將測得的序列進(jìn)行比對分析,去掉低質(zhì)量、較短序列和無法比對到16S rRNA數(shù)據(jù)庫的序列以保證數(shù)據(jù)的可靠性。根據(jù)UCLUST方法[26],將樣點(diǎn)序列以≥97%的相似性劃分為1個(gè)分類操作單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 OTU),采用RDP classifier將代表性O(shè)TU的序列信息比對至相對應(yīng)的物種信息[27],最后對所獲得的OTU數(shù)據(jù)進(jìn)行處理分析。所有的數(shù)據(jù)分析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xué)環(huán)境基因組研究所的網(wǎng)站平臺(tái)完成(http://zhoulab5.rccc.ou.edu:8080)。
1.4 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構(gòu)建
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是基于隨機(jī)矩陣?yán)碚揫20],通過在線平臺(tái)MENA進(jìn)行構(gòu)建和數(shù)據(jù)分析(http://ieg2.ou.edu/mena/),用于研究微生物網(wǎng)絡(luò)互作關(guān)系。為確保OTU相互關(guān)系的準(zhǔn)確性,在構(gòu)建網(wǎng)絡(luò)時(shí),去除同一樣地10個(gè)平行樣品中出現(xiàn)次數(shù)低于70%的OTUs。網(wǎng)絡(luò)構(gòu)建時(shí),將基于隨機(jī)矩陣?yán)碚?自動(dòng)生成閾值。每個(gè)網(wǎng)絡(luò)基于快速模塊優(yōu)化的方法形成不同的模塊。本研究中,不同網(wǎng)絡(luò)的拓?fù)湫再|(zhì)通過不同的指數(shù)如平均聯(lián)系數(shù)、平均聚集系數(shù)、平均路徑距離、連通性和模塊性[20]來進(jìn)行表征。網(wǎng)絡(luò)節(jié)點(diǎn)功能通過模塊內(nèi)連接度(Zi)和模塊間連接度(Pi)這2個(gè)指標(biāo)來進(jìn)行劃分,將節(jié)點(diǎn)劃分為4大類型:模塊樞紐(Zi>2.5且Pi≤0.62)、網(wǎng)絡(luò)樞紐(Zi> 2.5且Pi>0.62)、外圍節(jié)點(diǎn)(Zi≤2.5且Pi≤0.62)和連接節(jié)點(diǎn)(Zi≤2.5且Pi>0.62)[8]。此外,將環(huán)境因子當(dāng)成網(wǎng)絡(luò)節(jié)點(diǎn),與原核生物OTUs一起構(gòu)建網(wǎng)絡(luò),用來研究原核生物網(wǎng)絡(luò)中的關(guān)鍵影響因子。
1.5 統(tǒng)計(jì)分析
采用Excel和SPSS 18.0軟件利用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初步統(tǒng)計(jì)和差異性檢驗(yàn);微生物多樣性通過香農(nóng)指數(shù)和辛普森指數(shù)來表征,并計(jì)算微生物的物種豐富度;用除趨勢對應(yīng)分析(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DCA)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進(jìn)行排序;用典范對應(yīng)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研究群落分布格局與環(huán)境因子的關(guān)系;DCA和CCA均使用生物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R軟件中的Vegan軟件包[8]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不相似性檢驗(yàn)均利用在線網(wǎng)站(http://ieg.ou.edu/microarray/)進(jìn)行分析。采用SigmaPlot 12.5軟件作圖。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采用Cytoscape 3.0軟件進(jìn)行可視化。
2 結(jié)果
2.1 兩種高寒草甸的環(huán)境因子特征
對樣地進(jìn)行植物調(diào)查和植物指標(biāo)計(jì)算,結(jié)果表明,ASM(高寒沼澤化草甸)樣地的優(yōu)勢種為藏嵩草(Kobresiatibetica)和矮嵩草(Kobresiahumilis);AM(高寒草甸)樣地的優(yōu)勢種是矮嵩草和高山嵩草(Kobresiapygmaea)。AM樣地的植物多樣性高于ASM,而植物豐富度低于ASM(表1)。


表1 兩種草甸類型土壤的環(huán)境因子比較

2.2 土壤原核生物的多樣性比較
利用Illumina Miseq平臺(tái)對土壤樣品進(jìn)行高通量測序,按照15000序列重新抽樣,基于97%的相似性定位物種水平,共獲得23145個(gè)OTUs,其中,ASM樣地檢測到15555個(gè)OTUs,AM樣地共檢測到16225個(gè)OTUs。香農(nóng)和辛普森多樣性指數(shù)均顯示,AM樣地的原核生物多樣性顯著高于ASM樣地 (P< 0.1)(表2)。

表2 兩種草甸類型的原核生物多樣性
通過除趨勢對應(yīng)分析(DCA)對原核生物群落組成進(jìn)行排序,從圖1中可以看出,兩種草甸類型的原核生物群落能基本分開。進(jìn)一步進(jìn)行不相似性檢驗(yàn)(包括MRPP、Adonis和Anosim),結(jié)果顯示兩種草甸類型原核生物群落組成差異顯著 (P< 0.001,表3)。

圖1 土壤原核生物群落組成的除趨勢對應(yīng)分析(DCA) Fig.1 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soil prokaryotic community compositionASM:高寒沼澤化草甸,Alpine swamp meadow;AM:高寒草甸,Alpine meadow
Table3Dissimilaritytestofprokaryoticcommunitycompositionbetweentwomeadowtypes

不相似性檢驗(yàn)Dissimilarity testδ/R/R2PMRPPδ=0.609 < 0.001AnosimR=0.588 < 0.001AdonisR2=0.183 < 0.001

圖2 原核生物群落組成主要門類的相對豐度 Fig.2 Relative abundance in the major phyla of prokaryotic community composition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疣微菌門,Verrucomicrobia; 浮霉菌門,Planctomycetes;厚壁菌門,Firmicutes;綠彎菌門,Chloroflexi;其他,Others;泉古菌門,Crenarchaeota;芽單胞菌門,Gemmatimonadetes
2.3 土壤原核生物的群落組成差異
檢測到的OTUs可劃分為33個(gè)細(xì)菌門類和2個(gè)古菌門類。其中,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和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是優(yōu)勢門類(圖2),它們在ASM樣地中的相對豐度分別為34.8%、24.7%、11.6%和8.7%,在AM樣地中的相對豐度分別為32.1%、23.1%、19.5% 和6.5%(圖2)。其中,變形菌門、酸桿菌門和擬桿菌門的在ASM樣地中相對豐度較高,而放線菌門在AM樣地中相對豐度較高。
2.4 原核生物的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分析
基于RMT算法,利用高通量測序數(shù)據(jù)構(gòu)建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比較兩種草甸類型土壤原核生物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上的差異,研究它們之間的網(wǎng)絡(luò)互作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拓?fù)湫再|(zhì)見表4。構(gòu)建的兩種草甸類型的網(wǎng)絡(luò)具有相同的閾值(0.890),且均體現(xiàn)了網(wǎng)絡(luò)的無尺度特征、小世界特征以及模塊化特征。ASM的網(wǎng)絡(luò)包含739個(gè)節(jié)點(diǎn)和986個(gè)連接數(shù),而AM網(wǎng)絡(luò)包含860個(gè)節(jié)點(diǎn)和884個(gè)連接數(shù)(表4)。比較兩個(gè)網(wǎng)絡(luò)的拓?fù)湫再|(zhì),ASM具有較高的連通性和平均聚集系數(shù),而AM具有較長的平均距離和較高的模塊性。
模塊樞紐和連接節(jié)點(diǎn)是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中的兩大重要節(jié)點(diǎn)。從圖3可以看出,ASM含有6個(gè)模塊樞紐,其中,4個(gè)模塊樞紐屬于變形菌門,1個(gè)屬于綠彎菌門以及1個(gè)屬于浮霉菌門。而AM含有5個(gè)模塊樞紐,2個(gè)屬于放線菌門,1個(gè)為變形菌門, 1個(gè)為疣微菌門以及1個(gè)為芽單胞菌門。ASM含有5個(gè)連接節(jié)點(diǎn),而AM中不含連接節(jié)點(diǎn)。
2.5 影響土壤原核生物群落組成的環(huán)境因素

通過構(gòu)建網(wǎng)絡(luò)的方法進(jìn)一步進(jìn)行分析,比較原核生物群落組成與環(huán)境因子的聯(lián)系緊密程度,結(jié)果顯示,土壤pH值在所檢測的環(huán)境因子中具有最高的連接數(shù)目,再次表明了pH值在高寒草甸原核生物群落組成上產(chǎn)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圖5)。

表4 兩種草甸類型的原核生物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的拓?fù)湫再|(zhì)

圖3 基于網(wǎng)絡(luò)拓?fù)湫再|(zhì)的原核生物網(wǎng)絡(luò)Z-P分布圖 Fig.3 Z-P plot showing node categories distribution of prokaryotic network based on their topological properties

圖4 原核生物群落與環(huán)境因子間的典范對應(yīng)分析 (CCA) Fig.4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prokaryotic community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圖5 原核生物物種組成與環(huán)境因子的網(wǎng)絡(luò)互作關(guān)系Fig.5 Network interac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rokaryotic taxonomic community OTUs綠色的點(diǎn)表示與pH直接連接的OTUs,藍(lán)色的點(diǎn)表示與pH間接連接的OTUs
3 討論與結(jié)論
Illumina MiSeq高通量測序技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gè)強(qiáng)大的、高效的平臺(tái),可以幫助我們迅速和有效地確定微生物的群落結(jié)構(gòu)組成[18]。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關(guān)注于土壤微生物優(yōu)勢菌群的研究,有學(xué)者認(rèn)為,微生物群落的整體組成在不同生境中的差異可能較大,但優(yōu)勢菌群基本相似,如Shen等[28]通過高通量測序技術(shù)對長白山地區(qū)土壤微生物的研究發(fā)現(xiàn),變形菌門、酸桿菌門和疣微菌門是微生物主要類群,相對豐度分別為23.1%、20.8%和17.29%。Zhang等[7]對高寒草甸演替過程中微生物群落變化進(jìn)行了研究,結(jié)果表明酸桿菌門、變形菌門、放線菌門和浮霉菌門是優(yōu)勢菌群。本研究結(jié)果表明,兩種草甸類型的原核生物多樣性有顯著差異,而變形菌門、酸桿菌門、放線菌門和擬桿菌門的是兩種高寒草甸類型中相對豐度最高的重要細(xì)菌類群,在兩個(gè)樣地中相對豐度累計(jì)均超過79%。可以看出,土壤微生物優(yōu)勢菌群在不同土地類型和不同海拔梯度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可能是由于這些微生物類群種類最多、分布廣,且個(gè)體小、擴(kuò)散性強(qiáng),易形成隨機(jī)性和廣泛性的分布特點(diǎn)[29],除此之外,微生物生境特異性低,適應(yīng)環(huán)境能力強(qiáng)可能也是一個(gè)重要因素[30]。
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作為一種功能強(qiáng)大的工具,可以提供不同物種之間復(fù)雜的生態(tài)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并揭示微生物結(jié)構(gòu)網(wǎng)絡(luò)拓?fù)浣Y(jié)構(gòu)的變化[31]。ASM網(wǎng)絡(luò)較短的平均路徑距離和較高的連通性表明其土壤原核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比AM網(wǎng)絡(luò)更復(fù)雜、更緊密。然而,較短的平均路徑距離意味著局部的干擾可能會(huì)更快地傳達(dá)到整個(gè)網(wǎng)絡(luò)[2,32],而緊密連接的群落可能對干擾更加敏感[2],這意味著具有較長路徑距離的AM網(wǎng)絡(luò)較ASM網(wǎng)絡(luò)更加穩(wěn)定。ASM網(wǎng)絡(luò)的模塊樞紐種類較為單一,大部分OTUs屬于變形菌門,而群落組成的單一化可能導(dǎo)致其聯(lián)系較為緊密,對外界的抵抗能力反而較弱[33]。此外,模塊性的比較結(jié)果也證實(shí)了這一點(diǎn)。網(wǎng)絡(luò)模塊性作為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對抗外界變化的抗性指征[8],在AM樣地中較高,在ASM樣地中較低,說明AM網(wǎng)絡(luò)在應(yīng)對外界環(huán)境變化時(shí)將具有更高的抗性。
土壤pH值通常是影響微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因子之一[6],它與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和組成有著極為緊密的關(guān)系,這種相互關(guān)系在在不同空間尺度的研究中都有報(bào)道,如Shen等[6]發(fā)現(xiàn)土壤 pH 值是控制土壤微生物多樣性和群落組成的關(guān)鍵性因子,并指出pH值對微生物的分布普遍存在影響;張于光等[34]認(rèn)為pH值不僅是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的主要因素,而且影響了微生物的海拔分布格局。土壤pH值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環(huán)境參數(shù),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土壤pH值之所以能對微生物的群落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重要影響,可能與土壤pH值能夠?qū)ν寥榔渌蜃拥淖兓a(chǎn)生間接的影響有關(guān)[35]。本研究中,CCA和分子生態(tài)網(wǎng)絡(luò)的分析結(jié)果均表明,pH值是影響高寒草甸土壤原核生物群落特征的主要因子。
青藏高原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在全球氣候變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全球氣候變化十分敏感。本文通過對青藏高原特有的代表性的植被類型高寒沼澤化草甸和高寒草甸進(jìn)行研究,分析其地下原核生物在全球氣候變化下的響應(yīng),以期為高寒草甸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保護(hù)性管理和應(yīng)對氣候變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