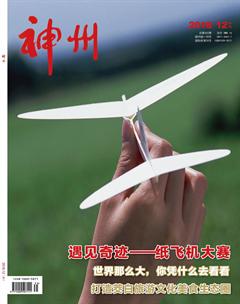生態美學視域下的賈平凹小說研究
吳若菡?閔蕾靜?李悅融
摘要:賈平凹的小說創作大多關注的是鄉土自然與生態變遷,陜北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在他的筆下仿佛被注入了新生,煥發出動人的生態之美。同時,賈平凹也是較早關注自然生態的當代作家,無論是前期作品《懷念狼》《老生》《秦腔》等,還是最新力作《山本》,其中都對秦嶺、對陜北土地的生態構建有著全方位、多角度的細致描寫。本論文以賈平凹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并反思在人與生態日漸抵觸的當下,如何重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身處生態系統中人自身審美狀態的平衡。從生態美學角度解讀賈平凹小說,為研究其作品中的精神生態觀提供更好的切入方式。
關鍵詞:賈平凹;生態美學;鄉土小說;生態精神;視域
在科技水平日益發達的當下社會,與之相隨而來的卻是環境污染、鄉土失落以及人自身生態審美的失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學者率先提出生態美學的論題,反思并探討在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如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自然生態、人文生態以及精神生態觀的良性發展,重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身處生態系統中人自身審美狀態的平衡。賈平凹作為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巨匠,他的小說大多描寫的都是陜北大地上的生態自然、鄉土變遷以及正在上演或早已消散的文化傳統。他的小說并不是將關注點全部放在那些“美”的事物上,對于“非美”的揭示他也是毫不吝嗇的。在賈平凹的小說中,除了存在對“丑”的痛斥與批評,他還為改善人與生態關系,建立“人類詩意地棲居”的生態家園提供了啟示與指導。
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生態美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生態美學研究僅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廣義的生態美學則包含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身處生態系統中人自身審美狀態的平衡。雖然目前對生態美學的定義并不明晰,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卻始終是其研究的核心主題。曾繁仁認為,生態哲學與生態美學完全摒棄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主張人類與自然構成不可分割的生命體系。[1]
在賈平凹的新作《山本》中,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被體現的淋漓盡致。小說以秦嶺渦鎮為背景,講述了陸菊人從娘家帶來的三分胭脂風水寶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贈與井宗秀后所引發的一系列風起云涌的故事。小說中,作者更是對秦嶺一代的草木鳥獸有著詳盡的描述,人對自然的贊美與呵護,自然給予人類的慷慨饋贈,描繪出了秦嶺美好的本真模樣。在題記中,賈平凹寫道“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嶺之志”,他最早的創作構想,就是試圖完成一部以秦嶺為對象的草木記、動物記,雖然最終小說的方向有所偏移,但人與自然的生態美并沒有就此埋沒。平川縣麻縣長便是這樣一個為秦嶺、為生態而生的小人物。
在小說中,麻縣長無法實現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愿,于是他將滿腔的雄心抱負轉移到研究秦嶺的山川地貌、飛禽走獸、花鳥魚蟲上去了。借麻縣長之口,賈平凹描述了秦嶺千奇百怪的自然生態,這也使得《山本》成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作品:
比如有一種猴子通身都是金絲一樣的長毛,有人一樣的大眼,發出的聲音和人說話的節奏也差不多,能大聲吶喊,也會嘟嘟囔囔,只是聽不懂。它們群居,雄猴內斗不斷,一旦勝者,所有的雌猴就安然歸其所有,但它卻一定要咬死那些雌猴的幼兒……[2]
這一小段對秦嶺走獸的細致描述,使得平面化的秦嶺頃刻間就變得立體起來、靈動起來、生機起來,自然的趣味悄然升騰,給讀者以無限意趣。賈平凹不僅寫出了動物的各自特色,還最大化的挖掘了動物性的殘酷——跳脫于“和諧”的視角,人與自然關系的復雜其實是歷史的復雜,歷史的復雜在于人性的復雜,因此《山本》有一個“自然——歷史”的線索,從而引出麻縣長所代表的歷史態度,并以此對比《懷念狼》人性的異化。他對自然的描摹與刻畫,一方面是描摹秦嶺雄渾風光,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突出人物形象。麻縣長觀察動物,結識花草,撰寫風物志,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看的太透。日復一日的在自然中觀察走訪,同是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動物與人又有何不同?他已然將人性的糾結與卑劣摸得一清二楚。現實的“非美”并沒有使麻縣長走上和井宗秀一樣的歧途,與自然結伴,與“美”相依才是一個智者的選擇。小說結尾,渦鎮失守已成定局,麻縣長并沒有倉皇逃跑,他笑著跳入渦潭了結自己的一生——回歸自然。自殺前,他將耗費畢生心血寫成的書稿留給蚯蚓,“一個紙本封皮上寫著《秦嶺志草木部》,一個紙本封皮上寫著《秦嶺志禽獸部》……”。井宗秀是渦鎮的英雄,麻縣長是一個傀儡般的小人物,但多年后,如井宗秀這般的梟雄將層出不窮,掌領渦鎮的風云變幻,又還能有誰記得住井宗秀這個人呢?就如陳先生所說“渦鎮成了一堆塵土,那也就是秦嶺上的一堆塵土么”。但秦嶺的雄渾與壯闊依然不變,秦嶺的花鳥蟲石依然不變,那么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麻縣長也勢必會活在每一個渦鎮人的心中。
當然,賈平凹在小說中并不僅僅講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故事,《懷念狼》就以商州的生態慘劇為背景,給當下社會以警示。小說中,人與狼為了爭奪生存領地而不斷爭斗,最終人類憑借現代武器將狼群趕盡殺絕。但是人類并不是勝利者,“沒有狼了,卻有了人狼了”,人性開始逐漸異化,出現種種丑惡與暴行。賈平凹說:“人是在與狼的斗爭中成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恐懼、孤獨、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是死亡的境地。懷念狼是懷念著勃發的生命,懷念英雄,懷念著世界的平衡。”[3]輕視生命、輕視自然、輕視平衡,于人有百害而無一利,生態鏈的斷裂,人類只能自食惡果。生態之美,美在和諧,美在平衡,人與動物相互掣肘,人與生態相互共存,這個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而這也正是生態美學的核心所在。
二、在社會中構建生態和諧之美
生態美學探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身處生態系統中人自身審美狀態的平衡,因此單單從人與自然角度分析賈平凹小說創作,并不能窮盡其中所蘊含的生態美。人是生態系統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生態美學所說的人與社會,在某種條件下也可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的審美關系。從被創造出來的那刻起,人類就生活在一個社會圈子之中,作為群居動物是無法脫離社會而獨自生存的。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經濟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并沒有使社會走向高度文明化,人與人之間依然充斥著猜疑、構陷、欺騙等等一系列丑惡現象,這些人性的卑劣與陰暗,極大地破壞了人與社會間的生態美。
《山本》塑造了陸菊人這樣一個幾近完美化的女主人公形象。在那個戰火紛飛,人人為了生存不擇手段的荒唐年代,她以聰明、沉穩、勤勞、與人為善的精神品質,站在了人性的道德之巔。為了爭搶土地和權力,軍閥與軍閥之間,土匪與土匪之間,軍閥與土匪之間發生的爭斗在所難免,死掉一個人在那個年代看起來是一樁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陸菊人卻以一種無私大愛給予逝者以關切和同情:
陸菊人又說:這幾年鎮上死的人多,死了的就給立個牌位,錢還是我掏……陸菊人就扳指頭:唐景,唐建,李中水,王布,韓先培,冉雙全,劉保子……還有些人我不知道名字,但都是這幾年在咱鎮上死的,那咋寫?比如被壓在城墻里的那兩個人,比如五雷手下的那些死了的土匪,比如攻城時死的那些保安……[4]
陸菊人對陌生人的悲憫給這個無情的年代點起了燈火,也讓《山本》這個原本悲涼的故事有了溫情的顏色。從賈平凹對陸菊人形象塑造的理想化可以看出,他對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對人性中的善良面是抱有期待的。不論這個世界如何藏污納垢,不論戰爭的殘酷毀掉了多少生命,不論暴力與丑惡是否仍然占據高地,總還會有那么幾個人,以真誠、善良、純真的心給人帶來光亮,而陸菊人就是那個閃著光的小人物。賈平凹對陸菊人和井宗秀的形象塑造也起了一定的對照意味。當陸菊人得知從娘家帶來的三分胭脂地被公公送給井宗秀時,她并沒有勃然大怒,而是推己及人,不僅以一種釋然的心態接受這一現實,還一直默默地勸誡井宗秀。反觀井宗秀,在渦鎮成立預備團之初,他下定決心要護好這一方水土,可是權力和欲望的無限膨脹,讓他漸漸變得暴躁、狠厲、冷血,完全喪失了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信任,最終成為嚴重的擾民者,死不瞑目。“水能載舟,水亦覆舟”,縱觀井宗秀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以暴力和丑惡的手段來對待他人,那么得到的注定是更多的暴力和丑惡。
賈平凹的小說不僅表現了人與社會中人的復雜關系,他還直指人所依存的物象社會——鄉村的破敗與消逝。《老生》以一位唱陰歌的老藝人的視角,記錄了陜西一個小村莊百年間發生的故事,在故事結尾小村莊因瘟疫的蔓延最終消失。村莊“破敗”的開端并不是因為瘟疫的蔓延,早在20世紀早期現代性暴力——槍的介入,就已經漸漸改變了傳統鄉村的寧靜格局。人與人之間階級的對立和沖突漸趨白熱化,老一輩人所堅守的傳統道德之美被年輕一代逐漸拋棄,他們的勢利、冷漠與兇狠,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賈平凹對現代社會人與社會關系的失望。小說結尾,瘟疫的蔓延讓當歸村迅速消亡,唱詩和蕎蕎一起去為死去的人們唱陰歌:
有一天,我問她:你再也不回當歸村了嗎?她說:還回去住什么呢?成了空村、爛村,我要忘了它!我說:那能忘了嗎?她說:就是忘不了啊,一靜下來我就能聽見一種聲音在響,好像是戲生在叫我,又好像是整個村子在刮風。[5]
唱師與蕎蕎的這段對話具有象征意義,它一方面代表鄉村這個物質社會的消亡,代表了人與社會關系的部分終止,但同時在另外一方面,人與社會是緊密相連的,即使斷了筋骨也始終連著血脈。人的欲望與浮躁加速了當歸村的消逝,但當村子真的消失了,當那些罪惡、仇恨與欲望連同它一起消散,人們會越發開始懷念身處本初社會的記憶。在現代都市文明的沖擊下,越來越多的“當歸村”面臨著“消逝”的危險,當然這里的“消逝”并不是村落的消失,而是人與社會關系的冷漠與空缺,金錢本位的思想使傳統鄉村間和諧、美好的社會關系越來越成為一紙空言。人與社會的和諧之美還需人類投入真心共同去打造,付出的越多,那么得到的就會是更加繁榮美好的生態關系。
三、人自身的精神審美生態觀
曾繁仁認為,生態美學包含著新時代內容的人文精神,是對人類當下“非美的”生存狀態的一種改變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更是對人類永久發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關懷,也是對人類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園與精神家園的重建。[6]生態美學所關注的自然與社會方面的內容還停留在人類生活的基礎領域,而對于人自身審美的關注則上升到精神領域,對被理性和經驗束縛住的人提倡精神的解放,回歸自然天性,重獲自由,共同建造人類的精神家園。
《秦腔》中,引生對“性”迷戀與排斥的糾結態度真實地反映出在當下社會中所存在著的人對自身生態本性的自我壓抑與控制。小說的開篇就是引生的一段自述“要我說,我最喜歡的女人還是白雪”,這句話直接而又赤裸地表露了引生對清風街上最美麗的女人——白雪的愛慕之情。但是,引生對白雪的愛戀卻遭到整個清風街的恥笑,人們把他發自本能的追求行為看作是瘋子的瘋人瘋語。引生的愛情不符合當時的倫理道德和日常處世常規,人們拒絕談論“性”這個敏感的話題,并對引生這個真實地表露自己生態本性的“瘋子”給予了最沉痛的道德批判。引生和清風街在人自身情感解放上的矛盾沖突由于“內衣事件”而達到高潮:
我記得我跑回了家,非常地后悔,后悔我怎么就干了那樣的事呢?我的鄰居在他家的院子里解木板,鋸聲很大,我聽見鋸在罵我:流氓!流氓!流氓!我自言自語地說:“我不是流氓,我是正直人啊!”屋子里的家園,桌子呀,笤帚呀,梁上的吊籠呀,它們突然都活了,全都羞我,羞羞羞,能羞綠,正直人么,正直得很么,正直得說不成,那正直么,正直得比竹竿還正,正直得比梧桐樹還正么![7]
這是引生偷了白雪內衣后的一段心理描述,賈平凹將引生無助、羞愧、懊悔的復雜心理刻畫的十分細膩。周圍人對引生的不解、攻擊與謾罵直接導致他以“自宮”的殘忍手段暴力壓抑內心的真實情感,壓抑身為人的生態本性。引生心中的“吶喊”并沒有達到振聾發聵的效果,反而使更多的人對他表示鄙夷與厭棄,就連那些沒有生命的死物都在哂笑引生的流氓行徑。作為一種本能,性欲與人類其他本能一樣,在本質上都是自由的,是一種自然的美的存在狀態。[8]引生與社會秉持的常規道德所對立,拼盡全力掙扎著反抗束縛在人身上的道德枷鎖,但卻被更多戴著枷鎖的人擁著一同墜入深淵。引生看似癡傻實則清醒的悲劇人生,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人自身生態審美的矛盾現實,生態天性的壓抑束縛,使社會相應地呈現出一個“非美”的不平衡狀態。
在《秦腔》中,夏天智是一個活出了真性情,真正為精神家園的建造犧牲了一切的智者。“秦腔”是夏天智耗費畢生心血熱愛的東西,他癡迷于聽秦腔、唱秦腔、制作秦腔臉譜馬勺,他的一輩子都在毫無顧忌、毫無保留的追求所愛。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大浪裹挾下,傳統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碰撞在陜北小鎮中也悄無聲息的發生了。新一代的青年們漸漸地都迷戀上流行音樂的熱鬧與瘋狂,傳統文化的代表——秦腔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式微的道路,就連夏天智的兒子夏風都始終無法理解父親的那份執著與堅守。夏天智就像是清風街上的“守道者”,他守的“道”是傳統文化的精粹,是精神家園的棲息地,是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夏天智對秦腔的熱愛堅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枕著六本《秦腔臉譜集》、蓋著臉譜馬勺才安然入土的。夏天智對秦腔的這份追求暗含著人類對精神世界構造的重視,不畏世俗、不畏流言,解放生態本性,追求自我精神的自由,創造生而為人的精神價值。
賈平凹的小說通過各種人物形象的刻畫與復雜的情節設計,向讀者大眾展現了陜北大地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自身審美的不同立場和態度。“美”和“非美”在小說中并存,相互碰撞出不同的審美火花,為當今社會實現生態和諧、精神文明的美好社會提供了一定思想啟示。
參考文獻:
[1][6]曾繁仁.試論生態美學[J].文藝研究.2002
[2][4]賈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4:329-330,342-343
[3]廖增湖.賈平凹訪談錄[J]當代作家評論.2000
[5]賈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100
[7]賈平凹.秦腔[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39
[8]郭萌.生態美學視域中的《秦腔》[J].名作欣賞.2015
作者簡介:吳若菡(1998-),女,漢,江蘇徐州,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