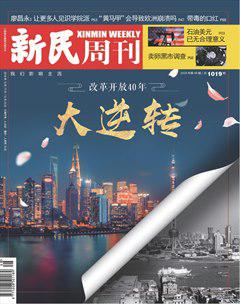從前慢,手藝再次成了香餑餑
周潔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這首木心先生的《從前慢》,讓我們在這個快節奏的生活下,愈加向往起慢節奏的過去。事實上,如果70后、80后回憶童年,那個時候家里夏天床上鋪的竹篾,冬天蓋的棉被,穿在身上的連衣裙和襯衫,無不是手工匠人耗費辰光做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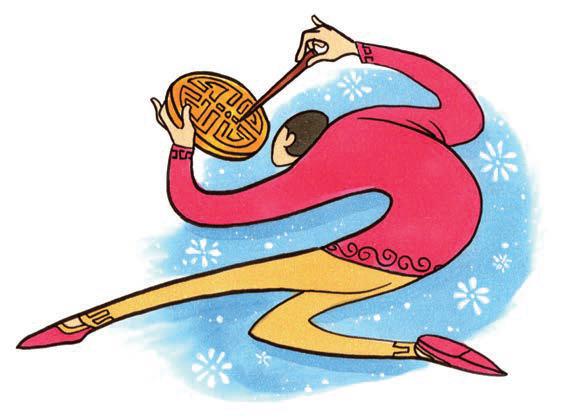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手作品在年輕人眼里成了“土”氣和“老”氣的東西,機器生產的才是“摩登”和“洋氣”。藝術史學者杭間就在文字中坦誠:“回想我小時候,聽到許多鄰人夸我母親手藝好,可是從我讀高中起,就不肯再穿母親給我做的老式衣服。工藝與時代的關系,在我身上就這樣細微地體現出來,我想這就是我和其他很多人所不可逃避的生活。”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慢》中這樣描述“慢”:“速度是出神的形式,這是技術革命送給人的禮物……當人把速度性能交付給一臺機器時,一切都變了:從這時候起,身體已置之度外,交給了一種無形的、非物質化的速度,純粹的速度,實實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誠然,有一段時間,汽車,拖拉機,電線,鐵塔,巨大的工廠和高聳的摩天大樓,是美的象征,美就是速度和機械化,它代表著進步。而手工業永遠和貧窮相接,是落后可恥的。不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工業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而當工業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后,人們的審美又產生了細微的改變——手工業開始復興了。
老祖宗傳下來的手藝再次成了香餑餑,君不見,現在的商場里只要是掛著手工定制的招牌,價格就比機器的貴上好幾倍;也別以為手工業就沒有技術含量,匠人們的眼,比機器更尖,匠人們的手,比機器更穩——手工業的復興,重又把從前的慢轉化成一種美、一種好、一種樸素的精致。
這是一種輪回,一次逆轉,也是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變革帶給我們的思考。
手工刺繡的復興
刺繡,是古代最早的時尚元素,一針一線,一起一落,古代未出嫁的女子要是女紅不好,說出去是要惹人笑話的。
今年暑假大火的《延禧攻略》女主角魏瓔珞,正是秀坊出身的宮女,通過魏瓔珞在繡坊歷經宮女入宮考核、助友人完成繡品、為皇后繡制鳳袍等一系列的故事,劇集用大篇幅、多細節展示了刺繡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手推繡、打籽繡、盤金繡、盤繩繡、珠繡、圈金等多種刺繡工藝包含其中。
這部劇中人物所穿戴的衣服,也大有講究。據悉,《延禧攻略》劇組專門找來了曾在故宮擔任文物修復工作的繡娘,為劇組縫制衣服,所以演員們身上的戲服,個個都是工藝考究:平、光、齊、韻、和、順、細、密缺一不可。
可以說,《延禧攻略》的成功,離不開這些精致的細節,而《延禧攻略》的口碑爆棚,也讓實打實的傳統手藝傳播得更為廣泛了。不少觀眾在看完電視劇后,紛紛表示自己也想學刺繡了。來自上海的佟琳琳告訴記者,追劇期間,她淘寶購買了多幅刺繡初級入門繡品,現在第一幅作品已經繡好了,“刺繡的針法足足有100多種,我只學會了三四種!我們的傳統手藝真是太厲害了,應該要有人傳遞下去。”
其實,新中國成立后,各地都有繡廠,生意都還不錯,成都蜀繡廠的老廠長郝淑萍回憶:“那時候蜀繡廠有幾百多號工人,那時候我在廠里主要繡床單、被面等生活用品,還有服裝廠定制的蜀繡旗袍。”然而,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相較于機械化印花、刺繡的服飾、床上用品、桌布等,大量的耗時耗力讓蜀繡失去了現代化的競爭力。2005年,成都蜀繡廠宣布倒閉。
機器的廣泛應用固然是理由,但刺繡工藝本身,也與當代人的距離太過遙遠。因此,為了復興蜀繡,除了得到政府的支持外,找到市場和人群也是最重要的。郝淑萍從當代審美出發,結合繪畫藝術,將蜀繡嫁接在繪畫、屏風上,保留了蜀繡最古老的132種針法,尤其是蜀繡中最獨特的錦紋針,這樣就保證了在手工藝原汁原味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與發展。
不一味地向市場妥協,在現代生活中找到立足點。這也是中國四大名繡之一的蘇繡大師的共同理念。為適應現代人的審美,蘇州刺繡研究所原所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張美芳不斷在針法、技法、材料和形式方面進行嘗試、探索,以找到傳統技藝與現代藝術、現代生活、現代科技的最佳結合點。
早在2000年,在李政道的啟發和鼓勵之下,張美芳專門成立了創新“科學蘇繡”的研制攻關小組,解決刺繡材料的難題,又抽調4名技藝高超的蘇繡高手專事針技法的研究攻關,并承擔刺繡工作,成功創作了刺繡作品《金核子對撞科學圖像》,受到藝術界和科學界的一致好評。
手工業的復興,重又把從前的慢轉化成一種美、一種好、一種樸素的精致。這是一種輪回,一次逆轉。
不忘初心,這是許多手工業者在推廣自己手藝時的初衷。正如詩人朵漁的描述:“手藝者的慢是一種去掉了因功利心理而生的焦慮的慢,一種沒有暴戾之氣的慢,是陽光下劈木柴、煮茶的慢。手藝者因歷史的積淀,他在生活方式的選擇上對傳統有一種天然的親和……藝術不是一項‘聰明人的事業,而是一種‘笨人的自救。在這里,更多的體現為一種笨拙不靈活的天真精神,一種平衡、靜穆的勞動場面。”

2018 年10 月14 日,廣西柳州,在融水苗族自治縣紅水鄉黃奈苗寨,“繡娘”韋州在檢查一塊繡的花飾質量。
所幸,他們的堅持如今都有著良好的反饋。今年3月,蜀繡首批產品經中歐班列遠赴波蘭展銷,上千萬元的貨物不到一周便被搶購一空;今年9月,人們發現蘇繡被應用到手表的設計中,所用的絲線是平時蘇繡絲線直徑的十六分之一,包括“梅蘭竹菊”、仙鶴、梅花鹿等設計元素,讓不少觀眾贊不絕口。
雕與刻的今日時光
有人說,手藝給機器生產和工業文明的首要的啟示在于“人與物的關系”。在手藝活動中,人和物的關系是緊密的,它融入了情感和心靈的交流,這賦予了手藝人以尊嚴,也賦予了物以尊嚴。雕刻便是一項代表手藝。
“雕刻百工,爐捶萬物。”雕刻一技,可在金銀銅錫之器,也可在樹木食材。刀法好比書法,在一次次的減法造型中,我們能夠體會到作品“脫殼而出”的驚喜。其中,磚雕雖是模仿石雕而來,但比石雕更經濟,省工,因此在民間建筑中被廣泛采用,成了生活中最常見的雕刻產品。磚雕也與木雕、石雕一起,被譽為“江南三雕”。
迎風舞動的飛云、騰云駕霧的蟠龍、爭芳斗艷的牡丹、含苞欲放的荷花……在師傅們的磚刀下,蘊含著各種吉祥含義的磚雕應運而生。“很多新建仿古建筑的負責人找到我們這里,用我們的產品做迎門墻或者地上、墻上的圖案。”東陽磚雕的磚雕師傅何鵬介紹了如今磚雕的一大去處。
其實,早在漢初,中國便已出現了磚雕雛形;明清時期,磚雕在祠堂、廟宇和民居中廣泛采用。不過隨著現代建筑的興起,磚雕裝飾已日漸式微,愿意學習這門技藝的年輕人也并不多,更何況還有機器雕刻攻占市場,磚雕沒落實在是太過平常的故事。
不過,隨著這些年我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中式風格”再度成為熱門,磚雕也成了裝修時會考慮的手工業產品。廣東非遺磚雕傳承人何世良就表示,雖然現在建筑上運用磚雕技藝的機會越來越少了,但磚雕可以被做成工藝品,比如小擺件和座屏,把磚雕作品做成裝置藝術。另外,還可以在傳統技藝的基礎上求新,比如加入寫實手法,加入國畫構圖,同時運用木雕、玉雕等技法,讓作品既有傳統性又吸引當代人的目光。
除了磚雕,木雕的復興也同此理。中國木雕藝術大師、國家級非遺傳承人黃小明認為,“只是繼承傳統,沒有創新,那是不流之水。脫離傳統,單獨創新,那是無根之木。”
他設計的竹簡式木雕、超寫實木雕、速寫木雕、取景框木雕等藝術表現形式,提升了傳統東陽木雕藝術的裝飾范圍。在傳幫帶方面,他也有奇招——通過互聯網傳播模式,從全國各地報名者中挑選徒弟,為木雕技藝的傳承找到了更多“能人”和“才人”。
其實,不論刺繡或是雕刻,都只是手工藝復興的一個測寫。“手工業復興”,復興的并非本色的手藝,因為它是歷史和自然的產物,人們無法阻擋。正如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副院長王敏教授曾在一次講座中指出的那樣,傳統工藝跟現代生活相結合,并非完全復原古代作品,更多的是在今天的環境下,今天的生活中,運用今天有的材料,發現今天的美,借鑒傳統的工藝方法,創造今天的工藝作品,服務現代人的生活、滋潤現代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手工業復興”,本質上是人們通過手工業行當中所需要的精神、觀念和氣質給人們的啟示,作為工業文明的對立面和平衡面,“手工業復興”,有助于整個工業文明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