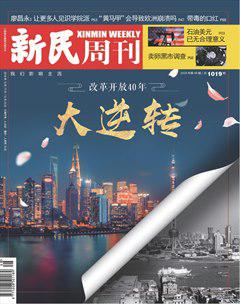法國“黃馬甲”會導致歐洲崩潰嗎?
和靜鈞

自11月17日始,每周六都會在凱旋門、香榭麗舍等附近出現一群穿黃背心的示威者,到了12月8日,除巴黎迎來新一波暴力示威高潮、被拘捕的抗議者達上千人之外,法國“黃馬甲”的身影開始漫延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荷蘭的海牙、德國的柏林及其他周邊歐洲國家。
正如世界上出現過的“符號革命”一樣,一旦某一場群體事件被符號化和暴力化后,事件已經上升為社會思潮與階層對立相結合的運動,它更具有持久性、組織性和對抗性,對它的理解層面就不應只止于抗議者表面的訴求,而是指向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國際背景。外交政策專家多米尼克·莫伊西認為,法國總統當前面臨的危機不僅僅是法國的危機,同時也是整個歐洲未來的危機。
表面看,引發抗議的導火索是法國總統馬克龍計劃上調燃油稅,但上調前后的油價差只相當于人民幣5毛錢,不至于成為由奢入儉的法國民眾被壓垮的那根稻草。抗議者抱怨“社會的冬天已經來臨”,認為他們的總統總是“談論世界末日”,而民眾面對的卻是怎么“度過這個月末”,顯然,歐洲社會在上層階層的“高政治”議程與中低階層的“低政治”需求上出現了嚴重沖突,在政治上的“高大上”還是“經濟福利和生活水平”的實在性的選擇上,處在國策的兩難困境。
先來看法國及歐洲精英階層的“高政治”議題。自二戰后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以來,歐洲在防務上成為美國霸權體系上的一支縱隊,結束了歐洲為中心的全球政治力量格局,而經濟上完全捆綁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基本上淪為美國的附庸。歐洲雖然實現了戰后的復蘇,但付出了與美國結成“自由世界”后不得不接受從屬地位的代價。歐洲精英階層打造的歐盟以及構想的“歐洲軍”,均是歐洲戴高樂主義及多極化渴求的追求路徑。歐洲精英在“巴黎氣候協議”問題上步調一致,無非是想借能源產業轉型重新獲得國家實力上的大幅度提升,扭轉新產業競爭中不斷表現出的劣勢。
歐洲要么迎來大改革,要么繼續沉淪,在“黃馬甲”的運動中繼續在政府更替上原地踏步。
歐洲的資產階級統治合法性是受到福利社會主義的平衡,在歐洲精英階層構筑“高政治”命題之時,同樣意味著擠占福利社會主義的資源。歐盟之路并不順利,歐元貨幣一體化,卻在財政一體化進展緩慢,各個機會主義的成員國爭相抬高財政預算赤字,不負責任地把債務轉嫁到其他負責任的成員國之時,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領袖,就不得不出手救助,最終意味著國內稅收的不斷上升。
而法國民眾更多是關心“低政治”的經濟福利等與自身生活舒適度相關的問題。歐盟化沖淡了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空間,民眾的愛國主義很難形成政治上的動員,是民眾關切與精英議程脫節的初始原因。而右翼政黨和組織操作民粹主義,是導致社會結構緊張和政府推進改革受阻的主要原因。假如歐洲經濟一直向好,這類脫節和緊張不會上升為嚴重社會問題,但自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元計價的法國GDP已經從2.918萬億美元萎縮到2017年的2.583萬億美元,降幅約為11.55%,經濟惡化、產業競爭落后、失業率居高不下、老齡化社會、移民等種種問題交織在一起,民眾把當前生活中的不滿與怨恨,會毫不猶豫發泄到政府任何一項會立即導致其生活負擔加重的政策和改革上,即便僅僅只是增加5毛錢的額外負擔。
從全球格局上看,隨著OPEC與非OPEC國減產協議的達成,美國逐漸占據石油及天然氣定價權,全球經濟的控制權向美國傾斜之勢越加明顯,歐洲在這一波傳統能源價格戰中邊緣化,新能源政策有可能無疾而終,巨額早期投資也有可能付諸東流。而在新產業及新經濟的挑戰中,新興經濟體表現優越,處于內耗的歐洲未能搭上這一趟班車,多極化進程并未如歐洲精英所愿一樣行進。因此,從整個大勢上看,歐洲要么迎來大改革,要么繼續沉淪,在“黃馬甲”風暴中繼續在政府更替上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