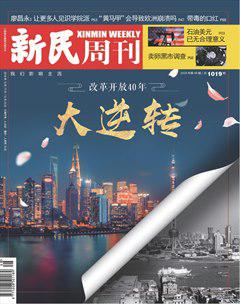“閑置”冷凍胚胎,是毀是留?
應琛

今年是世界首例試管嬰兒誕生40周年,也是中國大陸首例試管嬰兒出生30周年。這一輔助生殖技術在給萬千家庭帶來天倫之樂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棘手的法律難題與倫理窘境。
繼“凍卵”之后,“凍胚”又掀波瀾。近日,多家媒體相繼報道,隨著開展輔助生殖技術的患者數量增加和胚胎移植成功率的提升,手術中,剩余胚胎的數量越來越多,而不少胚胎主人在協定保存期限臨近時卻杳無音信。面對大量可發育為人類生命的“無主”冷凍胚胎,醫院又不敢輕易拋棄,致使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和地區胚胎冷凍庫空間告急之聲此起彼伏。
剩余冷凍胚胎的處置,成為人們不得不直面的問題之一。
胚胎歸屬權第一案塵埃落定
“白發人送黑發人,乃人生至悲之事,更何況暮年遽喪獨子、獨女!沈杰、劉曦(夫妻)意外死亡,其父母承歡膝下、縱享天倫之樂不再,‘失獨之痛,非常人所能體味……”“沈杰、劉曦遺留下來的胚胎,則成為雙方家族血脈的唯一載體,承載著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撫慰等人格利益……”
在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時永才親自擔任審判長的合議庭,經過審理后宣判的終審《民事判決書》上,上述令人“催淚動情”的文字,出現在了該判決書的說理部分。
這起從2013年11月由宜興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先后多次開庭審理,在一審判決后受到社會各界和媒體廣泛關注的國內首例冷凍胚胎繼承糾紛案,經過一審、二審長達近10個月的審理,終得定讞。
據了解,判決書直接撤銷了一審判決,并基于倫理、情感、特殊利益保護等情節,認為沈新南、邵玉妹(沈杰父母)和劉金法、胡杏仙(劉曦父母)要求獲得涉案胚胎的監管權和處置權合情、合理,且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相關規定,判決沈杰、劉曦存放于南京鼓樓醫院的4枚冷凍胚胎由上訴人沈新南、邵玉妹和被上訴人劉金法、胡杏仙共同監管和處置。
這是國內第一例通過法院最終判定胚胎歸屬權的案例。
而這起案件糾紛,源于《新民周刊》曾經報道過的一場讓人扼腕嘆息的事故。
沈杰(男)與劉曦 (女)2010年10月13日登記結婚,于2012年4月6日取得生育證明。2012年8月,夫妻二人因“原發性不孕癥、外院反復促排卵及人工授精失敗”,要求在南京市鼓樓醫院施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手術。鼓樓醫院在治療過程中,獲卵15枚,受精13枚,分裂13枚。取卵后72小時為預防“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鼓樓醫院未對劉曦進行新鮮胚胎移植,而是當天冷凍4枚受精胚胎在鼓樓醫院生殖中心冷凍保存。
其間,劉曦與醫院簽訂《輔助生殖染色體診斷知情同意書》,夫妻倆后又簽訂《配子、胚胎去向知情同意書》、《胚胎和囊胚冷凍、解凍及移植知情同意書》等,鼓樓醫院還明確,胚胎不能無限期保存,并強調冷凍保存期限為一年,首次費用為三個月,如需繼續冷凍,需補交費用,逾期不予保存;如果超過保存期,沈杰、劉曦選擇同意將胚胎丟棄。
然而,就在即將施行手術前數天,2013年3月20日深夜,沈杰駕駛車輛發生側翻撞到樹木,妻子當日死亡,沈杰也經搶救5天后死亡。此后,雙方父母因處理冷凍胚胎事宜發生爭執。雙方爭執不下遂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判決駁回了原被告的訴訟請求,認為含有未來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樣任意轉讓或繼承,依法不能成為繼承的標的,以及施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手術的夫妻已經死亡,其留下的胚胎所享有的受限制的權利不能被繼承。
而其中最大的法律障礙來自對受精胚胎法律屬性的理解,以及衛生部相關規定中“胚胎不能買賣、贈送和禁止實施代孕”等潛在的倫理、法律問題爭議。
對此,《判決書》也給予了較為清晰的釋法、說理和表述。《判決書》認為:在我國現行法律對胚胎的法律屬性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考慮到受精胚胎具有潛在的生命特質,不僅含有死者夫婦DNA等遺傳物質,且含有雙方父母兩個家族的遺傳信息,雙方父母與涉案胚胎亦具有生命倫理上的密切關聯性,不但是世界上唯一關心胚胎命運的主體,而且亦應當是胚胎之最近最大和最密切傾向性利益的享有者。
《判決書》還強調:“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對相關醫療機構和人員在從事人工生殖輔助技術時的管理規定,南京鼓樓醫院不得基于部門規章的行政管理規定對抗當事人基于私法所享有的正當權利”,最終依據法理原則化解了這一爭議問題。
在獲得冷凍胚胎的所有權之后,四位老人最終在一家代孕機構的幫助下,將胚胎植入一位老撾代孕媽媽的子宮里,因為在老撾,商業代孕是合法的。2017年12月,男孩甜甜出生。
上萬冷凍胚胎無人認領
對于國內首例冷凍胚胎繼承案的最終結果,相關法律專家認為,該判決“十分大膽”地厘清了多重法律問題和倫理問題,一旦獲得法學界、醫學界后續認可,勢必引發重要反響,并對今后出現類似爭議案件,具有典型的判例價值,還將對相關行政管理規定的適時修改,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但在現實中,不少醫院被數量眾多、難以處置的冷凍胚胎困擾著。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主任醫師、上海集愛遺傳與不孕診療中心常務副院長孫曉溪告訴記者,現在全國各個生殖中心都普遍存在“冷凍胚胎無人認領”這一問題。“這里面可能存在幾種情況:一種是失聯的,醫院無法與胚胎的主人取得聯系;一種是逾期不付費的,即便醫院聯系上他們,通知他們來補交保管費的,但以各種理由不來的;還有一種就是夫妻離婚或者死亡的,因為胚胎是夫妻雙方共有的,發生這種情況一般胚胎就不能用了,但如何處置也成為一個死結。”
2015年,江蘇省人民醫院生殖中心的一道“最后通牒”攪動著輿論:由于上萬個冷凍胚胎無人問津,凡是2005年前在該中心冷凍的胚胎,若在一個月內不續費,將按照之前簽署的知情同意書進行銷毀。當時,該中心有近3萬例冷凍細胞逾期無人認領,醫院為保存該部分胚胎墊付了150元每人每月的高額費用。
據了解,接受輔助生殖治療的女性患者先要通過藥物一次取得8—10枚卵子,受精后產生胚胎。若患者當時的身體條件不適合移植,就會選擇冷凍全部胚胎,等到身體條件適宜時再復蘇胚胎,進行移植,這樣也可以減少并發癥的發生;若患者移植新鮮胚胎后還有剩余胚胎,也會選擇將剩余胚胎冷凍起來。
一般情況下,在選擇冷凍胚胎時,接受輔助生殖治療的夫婦和醫院會共同簽署一份《胚胎冷凍、解凍及移植知情同意書》,自愿繳付胚胎冷凍保存費,并選擇逾期將冷凍胚胎經醫學方法處理后丟棄或去標識后供科研。

河南洛陽,300 多對胚胎“遺忘”在醫院,護士每天打電話勸續費。

“過了半年保存期,醫生會聯系患者,詢問其是否選擇繼續凍存胚胎,‘是則續交保存費,如果他們放棄就簽署《放棄冷凍胚胎知情同意書》。”孫曉溪表示,但實際上簽署《放棄冷凍胚胎知情同意書》的人很少,“現在的續存率大概在90%以上,尤其是國家全面放開二孩后,大家更愿意去保存了。”
在集愛每年有近萬名患者開展輔助生殖技術,這就意味著每年會新增上萬個冷凍胚胎。“首先,保存的場地占得越來越大。我們輔助生殖中心最初建立的時候是260平方米,現在已經發展成3000平方米。其中,新造的液氮儲存室也從原本 10平方米變成了100平方米。”孫曉溪進一步說道,“冷凍胚胎的儲存條件非常嚴格,要在零下196℃的液氮中。我們每年都要新購置三四個液氮罐,還要對液氮進行補充。儲存的環境會有24小時的監控,還要花費大量人力成本,定期對儲存罐進行維護,以及監護這些冷凍胚胎。”
處置難題主要在倫理層面
單從法律上講,按照我國所采納的國際通行的標準,這些發育時間不滿14天的胚胎并不具有明確的生命地位,在胚胎主人知情同意與意見一致的情況下,放棄對冷凍胚胎的保存并不違背法律。
英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頒布了人工授精與胚胎法,明文規定冷凍胚胎的保存時間不得超過10年。依據我國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逾期6個月不續費被視為自動放棄胚胎。
由于觸及生命這一相對禁忌的話題,逾期的冷凍胚胎去留問題已然上升到了倫理層面。
江蘇省衛生法學會副會長胡曉翔曾表示,目前國內對冷凍胚胎已經有一個普遍的定性:胚胎總的來講是物,但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正是這所謂的“一定的特殊性”,導致當事醫院在處理上非常糾結。法律應該明確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保存與使用限制,將人工生殖的許可、管理及監督納入法治的軌道,而不是只靠醫院與患者的一紙“協議”約束雙方的行為。
“胚胎介于人和物之間,可以形成生命,所以在倫理這一塊還是非常重視的。”孫曉溪說,要銷毀這些無人認領的冷凍胚胎必須通過醫院的醫學倫理委員會,“還要組織各方人士到場,才能做銷毀處理。”
依據我國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逾期6個月不續費被視為自動放棄胚胎。
孫曉溪強調,輔助生殖中心的醫生對胚胎都懷有一定的敬畏心,實際操作中并不會完全嚴格地按照知情同意書上寫的那樣到期就把胚胎銷毀,“加上國家放開二孩,有些夫妻之前覺得冷凍胚胎沒用,但現在又認為非常重要。這些因素都導致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有些困難。”
孫曉溪給記者舉了一個曾經發生過的案例。有一名女性患者在集愛生完孩子后,冷凍了五六個多余的胚胎。后來她超過6個月未繳費,醫院跟她聯系,她總是以人不在上海、過來不方便等各種理由推脫。就這樣,她大概欠了五六年的保管費。后來二孩政策放開了,這名患者突然打電話過來問,詢問她的冷凍胚胎。當得知胚胎還在時,她立馬補交了費用,后來成功利用這些胚胎懷孕了。
“她很慶幸自己當初沒有說放棄這些胚胎,醫院也沒有因為欠費把這些胚胎銷毀。”孫曉溪表示,正是因為當時沒有得到她本人的授權,醫生考慮再三才沒有按照規定銷毀這些胚胎。
孫曉溪補充道,因疾病需行生育力保存的配子與胚胎屬于稀缺生殖資源,可酌情延長保存期限,尤其是年少者保存時間更久,保持期間須根據出現的問題或可能發生事件予以階段知情告知,每5年續簽知情同意書。對于不再續存胚胎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的夫婦,應嚴格核對信息、保存時限等內容,遵守隱私與保密原則,“對于失聯或保存時限達上限的胚胎,經倫理委員會督導下實施銷毀或用于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