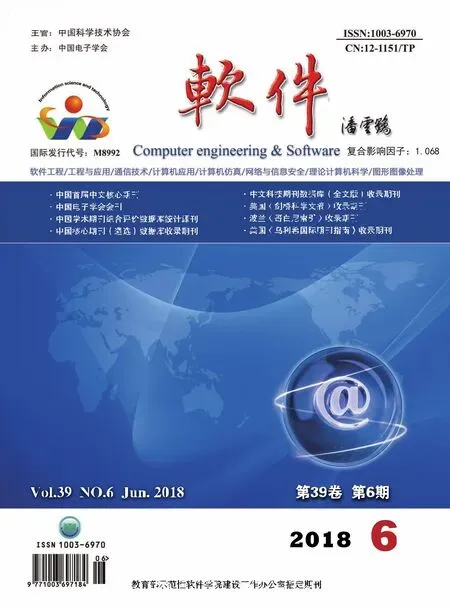MOOC的突破與挑戰(zhàn):一種課程觀點(diǎn)
張海燕
(遼寧師范大學(xué)計(jì)算機(jī)與信息技術(shù)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81)
0 引言
當(dāng)前,國(guó)內(nèi)外很多大學(xué)都紛紛推出自己的MOOC,并將其作為自身品牌影響力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很多一線教師也借助于高質(zhì)量的MOOC課程進(jìn)行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學(xué)習(xí)、深度學(xué)習(xí)等教學(xué)改革嘗試,旨在提高教育質(zhì)量。MOOC,以及后續(xù)出現(xiàn)的SPOC,集合了教育研究、技術(shù)探索的新成果,以完全開放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出來。MOOC不僅為跨越國(guó)界教育主體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提供了可能,充當(dāng)了典型范例,也為打破我國(guó)孤立的傳統(tǒng)課堂教學(xué)壁壘實(shí)現(xiàn)混合式學(xué)習(xí)充當(dāng)了一副催化劑。MOOC讓教育參與者們看到了更接近于學(xué)習(xí)本質(zhì)的教學(xué)。MOOC引發(fā)的教學(xué)改革也勢(shì)不可擋。對(duì)所有基于MOOC進(jìn)行教育改革的參與者而言,深入分析MOOC對(duì)傳統(tǒng)教育的突破,了解MOOC自身存在的缺陷與挑戰(zhàn),才能有效利用MOOC,讓每一位學(xué)習(xí)者都能獲得適合其需求的教育,避開或嘗試解決存在的缺陷和挑戰(zhàn),MOOC的價(jià)值才能更好地實(shí)現(xiàn)。
1 MOOC的定義及其發(fā)展
MOOC(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是大規(guī)模在線開放課程的簡(jiǎn)稱。它是隨著網(wǎng)絡(luò)資源、網(wǎng)絡(luò)課程、尤其是開放教育資源運(yùn)動(dòng)的深入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1]。
1.1 MOOC的概念
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MOOC并沒有給出統(tǒng)一的定義。2018年3月維基百科的定義依然是:MOOC是一種以開放訪問和無限制參與為目的的網(wǎng)絡(luò)在線課程。它除了采用傳統(tǒng)的諸如視頻、閱讀材料、問題集等課程資源以外,還使用了交互式用戶論壇,以便構(gòu)建學(xué)生、教授、助教組成的學(xué)習(xí)社區(qū)[2]。
1.2 MOOC的發(fā)展
2007年8月,美國(guó)猶他大學(xué)戴維·威利(David Wiley)教授在 Wiki上開設(shè)了一門全球用戶都可以共享的開放課程。2008年1月,加拿大里賈納大學(xué)(University of Regina)的Alec Couros教授邀請(qǐng)全球眾多專家遠(yuǎn)程參與開設(shè)了網(wǎng)絡(luò)課程“社會(huì)媒體與開放教育”(Social Media and Open Education)。這兩個(gè)項(xiàng)目為 MOOCs課程模式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和技術(shù)準(zhǔn)備。
2008年,加拿大學(xué)者戴維·科米爾(Dave Cormier)和布賴恩·亞歷山大(Bryan Alexander)提出了MOOC這一專用名稱,9月,加拿大學(xué)者喬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和斯蒂芬·唐斯(Stephen Downes)開設(shè)了第一門真正的MOOC課程“聯(lián)結(jié)主義與聯(lián)結(jié)知識(shí)”在線課程(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 Online Course,CCK08)[3]。
在 2012年,Udacity、Coursera、edX 三大 MOOC平臺(tái)相繼成立并獲得大量投資,并且部分課程被大學(xué)承認(rèn)學(xué)分,MOOC經(jīng)歷了井噴式發(fā)展,紐約時(shí)報(bào)據(jù)此將2012年稱為MOOC元年[4]。
1.3 MOOC的發(fā)展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
MOOC的發(fā)展也引起了中國(guó)高等教育領(lǐng)域的重視。2013年,上海市推出“上海高校課程資源共享平臺(tái)”。2013年,北京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上海交通大學(xué)相繼與 edX、Coursera建立合作伙伴關(guān)系,向全球提供在線課程。除了與國(guó)外平臺(tái)的合作,中國(guó)高校也在尋求國(guó)內(nèi)高校的強(qiáng)強(qiáng)聯(lián)手,實(shí)現(xiàn)MOOC的本土化[5]。
2 MOOC對(duì)傳統(tǒng)教育的突破
我國(guó)高等教育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不斷改革與發(fā)展,為國(guó)家培養(yǎng)了無數(shù)杰出的社會(huì)工作者。但是,不論是在國(guó)內(nèi)還是國(guó)外,高等教育備受詬病。畢業(yè)生知識(shí)陳舊、動(dòng)手實(shí)踐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封閉僵化、教學(xué)方法落后、收費(fèi)過高等都使其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大打折扣。由世界頂級(jí)教育者、領(lǐng)域?qū)<摇⒓夹g(shù)專家親自操刀、攜幾千萬風(fēng)投資金、團(tuán)隊(duì)運(yùn)作的 MOOC的出現(xiàn)及實(shí)施,使高等教育的參與者看到并親自體驗(yàn)到了未來高等教育的喜人前景。
2.1 技術(shù)的無縫深度介入
縱觀國(guó)內(nèi)外MOOC早期研究者的學(xué)科背景,他們大都出自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相關(guān)專業(yè)及教育技術(shù)學(xué)專業(yè)。技術(shù)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更改變了教育。當(dāng)前,所有教育者已經(jīng)不再糾結(jié)于教育過程中用還是不用技術(shù),甚至也不用過多考慮如何使技術(shù)更好地為教育服務(wù),教育參與者只需要選擇業(yè)已成熟的技術(shù)獲取信息、存儲(chǔ)信息、交流信息、創(chuàng)造信息、傳播信息即可,技術(shù)隱于教育之后,教育與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了真正的無縫銜接。Kop和Sara lbn等認(rèn)為,MOOC由教師、學(xué)習(xí)者、主題、學(xué)習(xí)材料和情境五個(gè)要素組成。李青等總結(jié)認(rèn)為MOOC由物的要素(平臺(tái)與工具,課程信息,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和人的要素(課程教師,學(xué)習(xí)者,課程協(xié)調(diào)人)構(gòu)成[6]。從MOOC平臺(tái)的架構(gòu),學(xué)習(xí)材料、主題的傳遞與在線生成,到師生交互與學(xué)生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的展開,學(xué)習(xí)者個(gè)人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的建構(gòu),課程的管理等都離不開技術(shù)的參與,技術(shù)成為貫穿于MOOC課程始終的唯一因素,但是技術(shù)卻不是MOOC的構(gòu)成要素,更不是MOOC的研究要素。重點(diǎn)進(jìn)行教學(xué)過程及影響教學(xué)過程相關(guān)因素的設(shè)計(jì)與研究是MOOC與網(wǎng)絡(luò)課程、視頻開放課程的根本不同。
2.2 教學(xué)過程各要素的裂變[7]
在傳統(tǒng)課程實(shí)施中,教學(xué)過程的基本構(gòu)成要素有教師、學(xué)生、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手段[8]。在 MOOC中,這些教學(xué)要素都產(chǎn)生了很大變化。它們分別由知名教授引領(lǐng)的教育團(tuán)隊(duì)、遍布世界的主動(dòng)學(xué)習(xí)者、預(yù)設(shè)與在線生成的課程內(nèi)容以及線上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線下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個(gè)人學(xué)習(xí)環(huán)境構(gòu)成的學(xué)習(xí)生態(tài)系統(tǒng)所取代。在MOOC中,大量資本介入吸引了眾多優(yōu)秀教育者與團(tuán)隊(duì)的參與,這使得MOOC課程質(zhì)量的重要保證。MOOC中留下來學(xué)習(xí)者,最大的特點(diǎn)就是主動(dòng)性。在設(shè)計(jì)良好的MOOC課程中,通過名師、教學(xué)輔助團(tuán)隊(duì)、學(xué)習(xí)者共同體構(gòu)建而成的開放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可以充分滿足每一個(gè)主動(dòng)學(xué)習(xí)者的需要。在MOOC中,由教師團(tuán)隊(duì)提供的課程內(nèi)容與由MOOC學(xué)習(xí)者在學(xué)習(xí)過程中生成的課程內(nèi)容,甚至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都成為了MOOC的課程內(nèi)容,集中體現(xiàn)了課程研究與教育研究的新發(fā)展[9]。不論是cMOOC還是小 MOOC,借助于開放的學(xué)習(xí)網(wǎng)絡(luò),MOOC教學(xué)團(tuán)隊(duì)和學(xué)習(xí)者個(gè)體,共同構(gòu)建了無主次之分的在線環(huán)境、線下學(xué)習(xí)共同體、個(gè)人學(xué)習(xí)環(huán)境,使學(xué)習(xí)的實(shí)施與研究更接近學(xué)習(xí)的本質(zhì),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已經(jīng)超越了過去的意義,將其稱為學(xué)習(xí)生態(tài)圈或許更恰當(dāng)[10][11]。
2.3 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教育研究思維的轉(zhuǎn)變
在傳統(tǒng)教育研究中,人們獲取數(shù)據(jù)的能力有限,因此,教育研究采用抽取隨機(jī)樣本的方式進(jìn)行,其目的在于使用一定量的數(shù)據(jù)得到盡量多的信息。顯而易見,這樣得到的信息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這些信息都是按照預(yù)先設(shè)定好的問題獲得,它并不能適用于教育中的一切可能狀況。MOOC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信息化教育進(jìn)入了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在這個(gè)以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分析、數(shù)據(jù)預(yù)測(cè)為特征的時(shí)代,教育研究的思維方式與工作方式也發(fā)生了重大變革。首先,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人們要分析與某事物相關(guān)的所有數(shù)據(jù),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數(shù)據(jù)樣本;其次,人們要習(xí)慣于接受數(shù)據(jù)的紛繁復(fù)雜,而不是追求數(shù)據(jù)的精確性,最后,人們的思想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人們不再探求難以捉摸的因果關(guān)系,轉(zhuǎn)而關(guān)注事物的相關(guān)關(guān)[12]。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這三個(gè)重大的思維轉(zhuǎn)變必然也在教育研究思維中體現(xiàn)出來。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獲得海量信息已經(jīng)變得非常容易,此時(shí),如果繼續(xù)固守?cái)?shù)據(jù)收集和分析技術(shù)落后時(shí)期采用的隨機(jī)取樣來進(jìn)行教育研究就極不合時(shí)宜了。在MOOC中,動(dòng)輒上萬的學(xué)生群體這一巨型樣本為教學(xué)規(guī)律、學(xué)習(xí)規(guī)律等的深層次研究創(chuàng)造了可能。“樣本=總體”的全數(shù)據(jù)模式,徹底改變了教育研究的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正如《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一書中所提到的,社會(huì)科學(xué)是被“樣本=總體”撼動(dòng)得最厲害的學(xué)科[13]。同時(shí),數(shù)據(jù)的價(jià)值是其所有可能用途的總和。數(shù)據(jù)的價(jià)值不會(huì)因?yàn)樗氖褂枚鴾p少,數(shù)據(jù)是可以被不斷處理、不斷創(chuàng)新的。大數(shù)據(jù)創(chuàng)新沿著“數(shù)據(jù),大數(shù)據(jù),分析和挖掘,發(fā)現(xiàn)和預(yù)測(cè)”的方向發(fā)展,這必將影響教育創(chuàng)新[14]。
2.4 教育的民主化與國(guó)際化
網(wǎng)絡(luò)的出現(xiàn),大大提升了教育領(lǐng)域的民主化與國(guó)際化水平。世界各國(guó)的教育者及教育機(jī)構(gòu)在教育的發(fā)展變革中,一直在不懈努力著。2001年,麻省理工學(xué)院開放課件項(xiàng)目啟動(dòng);2002年,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舉行專題論壇,將開放課件發(fā)展到開放教育資源,并界定其內(nèi)涵;2003年,麻省理工學(xué)院開放課件項(xiàng)目正式發(fā)布500門課程,同年,我國(guó)啟動(dòng)精品課程建設(shè)項(xiàng)目;2004年,猶他州立大學(xué)啟動(dòng)USU OCW 項(xiàng)目;2005年,開放課件聯(lián)盟(OCWC)成立,開放教育資源研究受到各國(guó)關(guān)注;2006年,英國(guó)開放大學(xué)啟動(dòng)實(shí)施 OC I項(xiàng)目,后更新為 Open Learn項(xiàng)目,成為第一個(gè)啟動(dòng)實(shí)施開放教育資源項(xiàng)目的遠(yuǎn)程教育機(jī)構(gòu);2007年,MIT OCW提前一年實(shí)現(xiàn)發(fā)布1800門課程資源的目標(biāo),啟動(dòng)面向高中階段學(xué)生的Highlight School項(xiàng)目,同年,我國(guó)累計(jì)發(fā)布國(guó)家級(jí)精品課程約1800門,“國(guó)家-省-校”三級(jí)精品課程體系形成;啟動(dòng)第二期精品課程建設(shè),規(guī)劃建設(shè)國(guó)家級(jí)精品課程 3000門;2008年,開放課件聯(lián)盟成員、共享課程資源的數(shù)量快速增加,影響進(jìn)一步擴(kuò)大,同年,誕生第一門MOOC課程;2010年,港臺(tái)以及大陸志愿者將MIT等發(fā)布的視頻公開課翻譯為中文,解決了語(yǔ)言瓶頸,國(guó)外視頻公開課受到國(guó)內(nèi)高校學(xué)生及社會(huì)學(xué)習(xí)者的追捧;2011年,教育部啟動(dòng)視頻公開課建設(shè)工作,5月,開始組織39所“985”高校申報(bào)首批視頻公開課[15],11月,由北大、清華等18所知名大學(xué)建設(shè)的首批20門“中國(guó)大學(xué)視頻公開課”免費(fèi)向社會(huì)公眾開放(視頻公開課[16];2011年底至2012年,Udacity、Coursera、Edx三大平臺(tái)成立,MOOC井噴式發(fā)展,同時(shí)國(guó)內(nèi)高校也開始與三大平臺(tái)合作,推出系列MOOC課程。短短十余年時(shí)間,世界教育領(lǐng)域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當(dāng)前社會(huì)中的學(xué)習(xí)者,只要有學(xué)習(xí)的需求,就可以不受限制地獲得世界一流高校提供的免費(fèi)課程。正如MIT在其公開課主頁(yè)上所寫的“讓億萬個(gè)體都達(dá)到他們的潛能”,體現(xiàn)了MIT完全開放、充分共享、回報(bào)社會(huì)的理念。從開放課件、開放資源、精品課程、視頻公開課,一直到MOOC,這一系列變革,進(jìn)一步降低了學(xué)習(xí)者獲取優(yōu)質(zhì)學(xué)習(xí)資源的門檻,并在世界范圍內(nèi)實(shí)現(xiàn)了學(xué)習(xí)資源的開放和共享,推動(dòng)了教育的民主化,踐行了教育的國(guó)際化。這是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教育所追求的,也是世界各國(guó)教育機(jī)構(gòu)應(yīng)該承擔(dān)的責(zé)任與義務(wù)[17]。
3 MOOC面臨的挑戰(zhàn)
盡管MOOC在2012年發(fā)生了井噴式發(fā)展,受到了國(guó)內(nèi)外教育者、教育機(jī)構(gòu)、企業(yè)等的高度關(guān)注與參與,但是,MOOC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依然面臨一系列挑戰(zhàn)。比如超高的輟學(xué)率、考試中的剽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盈利模式、平臺(tái)等都是MOOC發(fā)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對(duì)于這些問題,很多專家學(xué)者已經(jīng)進(jìn)行了研究。除此以外,MOOC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發(fā)展還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約。
3.1 語(yǔ)言障礙
雖然MIT在2001年就啟動(dòng)了開放課件項(xiàng)目,2007年實(shí)現(xiàn)了提供 1800門課程的目標(biāo),但是,直到2010年,這些開放資源才以視頻公開課的形式為部分國(guó)內(nèi)學(xué)習(xí)者熟知并廣泛傳播。其中原因主要就是因?yàn)檎Z(yǔ)言障礙。在MOOC逐步向世界擴(kuò)張的過程中,語(yǔ)言障礙是其面臨的首要挑戰(zhàn)。其實(shí),如果MIT真的如其所說,追求世界范圍內(nèi)的學(xué)習(xí)資源完全開放、完全共享,作為世界上的人口大國(guó)經(jīng)歷近十年未對(duì)該項(xiàng)目給予足夠重視與利用,這也體現(xiàn)出該項(xiàng)目在設(shè)計(jì)之初對(duì)這一問題的考慮欠充分。在2012年MOOC的井噴式發(fā)展中,商業(yè)運(yùn)作參與到 MOOC的實(shí)施中來,這必然有助于解決語(yǔ)言障礙,如至少可以在微視頻中加入不同語(yǔ)言字幕,同時(shí),隨著技術(shù)的發(fā)展,在線同聲傳譯軟件的發(fā)明和完善,也必將使這一問題逐步獲得解決。我國(guó)的MOOC課程如果著眼于未來占領(lǐng)國(guó)際市場(chǎng),當(dāng)前在資金允許的條件下,可以嘗試多字幕形式進(jìn)行教學(xué)傳遞。
3.2 新型教學(xué)模式的創(chuàng)新研究
從MOOC的類型來看,MOOC分為cMOOC與xMOOC。其實(shí),xMOOC中所用的教學(xué)模式我們并不陌生。它是基于行為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的以教為主的教學(xué)傳播模式。盡管xMOOC是基于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有學(xué)生的互動(dòng)、探究,但是,這些依然不能改變xMOOC教學(xué)模式的本質(zhì)。在xMOOC中,優(yōu)秀教師、強(qiáng)大的教學(xué)輔助團(tuán)隊(duì)、資金實(shí)力雄厚的公司團(tuán)隊(duì)與運(yùn)作等,這一切使以教為主的教學(xué)模式中的分析、組織、傳遞、評(píng)價(jià)等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的優(yōu)勢(shì)都盡量發(fā)揮到了極致,最后以xMOOC的形式通過網(wǎng)絡(luò)向世界范圍內(nèi)的學(xué)習(xí)者傳遞。以教為主教學(xué)模式的確定性為xMOOC的井噴式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面對(duì)世界范圍內(nèi)的學(xué)習(xí)者和眾多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盡管xMOOC在未來的發(fā)展過程中依然需要不斷完善,但是以教為主教學(xué)模式的前期研究成果的網(wǎng)絡(luò)應(yīng)用及xMOOC的發(fā)展為MOOC的未來發(fā)展贏得了開門紅。而未來的學(xué)習(xí)到底是什么,基于行為主義的xMOOC是未來MOOC的主流模式嗎?至少目前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 MOOC。這就是基于連通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的cMOOC[18]。連通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是由喬治·西門思運(yùn)用網(wǎng)絡(luò)思維思考學(xué)習(xí)的過程和本質(zhì)而提出的。西門思認(rèn)為連通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的主要觀點(diǎn)包括:“信息”是節(jié)點(diǎn),“知識(shí)”是連接,“理解”是網(wǎng)絡(luò)的凸顯特性;學(xué)習(xí)者通過“路徑尋找”和“意義建構(gòu)”對(duì)知識(shí)領(lǐng)域進(jìn)行探索和協(xié)商;學(xué)習(xí)者通過人工制品來表征自己對(duì)知識(shí)的理解。除了具備MOOC的開放、共享、大規(guī)模、在線、免費(fèi)等共同特征以外,cMOOC的主要特征還體現(xiàn)在基于社交網(wǎng)絡(luò)的互動(dòng)式學(xué)習(xí)、非結(jié)構(gòu)化的課程內(nèi)容、注重學(xué)習(xí)通道的建立、學(xué)習(xí)者高度自主、學(xué)習(xí)具有自發(fā)性等特點(diǎn)[19]。盡管包括西門思本人也進(jìn)行了 cMOOC的嘗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主要特征中隱含著的諸如專家、學(xué)習(xí)者在巨型參與網(wǎng)絡(luò)中的有效互動(dòng)、學(xué)習(xí)資源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及共享方式、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支持系統(tǒng)構(gòu)建等依然是制約 cMOOC發(fā)展的因素,同時(shí),就連通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本身,在人們逐漸更多地基于網(wǎng)絡(luò)開展學(xué)習(xí)時(shí),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的自組織、他組織等規(guī)律,還需要不斷地發(fā)現(xiàn)與完善。
3.3 世界名校的教育壟斷
正如約翰·丹尼爾在其文章中提到的,各個(gè)國(guó)家的高校積極加入MOOC,似乎并不是為了更好地服務(wù)于學(xué)生,而是擔(dān)心蒙受經(jīng)濟(jì)損失。從領(lǐng)導(dǎo)者的角度來看,高校參與MOOC開發(fā)的動(dòng)力不是為了經(jīng)濟(jì)利益而是害怕落伍[20]。依托世界名校及知名教授團(tuán)隊(duì)、充足風(fēng)投資金支撐的MOOC,只要克服認(rèn)證這一障礙,MOOC就有可能打破傳統(tǒng)的打包式大學(xué)教育,同時(shí)極大地降低國(guó)內(nèi)和世界范圍內(nèi)高等教育成本,借助于MOOC,不管是主動(dòng)還是被動(dòng),世界名校的教育壟斷正在逼近。
3.4 英語(yǔ)國(guó)家的文化入侵
置于標(biāo)準(zhǔn)英語(yǔ)的背景下,實(shí)現(xiàn)對(duì)其他文化的尊重與公平對(duì)待,這不過是一個(gè)美好的愿望。
隨著社會(huì)的進(jìn)步、網(wǎng)絡(luò)的發(fā)展,個(gè)體在社會(huì)政治、文化、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普通民眾的話語(yǔ)權(quán)、參與權(quán)正在逐步加大,因此,權(quán)利對(duì)于學(xué)校的控制正在逐漸消弱。同時(shí),教育也把目光聚焦于如何在世界發(fā)展過程中建立自己位置。如MOOC,期望通過提供免費(fèi)、開放、一流的課程,實(shí)現(xiàn)教育的明主、公平、共享。但是,MOOC卻無法改變本國(guó)、甚至世界范圍內(nèi)弱勢(shì)階級(jí)客觀上的受教育機(jī)會(huì)不平等和差異性的現(xiàn)狀。語(yǔ)言本身具有自身的價(jià)值、傳統(tǒng)和世界觀,而語(yǔ)言中所傳達(dá)出來的意義也一定會(huì)傳達(dá)各族文化的價(jià)值、傳統(tǒng)和世界觀[21]。在某種程度上,世界名校所提供的MOOC,對(duì)學(xué)生割裂于情境之外認(rèn)知過程的關(guān)注在最終意義上可能會(huì)否定學(xué)生本土文化和語(yǔ)言的價(jià)值, MOOC名校、名師、知名團(tuán)隊(duì)等光環(huán)掩蓋了其對(duì)來自從屬文化學(xué)生事實(shí)上的不公平與不公正對(duì)待。正如北京教育科學(xué)研究院教育信息中心的唐亮在其《MOOC熱下的冷思考》中提到“文化侵蝕之憂”時(shí)所說,如果我們還沒有認(rèn)清 MOOC的本質(zhì)和實(shí)際效用便全盤接受,將其當(dāng)做萬能藥采用,便可能在潛移默化、不知不覺中丟掉本民族、本文化中的思維習(xí)慣以及教學(xué)方法[22]。
4 結(jié)語(yǔ)
MOOC,集合了教育研究、技術(shù)研究的新成果,結(jié)合良好的商業(yè)運(yùn)作,強(qiáng)勢(shì)地進(jìn)入教育領(lǐng)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大數(shù)據(jù)支撐下的MOOC教育研究必將更快取得突破性的研究結(jié)果,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MOOC的突破與挑戰(zhàn),必將使每個(gè)向往學(xué)習(xí)的人都能接受到高質(zhì)量的、免費(fèi)的教育,這又何嘗不是教育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