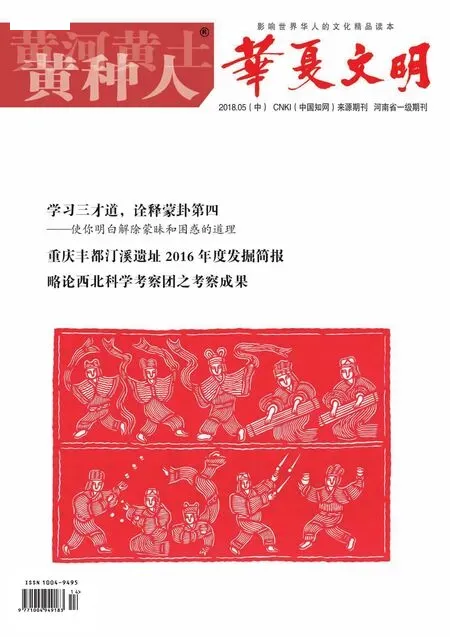文化遺產保護中土地利用的歷史、困境與思考
□崔天興
文化遺產保護理論有兩種,即唯美主義保護理論和科學保護理論,這兩種理論都著眼于保護和恢復對象的完整性。唯美主義保護理論,以美學完整性為核心,主張應盡量保存和修復,并同時保存藝術品上的歷史印記。而科學保護理論,則強調自然科學在保護中的應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它被認為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可行的保護方法,而非科學的方法逐漸被淘汰[1]。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文化遺產所在地的人口、土地、資源、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矛盾加劇,給遺產保護帶來了很大沖擊,文化遺產所承擔的壓力和風險不斷加大。目前我國實施的文化遺產保護,多偏重對文物本體的研究,對文化遺產保護是否能順利落實,并得到人們的認可,缺少必要的關注。文化遺產保護單單依靠技術路線,往往是花費頗多,保護效果卻很難令人滿意。鑒于此,學術界對文化遺產載體,尤其是大遺址所在的空間和土地利用規劃,做了探討和研究,如城郊大型遺址土地利用風險分析[2]、大遺址區土地利用管理分析[3]、古村落型旅游地土地利用研究[4]、城鎮化進程與文化遺產保護[5]等。但這些分析僅僅是局部技術、案例分析,很少從文化遺產保護中土地利用的經濟角度出發,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價值方法進行理性的系統的討論,因此本文就文化遺產保護中土地利用的歷史、實踐及困境作一粗淺探討。
一、土地利用的歷史和實踐
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土地利用問題與新中國建設進程密切相關,每一次建設高潮,既是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得以深入的機會,也是文化遺產被破壞的厄運。
20世紀50—80年代,在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基礎上獲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完成了從文化歷史考古學向全面復原古代社會生活的轉變:田野發掘和調查遍及全國,西安、洛陽、安陽、鄭州、長沙、南京、廣州、成都已經成為考古發掘的重要據點[6]。如三門峽水庫建設,發掘了河南三門峽廟底溝與三里橋遺址,陜西西安半坡遺址,陜西華縣元君廟、泉護村遺址,以及陜西華陰橫鎮遺址等,建立了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到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但因為當時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觀念淡薄,考古遺址被發掘后多被回填或者破壞,能保存下來的,往往僅是一紙文字。此外,當時的政治因素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也帶來一定的影響,如北京舊城的改造問題。
20世紀80-90年代,文物保護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設的矛盾還不突出。1981年開始的第二次全國性文物普查,除了對已知的考古遺址進行了更加詳細的調查以外,還新發現了數以萬計的各個時期的遺址,并在這個基礎上著手編輯和陸續出版多卷本的《中國文物地圖集》。1982年公布了我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我國的田野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規模不斷擴大,開始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治理軌道。
這個時期,為配合長江三峽水庫和黃河小浪底水庫等許多工程建設,組織了全國規模的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工作。對這一階段的工作,嚴文明先生認為:“我們的田野考古工作既要注意配合工程建設,又要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來選擇重點,必要時還可以作一些主動性發掘。這一政策不但有效地解決了工程建設和保護古跡的矛盾,而且大大加速了考古學科的發展,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學術問題。 ”[7]
2000年以來,文化遺產被破壞事件時有發生,并造成了若干公共危機事件。究其原因,除了城鎮化建設加速,還包括國家基本建設的提速,如南水北調工程,覆蓋全國的高鐵線路、高速公路等。根據遺址所在區位,學者將遺址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位于經濟發達的城市 (郊區);第二類處于經濟欠發達的農村;第三類分布在遠離人類經濟活動的偏遠地區。區位差別引致大遺址保護難度出現分異,其中城市化的脅迫作用使得地處城市郊區的一些大型歷史遺址保護困難最大。劉衛紅總結其特征為:目前文化遺產保護土地利用模式的主要問題,保護用地偏少,農業用地結構變化大,建設用地和工業用地擴張迅速[8]。
對文化遺產被破壞的社會因素,有學者歸結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1)城鄉建設發展造成的破壞;(2)基礎設施建設破壞;(3)不合理的旅游開發導致的破壞;(4)社區居民日常生產生活破壞等。有些破壞甚至是毀滅性的,使大批遺址或遺跡不復存在,遺址包含的文化信息消失殆盡。典型的如漢長安城遺址、唐十八陵遺址、秦雍城遺址、北京金中都遺址、洛陽大遺址群等。
城鎮化進程加快使得文化遺產保護和城鎮化開發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使得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傳統建筑被無情摧毀,一處處文物保護單位被拆除破壞。使得一些城市在經濟建設、房地產開發和旅游發展中,由于急功近利作祟、經濟利益驅使等人為因素,采取大拆大建的開發方式,實施過度的商業化運作,致使一片片積淀豐富人文信息的歷史街區被夷為平地;由于忽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造成這些歷史性城市文化空間的破壞,歷史文脈的割裂,社區鄰里的解體,最終導致珍貴的城市記憶的消失”[9]。
文化遺產類公共危機事件,一般都是發生于城市社區之中。重要旅游景區的文化遺址公共危機事件,通常不是文化遺產利用的問題,而是空間利用不當的問題。當然,在一些偏遠地區也有文化遺產景觀被破壞事件并沒有引起公共危機,這主要是因為偏遠地方的話語權缺失,但問題依然存在,有的甚至更為嚴重。
二、文化遺產保護的土地利用困境
文化遺產保護中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是文化遺產規劃。文化遺產規劃的本質,是文化遺產所在地空間功能重新規劃。空間規劃的重要載體是土地利用方式的變革,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造成文化遺產保護中土地利用困境,思想根源在于人們把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土地利用和城鎮開發的土地利用等同起來。具體表現如下:(1)建設性破壞。新的規劃建設范圍內文化遺產全部被破壞,一般都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原則被破壞或文化遺產保護為基礎建設讓行。這是城區和基礎建設規劃內大多數文化遺產的宿命,屢遭公共危機,風頭過后依然被破壞。如鄭州商代遺址,在遺址范圍內幾乎全部都是高樓大廈,文化遺產被嚴重破壞。(2)錯位開發。錯位開發使文化遺產受到嚴重傷害。一些文化遺產及其環境面臨游客超載、錯位開發的嚴重威脅,大量游人的擁入使文化遺產地不堪重負,給文物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另外,“樓滿為患”,文化遺產所在地的“商業化”“人工化”和“城鎮化”,嚴重損害了文化遺產的原生環境,如武當山遇真宮失火事件、大理巍山古城樓失火事件等。 (3)文化遺產博物館和遺址公園建設規劃不科學。建設遺址公園、遺址博物館,符合當下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但如果文化遺產保護的土地利用方案有失偏頗,厚古薄今,盲目拆遷,不僅失去了當地社區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性,而且失去了文化遺產所代表的公平、正義原則。(4)文化遺產社區“孤島”。如秦始皇陵、殷墟、高昌古城。這些社區,不同程度上都遇到了“與社區居民原來生活習慣和社會關系、空間文化景觀嚴重沖突,從而導致文化景觀單一化、門禁化、與以社區為代表的社會階層隔離”的困境。不能使文化遺產社區居民共享社會發展的多層次成果,反而造成社區居民生活不便[10]。鄉村文化遺產大遺址保護的最大問題在于過高的經濟投入,卻無明顯的社會效益,一旦資金、人員等方面投入乏力,就會形成保護倒退的局面。
因此,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土地利用一定要進行充分的科學論證,綜合考量,系統分析決策實施的社會影響和潛在的社會風險,同時分析相關居民、群體、社區、歷史文化遺產等諸要素,做出合理的評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公共政策視角看,土地利用規劃是政府為解決“市場失靈”、借助于行政力量對土地利用進行干預的政府行為,其目標是在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互平衡基礎上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從而要求遺址使用的社會評價兼顧公平、公正、科學。
社會公平。土地利用規劃是對不同區域、不同部門土地資源占有的一次再分配,在分配過程中應貫徹公平、公正原則。在規劃過程中指標的不合理分解,可能造成中心城市大量占用偏遠地區指標來發展自身經濟,使偏遠地區喪失公平發展經濟的機遇,造成人們享受經濟福利差距的過大。
社會公正。土地利用規劃的編制和實施,應當在信息公開的條件下允許公眾參與,這樣才能在社會分層多樣化、公眾需求多樣化的情況下,提高規劃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減少規劃實施阻力,保證規劃目標的順利實現。土地利用規劃本身的信息公開程度和公眾參與程度,都是社會公正原則的具體表現,并對其他社會環境產生積極影響。
區域居住結構和布局科學。作為區域土地資源的時空安排措施,土地利用規劃對各區域居住用地的結構和布局都有明確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居住社區未來的發展方向,并基本決定居住區域內的社團活動類型、規模和居住區域內政府組織機構的數量、形式以及其他一些社區制度的環境。
文化遺產保護的土地利用歷史表明,文化遺產保護需要進一步從法律法規入手,完善文化遺產行業法律,使文化遺產保護有法可依,文化遺產得到可持續保護、研究。摒棄文化遺產保護中以成本與收益核算為代表的偽經濟理性,樹立以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為本位的文化理性,從而促進過去、現在、未來的傳承和持續發展。
國家已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現代文明治理體系。2016年,中央文明辦在《關于商請將文物工作納入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的函》復函中表示,把文物工作作為文明城市創建的重要內容,納入文明城市測評的指標項目,強化對文物工作的指標要求。并協同國家文物局相關部門,就破壞文物本體及周邊環境的重大文物違法案件、文物建筑火災事故、盜竊盜掘文物案件和不可移動文物大規模消失情況做專門研究,納入“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動態管理措施”的制訂過程。
作為人類文明的遺產,歷史文化承載著一定的文化和歷史價值,是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是當今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源。在土地利用規劃制訂實施中,應該把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東西保留下來,融入新時代的精神風貌,保障歷史文物社會效益的持續發揮[11]。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希爾斯在其專著《論傳統》中指出:“傳統”一詞拉丁文為traditum,意指從過去延傳到現在的事物……延續三代以上,被人類賦予價值和意義的事物都可以看作傳統。這種意義上的傳統與文化人類學所使用的“大文化”傳統是一致的。不過,“傳統”一詞還有一種特殊的內涵,即指一條世代相傳的事物之變體鏈,也就是說,圍繞一個或幾個被接收和延續的主體而形成的不同變體的一條時間鏈。這樣一種宗教、一種信仰、一種哲學思潮、一種藝術風格、一種社會制度,在其世代相傳的過程中既發生了種種變異,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題。……傳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是人類過去所創造的種種制度、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構成的表意象征;使代與代之間、歷史階段之間保持了某種連續性和同一性,構成了一個社會創造與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密碼,并且給人類生存帶來了秩序和意義[12]。
三、結語
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土地利用受政策性影響比較大,與社會實用主義理念的成本和收益核算有密切相關性。隨著經濟與城市化加速發展,文化遺產保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其中最根本的矛盾,是遺址保護與遺址區土地利用之間的矛盾。遺址保護需要土地,經濟發展也需要土地,大遺址保護的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模式的缺陷越來越明顯。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土地利用困境在于城 市遺址保護中經濟原則、便利原則的失控,因此,不能把經濟理性作為衡量社會價值的唯一標準,價值尺度應該可以多元化,國家、社會、個人層面均可把文化遺產作為價值衡量尺度來進行評判。
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碼,給中華民族的生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文化遺產的利用,原則上應以保護性研究為主,土地利用規劃要兼顧公平、公正原則;對社區居民不能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一遷了之,社區居民和形態也是文化歷史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1]比尼亞斯.當代保護理論[M].張鵬,張怡欣,吳霄婧,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23-27.
[2]陳穩亮,吳向山,駱威,等.城郊大型歷史遺址區土地利用風險分析:以漢長安城為例 [J].資源科學,2007(3):198-205.
[3]劉衛紅. 大遺址區土地利用管理分析[J].中國土地,2011(9):26-27.
[4]梁棟棟,陸林.古村落型旅游地土地利用的初步研究:世界文化遺產黟縣西遞案例分析[J].經濟地理,2005(4):562-564.
[5]單霽翔.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遺產保護[J].求是,2006(14):44-46.
[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1-2.
[7]嚴文明.走向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J].文物,1997(11):67-71.
[8]劉衛紅.大遺址區土地利用管理分析[J].中國土地,2011(09):26-27.
[9]單霽翔.城市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城市建設[J].城市規劃,2007(5):9-23.
[10]張純.城市社區形態和再生[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106-132.
[11]李鑫,歐明豪.土地規劃需要社會影響評價[J].中國土地,2010(5):54.
[12]汪丁丁.行為經濟學講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