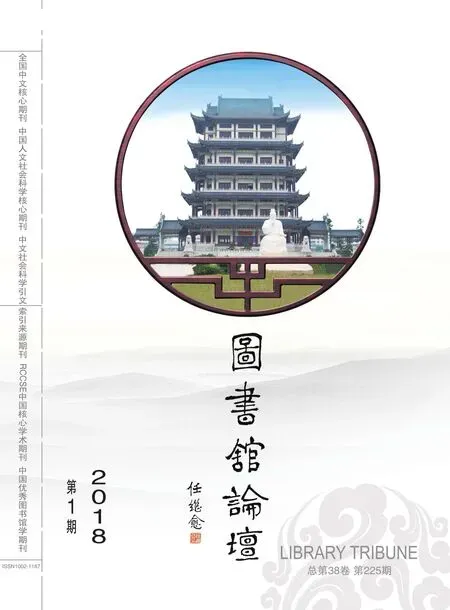我們需要怎樣的學科名
——從于良芝《圖書館情報學概論》說起
王喜明
我們需要怎樣的學科名
——從于良芝《圖書館情報學概論》說起
王喜明
于良芝教授的《圖書館情報學概論》是一部重要的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的融合之作,但其選擇“圖書館情報學”這一學科名稱來對應LIS是較為保守的。文章通過從直觀印象、詞匯選擇、詞匯意義、學科核心內容和學科發展等層面對學科名稱選詞進行探討,發現在漢語語境中,現有學科名無法完整涵蓋和準確表達LIS學科的研究任務和研究領域,而且對改善社會認知、提高學科知名度并無益處。
圖書館情報學概論 圖書館學 情報學 學科名稱 書評
1 關于《圖書館情報學概論》
2016年8月,于良芝教授新著《圖書館情報學概論》[1](以下簡稱《概論》)面世,迅速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該書被視為“國內外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圖書館情報學融合之作”,且“理論研究水平國際領先”[2]。有學者指出,該書“理清了長期以來圖書情報領域關于數據、信息、知識、作品、文獻等一直爭論不休的概念,為圖書情報領域的基礎概念框架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本書所闡釋的基本理論,作為觀察與分析人類社會涉及的信息需求、查詢、獲取、利用的現象和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和手段”[3]。
還有研究者稱該書值得“‘走出去’,不斷提升中國圖書館情報學的國際話語權!”[4]此論固屬真知灼見,我國圖情學術界也確實需要這樣一部能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一爭雄長的代表作,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本書似乎恰恰是“走進來”的代表:全書參考文獻、注釋引用的資料絕大部分是英文資料,引述、介紹的本學科或相關學科的理論絕大部分來自歐美學者,引用的案例、數據多半來自歐美國家,我國學者的相關理論和觀點的出現屈指可數;而且作者的思考方式幾乎也是西式的,如《概論》中關于印刷術的表述[1]176就是典型的西方視角。
顧燁青和張路路對《概論》進行了全面中肯的評述,也提出了“需要探討的問題”[4]。2017年4月《概論》重印,作者“最大限度地借鑒了”顧燁青和張路路指出的問題,進行了多處內容增補和修訂,包括增加書后索引及兩小節內容[1]自序6。筆者認為重印的《概論》仍有個別遺漏,比如第182頁稱“劉向、劉歆父子曾將知識分為七大類”,屬于明顯錯誤,而且與該書第60頁的表述不一致。瑕不掩瑜,作者積極訂正錯誤、完善作品的態度值得敬佩。筆者認為還有一點也應提出:《概論》沒有提到在圖情領域廣有影響的波普爾“世界3”理論,這非常奇怪。因為該理論曾深刻地影響了我國圖情界,我國主流圖情教材對該理論都有重點介紹,甚至作為理論基礎,《概論》中介紹了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的相關理論,其理論基礎正是“世界3”理論。可能的解釋是該理論影響力太大,而又與該書的知識體系不兼容,被作者有意忽略了。
2 問題的提出
由于《概論》的理論架構“已經先期在本領域公認的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4],某種意義上說已經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如何讓其思想和理論影響我國學術界。這其中一個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是關于學科名稱的問題。
從國際來看,1970年代從美國開始,本來就高度交叉滲透的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為應對信息時代來臨的沖擊和挑戰,開始走上了逐步整合之路,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學科LIS,即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我國對應LIS的翻譯可謂五花八門,《概論》選用的“圖書館情報學”只是其中之一。
雖然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在1980年代也曾出現過融合趨勢,但出于某些原因,這一趨勢在1990年代后不但事實上停止了,而且有分離的趨勢。早在2009年,于良芝教授就指出:“我國從未出現過與國外LIS完全對應的學科內容、課程體系、課題資助范圍及交流媒介。可以說,我國的圖書館與情報科學不過是國外LIS投射的影子,它缺少課程體系、交流媒介、研究社區的實際支撐,一直沒有形成實實在在的存在。”[7]而近年來在我國影響越來越大的iSchool運動,除了給我國圖情學科的變革帶來巨大的機遇以外,也引發了一些新的疑慮。已有學者對iSchool運動“去圖書館化”的傾向表示憂慮[8],而于良芝教授則關注iSchool運動對LIS的“嚴重曲解”[9]。
從一個學科整體的角度看待LIS,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學科名稱的問題。法國思想家福柯認為,話語不是對外在社會實體的某種反映,而是構成了社會實體以及事物之間的關系[10]。一個學科的名稱實際上就是這一學科與外界交流時使用最直接的“話語”,它不僅反映了該學科的主要研究領域,而且對學科發展會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國內對LIS多樣化的翻譯本身就意味著認識的不統一。
在《概論》中,作者專門用了兩節來討論“圖書館情報學的信息概念之惑”“信息社會中圖書館情報學的定位之惑”,實際上都指向了目前以LIS為學科名的研究體系和領域存在的理論困境,這在其他概論性教材中是非常少見的,體現出作者直面問題的學術勇氣。《概論》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作者不是簡單列舉不同的認識和紛爭,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定義體系(包括其中關聯的邏輯體系),在此體系基礎之上進行各種擴展與延伸。
筆者在閱讀《概論》的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的否定與再否定,在接受了該書理論體系和學術思想洗禮之后,繼承了《概論》作者的思辨精神,認為用“圖書館情報學”這一學科名稱來對應和指稱LIS所涉及的研究體系和學術領域存在問題,下面逐一進行論述。
3 從直觀印象看學科名
學科名是一個研究體系和領域的最直接代表,既是給本學科相關人員使用的,更是給學科外的人識別的,它是本學科給“外人”的第一印象,在中學生高考填報志愿或用人單位選擇應聘者等重要場合都可能產生非常關鍵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并沒有“圖書館情報學”專業,而是分為獨立的圖書館學(專科以上開設)和情報學(研究生階段開設)。在直觀印象層面,由于圖書館學專業受到“圖書館”一詞與機構“綁定”的社會習慣認知的“拖累”,長期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由于“情報”一詞的“神秘”色彩,情報學專業在某種意義上說占據了高點,但這種優勢并不是絕對的,早有學者指出這種“神秘”對“外事工作、宣傳工作、交流工作等的開展諸多不利”,并疾呼“名實不副,害莫大焉”[11]。
我國在1990年代出現的“圖情高等教育系科易名”風潮,非常重要的動因就是圖書館學專業學生和教學機構自身出于競爭劣勢的自我要求[12]。在這之前,美國一些著名的LIS學院就已經在其名稱中刪除“圖書館”字樣,而“日益嚴峻的生源、就業及研究經費競爭”也是主要的動因[9]。然而在我國,圖書館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和專業,還是依靠強大的學術慣性堅持了下來。
事實上,無論是圖書館學還是圖書館情報學,作為學科名稱,已經影響了業內外對學科領域和價值的認知。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社會科學,應該讓人見名知義,容易聯想到對應的實踐領域。《概論》中的“緒論”部分出了一道思考題:“請嘗試向一個外行人解釋圖書館情報學是怎樣的學科。”題干中寫到:“圖書館情報學是一個被社會高度誤解的學科。人們習慣于把圖書館信息職業的活動化約為圖書館活動,又進一步把圖書館活動化約為‘借書還書’活動,因而很奇怪為什么一個借借還還的活動需要一個學科的支撐。”[1]11該題已經明白無誤地點出了學科名稱帶來的負面效應。
《概論》給“圖書館”賦予了包含更廣的新定義(后文另述),即使在理論上可以自圓其說,但要讓該學科人士理解和認同也頗為不易,而專家學者們對于詞匯意義的闡釋其實并無助于扭轉外界的習慣認知。初級學習者和從業者們在面對混亂的專業核心概念和指向狹隘的學科名稱時產生的迷茫與糾結,又是否真正引起過理論研究者的關切?
綜上,僅從直觀印象看,“圖書館”已經成為該學科的“負資產”,作為學科名稱中的核心詞匯并不合適。于良芝教授從改善社會認知的角度出發,也并不反對“改名”,她在另文中就說:“全新的LIS教育當然可以使用適當的品牌策略(包括為了提高社會知名度而采取的更名策略)。”[9]
4 從詞匯選擇看學科名
正如《概論》所說,LIS的中文翻譯很多,比如圖書館情報學、圖書館與情報學、圖書情報學、圖書館與信息學、圖書館資訊學。在《概論》中,作者選擇了圖書館情報學的提法,原因是:“取‘情報’而非‘信息’是因循傳統,省略‘與’或‘和’是為了簡練。”[1]6這一組合名稱看似偏正結構,實則為并列結構。所以,從詞匯選擇的角度出發,需要分別從圖書館和情報兩個詞匯出發進行討論,此時涉及的主要問題是翻譯問題和語言特點問題。
4.1 關于“情報”
在《概論》中,除了學科名之外,情報已經完全被替換為信息,從學科名稱派生的職業則稱為“圖書館信息職業”。書中第一章介紹了一系列學科基本概念,而理論上的核心詞匯“情報”并未出現。通觀全書,情報一詞完全符號化,作為信息的同義詞,自身在書中并沒有專門的定義。事實上,被作者一筆帶過的正是所謂“世界情報學史上頗具中國特色的概念之爭,即情報與信息概念的討論”[13]。
早在1980年代初,情報與信息之辯就已經開始了,而且在1992年9月國家科委作出用信息替代情報的決定之后,這場爭論逐漸達到高潮。相關論述很多,如姚健[14]、沈固朝[15]等學者的文章,本文僅就一些他人較少注意到的問題進行簡要介紹。
“情報”一詞是來源于日本的外來詞[16]288,被引入我國之初主要作為軍事術語使用[17]。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科技等其他存在對抗性活動的領域逐漸引入情報一詞,比如大約從1930年代起,我國曾出現過許多以情報命名的刊物,如《每周情報》《南洋情報》《敵偽經濟情報》《國際貿易情報》《世界政治經濟情報》[18-19]。在解放戰爭后期,中國人民銀行冀南分行曾編印過一份名為《經濟情報》的刊物[20]。1956年國家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該年10月中國科學院成立科學情報研究所,許多人認為當時是把俄語“Информация”(基本等同英語information)一詞翻譯為情報,并導致了后來“幾十年文字語義混亂”[21]。還有一種說法是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效仿日語的做法,把information翻譯為情報[22](經查《郭沫若年譜》[23],郭曾在情報所成立儀式上講話,但講話內容暫闕)。筆者認為這兩個說法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關于郭沫若“定名”說,除了郭與日本深厚的淵源這一個人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當時“信息”一詞的含義和情報工作實際需要相差較遠。
詞匯含義會隨著時代的發展發生變化,而翻譯很難實現兩種語言中的詞匯完整對應。這從英語詞匯“information/intelligence”和漢語詞匯“信息/情報”對譯的歷程中就可以明顯看到。“不論是漢語‘信息’還是英文‘Information’,起初都僅是‘消息’(Message)的意思。”[24]但在我國,“信息”和information建立聯系應該要比“情報”早很多。在1934年出版的《中華漢英大辭典》中,“信息”一詞的英文對應詞匯就包括“news”“information”,而該辭典中并無“情報”一詞[25]。而在民國時期風行幾十年的《英華大辭典》(顏惠慶主編,1908年初版)中,“information”的若干中文義項中并無“信息”字樣,與之最接近的是“消息”,反而“intelligence”的義項中有“信息”一詞。同樣,該辭典中也沒有“情報”一詞[26]。而在1950年出版的《英華大辭典》(鄭易里,曹成修主編)里,“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都包含了“消息”和“情報”的義項,“信息”一詞卻又不見蹤跡[27]。
可以說是香農的“信息論”給了“information”和“信息”改變“命運”的機會。有一個似乎未被我國圖情學界注意到的情況是:幾乎就在科學情報研究所成立的同時,1956年創刊的《電信科學》雜志第5期重點刊發了多篇與信息論有關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是《介紹信息論》[28],文中“信息”一詞反復出現。這說明當時“信息”一詞主要作為通信領域的科學術語來使用,和情報工作起步時所從事的文獻資料工作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或者說,當時“信息”一詞主要強調傳遞屬性,而“情報”一詞主要強調知識屬性和效用屬性。后來看起來所謂的“歷史的誤會”[29],在當時可能是合理的選擇。
隨著信息論的發展及其在其他學科的廣泛應用,以及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信息”一詞的內涵和影響力不斷擴大。而在我國,“情報”一詞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大,并在與國際學術話語體系逐步接軌的同時向信息的“內涵”趨近,直到“情報就是信息”[30]這一觀點開始流行,至此二者合一就近乎水到渠成了。然而,由于1992年開始的情報改信息的相關工作并不徹底(保留了研究生階段情報學的學科設置),以及我國情報學自身的一些發展特點,才留下了今天“信息”和“情報”爭論不休的局面。
雖然在我國,“信息”已經成為“information”一詞的主流譯法,許多圖情界人士也支持順應時代潮流把“情報”替換為“信息”,而且就像《概論》一書所做的,除了學科名,具體表述中絕大部分場合都完成了更替,但還有部分情報學領域的人士堅持要保留“情報學”的稱謂,并希望用“Intelligence Science”來對應我國的“情報學”,以與“Information Science”相區別,但依然存在問題:第一,雖然英語中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存在意義上的區別,但據有關學者研究發現,近年來這兩個詞“經常有相互換用的情況,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有趨同的趨勢”[31]。第二,在我國,“Intelligence Science”現在更廣為接受的對應詞是“智能科學”,目前人工智能已經成為最受矚目的科學領域,與智能科學競爭“Intelligence Science”無疑是下下之策。因此,筆者贊同《概論》中把原來翻譯為“情報”的地方全部替換為“信息”,但認為仍然在學科名中保留“情報”的提法顯得過于保守。
4.2 關于“圖書館”
“圖書館”也是一個源于日語的外來詞[16]346,其“引進之功”被歸于梁啟超和他主持的《時務報》[32],其對應的英語詞匯是“library”,似乎沒人對此有何異議,然而依然潛藏著一些問題。
從詞匯外觀看,英語是拼音文字,漢語是表意文字,英語中表示“圖書”概念的常用詞匯很多,比如book、codex、volume,而這些詞匯與表示“圖書館”的詞匯library從外觀看差別很大(當然,英語單詞library源于拉丁文liber,liber詞義也很豐富,其中就包括書的義項)。漢語則不同,即便不了解圖書館的人也能夠從字面上“望文生義”,知道這一定是與“圖書”有關的場所(館)。對于漢語來說,抽象化的名稱更便于表達和區分學科統屬,“圖書館”一詞實體意象過強,作為一門科學的名稱,其局限性是非常突出的。
更重要的是,從library到圖書館,翻譯造成了多義詞單義化,也增加了中文對LIS和圖情學科的接受和理解難度。隨便查一本英語詞典就會發現,library除了圖書館的義項(甚至都不是第一義項)外,還有藏書、收藏的唱片、電腦程序、叢書、文庫、庫(計算機學科范疇)等許多義項。而在漢語詞典中,圖書館一詞基本上只有作為“機構”意義上的一種解釋,這也是我國約定俗成的普遍認識。Library豐富的意義讓其作為一個學科名顯得游刃有余,而圖書館單一的指向讓漢語語境中的人們對其做延伸使用時就形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概論》中提到英國的一輛流動圖書車也被認定成一個“圖書館”[1]251,若在我國恐怕很多人接受不了。作者還擔心百度文庫(而非百度圖書館)等名詞也會擠壓圖書館的話語空間[1]311,而這些如果換在英語語境中,則根本不存在問題。借助翻譯,中英詞匯只能實現主要意義的對應,不能實現完整映射。
在漢語語境中,圖書館一詞意味著一所以固定建筑為外在形式的機構,這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至于“超星圖書館”之類,在圖書館學話語體系之外,一般只會視為一種借用和延伸,很少會認為其在本質上是同類事物。
其實,之前已有我國學者意識到在學科名中把library翻譯為圖書館存在的弊端,并指出日本和韓國在翻譯LIS時對library所作的靈活處理[33],但似乎并未引起我國學界足夠的注意和反響。
所以,單從詞匯選擇看,筆者認為,用“圖書館學”來對應“Library Science”存在先天不足,隨著信息社會發展,這種不足對該學科發展的束縛會越來越嚴重。如果按傳統譯法,LIS無論被翻譯成“圖書館與情報”還是“圖書館與信息”,圖書館一詞的局限性都會成為學科發展的一個障礙。
5 從詞匯意義看學科名
情報與信息之爭,表面上爭的是翻譯用詞,實際上爭的是詞匯概念和意義。目前信息是情報的上位概念這一關系已基本取得我國學界的共識。因筆者認同《概論》中信息對情報的實質替換,限于篇幅,此處不再討論信息或情報的意義,而將專門就《概論》中對“圖書館”意義的拓展進行討論。
《概論》中對圖書館進行了如下定義:“通過對文獻進行系統收集、加工、保管、傳遞,對文獻中的信息進行組織、整理、傳遞、傳播,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詢與有效獲取的實體或虛擬平臺。”[1]54這一定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圖書館與實體圖書館在概念和意義上進行區別:“從理論上說,圖書館的未來與實體圖書館的未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需要區別對待。”[1]311這也成為該書的邏輯起點。
可以說,把傳統意義上的圖書館定義為實體圖書館,把“圖書館”抽象為一種由實體圖書館、數字圖書館和其他網絡信息服務平臺等各種保障信息查詢與獲取的機構或系統共同構成的集體的符號,是《概論》為了保留“圖書館學”這一學科名稱所做的努力和選擇。然而,“學術界在定義一個專業術語的時候,想拋開約定俗成的含義,難度顯然是非常大的”[13],這也和“同一名詞術語應始終用來表達同一概念,同一概念應始終采用同一名詞來表達”的科學標準[34]相抵觸。
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圖書館”含義的抽象化會讓“場所+組織+平臺”三結合的實體圖書館更加迷失,比如口語、手語、旗語都屬于語言,但把圖書館(即實體圖書館)、數據庫、百科全書都稱為圖書館就很奇怪,也說不通。《概論》中舉了“馬車和交通工具”的例子[1]311,恰好證明了當原有名詞不能很好地指代或包含發展后的同類事物時,就需要有“層級”更高的名詞出現,以統領和指代各種下位事物的名詞。順著書中的思路,如果人類從來就沒有見識過馬車之外的交通工具,那有必要再造一個表達屬性意義的同義詞來表示馬車嗎?交通工具這一名詞不就是為了對知識進行組織歸類而產生的嗎?學術詞匯必須嚴謹規范,虛化圖書館一詞的實體意義,擴大其指代范圍,至少會讓中國人難以接受,讓該詞同時指代上下位概念,在邏輯上也會造成混亂。
然而,如果改名,也就是增加一個上位類名是一個經濟高效的方案,為什么一定要因循守舊不放呢?直觀、清晰的區分,不是比勉強的解釋和附會更容易讓人、特別是“外行”人理解嗎?或許是出于類似的考慮,同樣是追尋圖書館的本質屬性,王子舟教授提出了“知識集合”的概念,圖書館只是其中的一類,這一選擇本身與《概論》中把圖書館定義為“信息……平臺”如出一轍,但顯然概括更精煉,也便于傳播和交流。
當圖書館被從“本質”的角度定義為“信息……平臺”或“知識集合”之后,其場所和機構屬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同時下降了,此時圖書館雖有一個看似實體的名稱,但實際上是“降格”了,與其他大小不同的概念平等起來,成為信息交流活動的中間環節之一(而且據《概論》中科學交流系統圖顯示,圖書館只是整個交流系統中的一個非必備環節[1]48)。
《概論》中指出的“圖書館職業身份模糊”[1]74問題,其根本原因還是職業名稱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再回到老問題,以機構(現實存在的)命名學科和職業,其天然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相反的例子很多,比如醫院是機構,但從業者不叫醫院職業,而分醫生、護士、藥劑師、檢驗師等,統稱為醫療衛生行業,該行業從業人員也不一定在醫院工作。圖書館學——圖書館職業——圖書館員,這樣的體系過于僵化和狹隘。
由此出發,圖書館學作為LIS關注的整體學科領域的學科名稱是不合適的。從圖書館事業在科學交流系統中的位置來看,圖書館學其實不必刻意與誰合并,但也應該降低自身級別,成為整個信息管理學科體系中的一個專門方向。
6 從學科核心內容看學科名
一個學科主要研究并用于指導實踐的理論和知識可以稱為該學科的核心內容,而該學科在高等教育環節正在使用的權威教材最能體現其核心內容。本文試圖通過幾種圖情領域代表性教材的對比分析,探討學科核心內容是否與當前使用的學科名相適應。這里所選擇的教材分別是《圖書館學概論(修訂二版)》(吳慰慈、董焱編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1月),《情報學基礎教程(第二版)》(葉鷹、武夷山主編,科學出版社,2012年9月),《信息管理學基礎(第二版)》(馬費成、宋恩梅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
首先,將《圖書館學概論》與《情報學基礎教程》各章進行對比(如表1所示),發現《圖書館學概論》一書幾乎每章題目都包含了圖書館一詞,而《情報學基礎教程》則更是全部包含情報一詞,然而基本看不到二者之間有哪些部分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這對于一個號稱已經融為一體的學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表1 《圖書館學概論》《情報學基礎教程》各章對比
然后,再來對比《情報學基礎教程》和《信息管理學基礎》(如表2所示),發現這兩本教材內容有著極高的相似度,特別是傳統情報學領域關注的情報組織、檢索、服務等內容,幾乎就是直接換了個信息的名字就成為了信息管理學的核心內容,還不用說二者共用的基本理論和科學規律。這說明從“情報”向“信息”的轉變,并不是那么困難。

表2 《情報學基礎教程》《信息管理學基礎》各章對比
最后比較《信息管理學基礎》和《圖書館情報學概論》(如表3所示),發現這兩本教材的重合內容依然很多,而且也多集中在基本科學規律和實踐環節。明顯不同的是:《信息管理學基礎》更偏向于技術,并且把圖書館相關內容做了一般化處理;而《圖書館情報學概論》更偏向于哲學社會科學,并且把圖書館相關內容做了重點介紹。

表3 《信息管理學基礎》《圖書館情報學概論》各章對比
綜上,從學科核心內容角度看LIS學科名,可以看出把情報替換為信息幾乎不存在任何障礙,實踐已經走在了前面,之所以保留圖書館字樣,主要功能或只在于突出學科的特點和傳承。而在LIS框架下把圖書館相關內容與其他信息查詢與獲取平臺進行整合處理并非難事,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人有更廣的學術視野來平等看待各種信息查詢與獲取的平臺。去掉圖書館的“獨尊”地位,換來的將會是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7 從學科發展看學科名
雖然我國還沒有形成能夠與LIS完整對應的學科,但相關的研究和工作并未停止。圖書館學和情報學之間的分分合合,以及夾雜其中的爭論和分歧,都是這種探索的外在表現。《概論》直面了這些爭論,指出圖書館學和情報學融合之后,圖書館相關問題在圖書館情報學學科體系中的重要性或重要等級下降,成為“一般問題的組成部分”[1]69。但是,由原來學科名稱的簡單相加并不能真正適應學科的發展,而且從社會發展來看,學科體系也需要進行深層次整合。
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圖書館學和情報學作為同族學科,從屬于管理學大類,二者之間的密切程度要高于“圖情檔”中的檔案學。在2011年修訂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在“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之下,還增設了信息資源管理專業。而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中,圖書館學、情報學相關類目設于“文化、科學、教育、體育”大類之下,與新聞、廣電、出版等類并列,同屬“信息與知識傳播”二級類目;在最新的第五版中,“合并G25、G35圖書館學情報學體系”,“修改G25類名為‘圖書館事業、信息事業’”[35]。最新版的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沿用了這一分類方法和類名。雖然這幾種文獻編制的出發點并不相同,但在適應圖情學科發展變化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嘗試是顯而易見的。相關學科專業所在知識體系位置的變化和學科名的變化,其本質都是出于對學科性質、學科任務認識的變化。
與學科體系和學科名一起發生改變的還有直接與社會需求接軌的職業群體。《概論》指出:“信息獲取平臺的多樣化不構成對圖書館信息職業的威脅,很多平臺事實上擴大了圖書館信息職業技能的用武之地。圖書館信息職業確實是時候在強化統一身份意識的同時,在戰略上考慮如何系統地將現有圖書館的同類平臺納入自己的實踐范圍,以及如何參與其他平臺的建設。”[1]299該結論成立的前提是確實存在“圖書館信息職業”這樣一個職業,并且搜索引擎、專業門戶等也屬于并認同這一職業,如此才能合理解釋高校圖書館讀者流失的現象,好比從左手換到了右手。但問題是,《概論》也提到,從世界范圍來看,根本就沒有統一的“圖書館信息職業”的身份意識。書中說“圖書館信息職業從業人員的基本條件是接受圖書館情報學教育、以圖書館情報學作為職業活動的智力源泉”[1]58,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圖書館學專業,還是情報學專業的畢業生,都遠未構成各種網絡信息獲取平臺開發和維護的主力,這也反證了圖書館情報學如果要完整支撐(至少是占據主導地位)所謂的“圖書館信息職業”,學科體系、專業教育體系都必須要改變。
有一種頗具代表性和說服力的觀點:“圖書館行業是信息職業的重要組成”[36]163。由此看來,如果一直堅持使用類似“圖書館信息職業”之類的表述,那么該職業對應的行業大約主要還是圖書館相關組織機構,而這顯然和《概論》中希望的情況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改為“信息管理職業”,是否既能拓寬口徑,又能和信息技術職業相區別呢?
肖希明教授等專門調查研究了“美國iSchools學院的信息科學、圖書館學、情報學、圖書情報學”等學科的核心課程,指出“國內圖書情報學教育應注重結合職業能力培養需求,尤其是注重核心課程在信息倫理、政策與法規,信息安全,信息與社會,信息跨學科應用類,信息職業管理等方面的設置”[36]77。而這些內容基本上都出現在《信息管理學基礎》一書中,再考慮到其他共同的核心內容(如信息組織、信息檢索、信息服務),從學科發展角度看,我國圖情學科的整合目標是否就是已經基本成型的信息管理學呢?
8 我們需要怎樣的學科名?
從上述分析出發,筆者認為,無論是獨立的圖書館學還是情報學,僅就學科名稱而言,都存在“先天”問題,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信息社會的發展,其學科名對學科發展的不利影響將愈加凸顯。而由此二者簡單拼湊起來的“圖書館情報學”學科,無論實質性融合情況如何,僅就學科名而言,同樣無法完整涵蓋和準確表達學科研究任務和研究領域,而且對于改善社會認知,提高學科知名度并無益處。所以,整個學科體系的變革重組勢在必行,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學科名稱的問題。
誠然,要實現上述目標可謂困難重重,拋開龐大的專業學/協會體系不談,我國圖書館學界和情報學界各自的反對甚至分離的聲音都很強大,比如在圖情融合的大趨勢下,還有我國學者在呼吁“建立情報學一級學科”,但呼吁者本身也陷于學科名稱是什么和如何翻譯這一困境之中[31]。如果再考慮到某些較為強勢的專門情報學學科(如競爭情報學、軍事情報學),情報學的情況又會更加復雜。
《概論》選擇“圖書館情報學”作為學科名,除了習慣之外,其實也表達了對學科轉型的深度憂慮,“對話語力量缺乏敏感則導致我們不能洞察‘圖書館’消亡論對同名職業和學科帶來的毀滅性打擊”[1]314,或許正是其固守圖書館名稱不放的心理原因。書中還提到:“盡管從理論上說,圖書館信息職業的前景因為維系于永恒的人類信息查詢與獲取需要而擁有比較牢固的根基,但在互聯網引發的新一輪社會分工中,她確實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戰略眼光,才能鞏固自身的地位。”[1]313由此看來,作者并非沒有從更高的站位、更全面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是舍不得放棄,而為圖書館“正名”就成為該書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然而,當考慮到1980年代黃宗忠教授對圖書館所作的界定:“作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圖書館,不是具體形態的圖書館,不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具體的圖書館,而是不受時空影響的圖書館,一種科學概念的圖書館。”[37]《概論》中的“正名”很難說是理論創新,而這種跨越幾十年,仍然把概念“糾偏”作為“救命稻草”的行為,恰恰證明了概念對應名詞自身存在的缺陷。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社會科學,理論的自洽固然必要,但必須考慮到社會的普遍認知能力。
愛因斯坦曾說過,關注人類自身及其命運,必須作為所有技術努力的主要事業,從我們頭腦創造出來的,應當是人類的福祉。“科學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人類創造更好的生活。只有始終秉持造福人類的宗旨,科學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發揮自身的價值,也才能不負人類的希望與期待。”[38]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跳出本學科來思考一個根本問題,即我們是要努力守住某個“牌位”,還是要貫徹我們的學術精神和職業宗旨,去追求人類共同福祉,而無懼改變自己,破繭重生?
事實上,國內外都不乏可供參考的例子。比如,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圖情界專業協會組織ASLIB,1924年成立時的名稱是英國專門圖書館和情報機構協會,1949年與英國國際書目協會合并后改稱英國情報組織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現在看來翻譯為信息管理協會更恰當)。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ASLIB逐步調整其職能和服務,很早就放棄了專業圖書館協會的身份,并聲稱“從1924年起,我們的使命一直是開發產品與提供服務,為改變世界的管理信息的問題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案”[39]。而作為我國最重要的數字圖書館項目——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其英文名稱是China Academic Library&Information System(簡稱CALIS),中英文名稱并不完全對應,體現出名稱選擇和翻譯時的大視野和靈活性。
如果說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各自改名,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存在諸多很難逾越的障礙的話,那么作為面向信息時代的兩者融合的產物,我國的“圖書館情報學”是不是可以首先從名稱上破舊立新,亮明旗幟呢?當前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的iSchool運動正是我國圖情學科進行變革的重要契機。因為“iSchools的重要理念是擺脫‘圖書館機構為主體’,邁向‘以信息為中心’的發展道路”[36]302。
在此,本人提出對學科名變革的兩點看法:(1)作為對應LIS學科的整體學科名,情報必須用信息替換,這是一種“快刀斬亂麻”的做法[40],目前的情報和信息共用、混用現象過于突出,人為制造了交流的障礙;至于情報,可以保留在一些專門的研究領域中,比如競爭情報、軍事情報。
(2)關于圖書館一詞的處理,有兩個方案可供討論:①把圖書館改為圖書,即確定學科名為圖書信息學,也就是把現在使用最廣的LIS中文譯名——圖書情報學(筆者以各種LIS中文譯名為檢索詞在CNKI中按篇名進行檢索,圖書情報學檢出結果700多條,排名第二的圖書館情報學只有不到50條,其他更少)中的情報替換為信息。圖書信息學的譯法在包昌火[41]、繆其浩[42]、肖勇[43]等學者的論文中都出現過,其優點:一是去掉“館”字就脫離了機構印象的束縛,二是與LIS對譯基本不存在障礙,三是偏正結構便于體現主次和學科傳承及特點;缺點是依然不夠“大氣”,并不能有效解決普通社會民眾的認知問題。②棄用圖書館相關字樣,改稱信息管理學。事實上,1990年代中前期,我國圖書情報一體化的方向正是“信息管理化”,但由于一系列復雜的原因,這一進程遭遇了很大的挫折[44]。改稱信息管理學的優點:一是可以直接體現信息科學和管理科學的交叉學科特點,并且符合iSchool運動的精神;二是已經有相當的基礎,信息管理學已經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學科稱謂;三是符合信息社會發展要求,便于針對社會職業需求培養寬口徑人才;四是社會“觀感”好,容易吸引人才;缺點:一是基于當前的理論認識,從整體上看,檔案學、博物館學、出版學等都屬于“信息管理學科群”[36]166,從圖情直接轉向信管,比1990年代時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學科整合難度大;二是與LIS的名稱不匹配,不利于對外交流。
1995年11月,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托,由武漢大學牽頭組織召開了一場圖書館學與情報學博士生培養和修訂專業目錄方案的研討會,與會者建議將“圖書館學與情報學”這個一級學科擴充為包括圖書館學、目錄學、文獻學、情報學、科技情報學、社會科學情報學、編輯學、出版發行學、檔案學9個學科在內的學科群。當時為了這個新的一級學科的學科名稱,與會專家各抒己見,其中黃宗忠、倪波兩位教授提出可稱為“文獻信息學”[45](該名稱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出現并獲得不少學者的認同)。可以說以文獻信息學作為學科名稱,比筆者的兩點意見都要好,體現出極高的學術眼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該提議最終未被采用,以至于2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在使用當時提出的一個結構松散、割裂的“暫行”方案——“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而且不知道還要用多久!
最后,無論學科名如何變化,至少應做到統一稱謂,這不但有利于對內對外的學術交流,更是未來高等教育體系中調整專業設置時所必需的。而這種調整行為本身,既是時代和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也需要學界同仁齊心推動。
筆者具有15年圖書館學專業學習和基層圖書館工作經歷,并非沒有專業感情。本文不揣淺陋,只希望以一孔之見,在推動學科變革和發展車輪前行方面,獻出自己的微薄之力。至于本文提出的問題,如果能夠得到業界同仁的共同思考,那就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1] 于良芝.圖書館情報學概論[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2]《圖書館情報學概論》——圖書館情報學領域一部全新的入門性著作[N].圖書館報,2016-09-02(9).
[3]劉茲恒.大眾創新背景下的圖書館學研究[J].山東圖書館學刊,2017(1):113-115.
[4]顧燁青,張路路.一部值得“走出去”的圖書館情報學理論著作——評《圖書館情報學概論》[J].圖書館論壇,2016(12):44-53.
[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GB/T13745-2009) [S/OL].[2017-07-20].http://zy.zwbk.org/index.php?title=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GB/T13745-2009).
[6]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EB/OL].[2017-07-20].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4/201104/116439.html.
[7] 于良芝.圖書館與情報學(LIS)的使命與視域[J].圖書情報工作,2009(9):5-9.
[8] 肖希明,李琪,劉巧園.iSchools“去圖書館化”的傾向值得警惕[J].圖書情報知識,2017(1):19-25.
[9] 于良芝,梁司晨.iSchool的迷思:對iSchool運動有關LIS、iField及其關系的認知的反思[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7(5):18-33.
[10]R Keller.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 Discourse (SKAD) [J].Human Studies,2011 (1):43-65.
[11]周智佑.對“科技情報”正名為“科技信息”的看法[J].科技情報工作,1991(12):13.
[12]王世偉.關于圖情高等教育系科易名的思考[J].圖書館雜志,1993(3):12-13.
[13]成穎,孫建軍,柯青.情報學研究反思——從信息與情報的概念視角思考[J].情報科學,2011(8):1147-1153.
[14]姚健,賈桂華.英漢信息與情報概念辨析[J].情報學刊,1994(1):5-11.
[15]沈固朝.兩種情報觀:Information還是Intelligence?[J].術語標準化與信息技術,2009(1):22-30.
[16]劉正埮,高明凱,麥永乾,等.漢語外來詞詞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
[17]王存奎,王愛博,謝曉專,等.情報界定的相關基礎理論研究[J].保密科學技術,2013(9):12-21.
[18]國家圖書館.民國期刊數據庫[DB/OL].[2017-08-15]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qikan.
[19]古籍網.[2017-08-15].http://www.bookinlife.net/.
[20]經濟情報[DB/OL].[2017-08-15].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740f3c260313d141583c 869fc803747f)&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E7%BB%8F%E6%B5%8E%E6%83%85%E6%8A%A5&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us=8227934758818813080.
[21]惠世榮.結論?共識?——關于情報與信息定義討論的綜述[J].津圖學刊,1995(1):37.
[22]李彭元.從語源學看“情報”改“信息”[J].圖書館學研究,1997(5):59-60.
[23]王繼權,童煒鋼.郭沫若年譜(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138.
[24]葉繼元,陳銘,謝歡,等.數據與信息之間邏輯關系的探討[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7(3):34-43.
[25]陸費執,嚴獨鶴.中華漢英大辭典[M].上海:中華書局,1934:33.
[26]顏惠慶.英華大辭典(小字本)[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530,538.
[27]鄭易里,曹成修.英華大辭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640,649.
[28]畢德顯.介紹信息論[J].電信科學,1956(5):1-5.
[29]王萬宗.再論情報的定義與屬性[J].情報學科,1992(4):250-255,263-264.
[30]李毅.再談對情報概念的認識[J].情報學刊,1980(2):19-21.
[31]黃長著.關于建立情報學一級學科的考慮[J].情報雜志,2017(5):6-8.
[32]蔣永福.圖書館學基礎簡明教程[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19.
[33]葉繼元.圖書館學、情報學與信息科學、信息管理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4(3):11-17,23.
[34]姚健.情報概念泛化論[J].圖書情報工作,1996(1):64-67.
[35]國家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編輯委員會.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第五版)[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8.
[36]肖希明,司莉,吳丹,等.iSchools運動與圖書情報學教育的變革[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37]黃宗忠.圖書館學導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19.
[38]鞠強.探索未知、造福人類是科學的本義[J].科技導報,2014(8):7.
[39]范并思,邱五芳,潘衛,等.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圖書館學[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5.
[40]謝曉專.情報學“名不副實”的尷尬及其解決之道[J].情報資料工作,2010(3):14-19.
[41]包昌火,李艷,包琰.論競爭情報學科的構建[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2(1):1-9.
[42]繆其浩.情報觀:一個來自實踐的命題[J].圖書情報工作,2005(9):11-12,22.
[43]肖勇.我國圖書館學的學科存在與學科關系[J].情報理論與實踐,2009(9):1-4.
[44]王知津.中國圖書情報學教育20年評述[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1(2):68-72..
[45]黎盛榮.也談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定位和學科建設[J].圖書情報工作,1997(10):21-22.
What Kind of Subject Name Do We Need——Revelations from YU Liangzhi’s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ANG Ximing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ritten by Dr.YU Liangzhi,is a significant work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However,it is conservative to adopt this Chinese subject name for LIS.By exploring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name for LIS from the aspects of visual impression,lexical meaning,core subject content,and subject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at,in Chinese context,current Chinese names for LIS cannot completely cover and accurately express the research missions and fields of the subject,and then bring no benefits to improve the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popularity of LIS.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subject name;book review
格式 王喜明.我們需要怎樣的學科名——從于良芝《圖書館情報學概論》說起[J].圖書館論壇,2018(1):36-46.
國家標準(GB/T13745-2009)》中,二者同屬“人文與社會科學類”下“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一級學科[5];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制定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同屬管理學大類下的一級學科“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6]。在這兩個權威文件中,雖然大類歸屬、一級學科名稱均有差異,但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的關系是一致的。
王喜明,河北建筑工程學院圖書館館員,兼信息管理系任課教師。
2017-07-31
付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