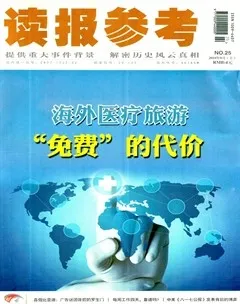七大前后的毛澤東與劉少奇
從抗戰后期的1943年到“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系是黨內最重要的一對同志關系,在,這20多年間劉少奇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
唯英雄能識英雄
在“毛周劉朱”四人中,毛澤東與劉少奇淵源最深。他們之間的淵源可以從1920年算起。那年,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漂泊四方的青年劉少奇在長沙的報紙上獲悉湖南有一個“俄羅斯研究會”組織湖南青年赴俄國勤工儉學,當即報名參加。這個研究會的實際組織者就是毛澤東、何叔衡等。當時,他們尚未直接交往。
1922年春,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劉少奇奉調回國,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當年夏天,陳獨秀派他回湖南工作,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此時的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正是毛澤東,他還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8月初,兩人在長沙清水塘一座小平房第一次見了面,這似乎是一次普通的會面,當時他們估計不會料到,20年后,他們會在延安開始建立一種持續20余年的“毛劉體制”。而當時的毛澤東無疑具有知人之明,劉少奇剛回湖南一個月,毛澤東便派他去安源領導工人運動。安源路礦大罷工的勝利成就了劉少奇的聲望,也增加了他在毛澤東心里的分量。毛澤東、楊開慧夫婦還成為了劉少奇與何寶珍的月老。1925年底,當劉少奇被湖南軍閥逮捕時,毛澤東多方組織營救。
大革命失敗后,劉少奇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先后在河北、上海、東北等地做地下工作,他提出了一套白區工作策略;毛澤東則領導農村武裝斗爭,“喚起工農千百萬”,探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他們雖然身處不同戰線,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卻是觀點一致。這段時期也是兩人備受“左”傾路線打擊的時期。毛澤東被視為“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失去了兵權,在一個破廟里養病。劉少奇與毛澤東同病相憐,屢遭“左”傾路線打擊,但因為他在工人運動方面具有特殊的才干和無可替代的作用,雖然被撤去中央職工部長的職務,卻又讓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蘇區,與毛澤東久別重逢。他們都不知道彼此受打擊的歷史情形,一直到延安后,劉少奇才向毛澤東吐露,毛澤東也向劉少奇講了他的歷史。當然,根本觀點的一致勝過千言萬語,在紅軍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毛澤東幾十年后仍然沒有忘記這重要的一票,說劉少奇的支持“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寶貴的”。
長征到達陜北后,根據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闡述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36年初,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劉少奇冒著生命危險到華北敵占區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由于“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使白區黨組織幾乎損失殆盡,當時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絡到的黨員不過30人左右。在毛澤東堅強有力的支持下,劉少奇放開手腳,僅僅半年就讓北方局的工作煥然一新,中央評價“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當劉少奇1938年離開北方局時,中共和八路軍已經成為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政黨和最強大的抗日武裝力量。
對于劉少奇的工作能力,毛澤東非常欣賞。1937年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的報告認為,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基本上是錯誤的,于是引發了爭論。毛澤東堅決支持劉少奇:“少奇對這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斗爭和處理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在華北的領導也是一樣。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干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又說,劉少奇提出的問題“基本上是對的,是勃勃有生氣的。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癥,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澤東還經常為劉少奇鳴不平:“我黨在國民黨區域工作中,不但有劉少奇同志那樣的正確的領袖人物,而且有不少類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臨時中央斥之為‘機會主義者’”“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證明了”。毛澤東甚至認為: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
這并不是毛澤東偏袒劉少奇。王稼祥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在蘇區“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證法”。陳云也在會上說:“過去10年白區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同志到白區工作后才開始轉變。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10年來的白區工作中的正確路線。”王稼祥和陳云當時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其評價是非常有分量的。
高舉旗幟的旗手
雖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由于黨內思想路線問題沒有徹底解決,組織問題也沒有提出,特別是1937年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后,教條主義一度又在黨內盛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甚至與中共中央形成了“兩個中央”的不正常狀況。當時的毛澤東經常感覺自己是孤立的。直到1938年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劉少奇在會上提出要依照“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形成一個“黨規”,這個建議無疑是針對搞宗派主義的王明,深得毛澤東的贊同。會后,毛澤東推薦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把開辟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重任交給他。
當時黨中央決定“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在劉少奇看來,發展華中的最好時機已經錯過了,但還來得及補救。當時中共在華中的力量十分薄弱,華中的日寇、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力量非常強大,毛澤東號召:“東進、東進、再東進,到敵人的后方去!”劉少奇再次受命于危難之際,提出華中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只能按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向東發展。毛澤東也全力支持劉少奇,命令華中黨政軍“一切具體部署,統歸胡服負責”。皖南事變后,劉少奇處變不驚,作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領導中共在華中建立了大片根據地。抗戰勝利后,根據毛澤東強調的要控制東北、熱河、察哈爾,劉少奇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時,又確定了“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面對國民黨搶占東北,他又提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策略,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從而轉變了中共中央東北局的戰略部署,鞏固和發展了中共在東北的力量。解放戰爭中,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華北、華中、東北三大根據地,劉少奇都為其打開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礎。正是因為全面抗戰這個大舞臺和毛澤東的重用,劉少奇在1936年至1942年這6年多中大展身手,使全黨上下看到了他過人的戰略眼光、高超的領導才能和非凡的組織能力。當時中共能人輩出,只有實際成就才能服人,這些成就為劉少奇后來居上成為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鋪平了道路。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劉少奇與毛澤東觀點一致、合作無間。這在當時并非易事。毛澤東在1943年回顧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后自己的境遇時,說:“現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時代為基礎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5個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路線的。”毛澤東非常需要劉少奇的支持,而且劉少奇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能夠透徹地批判教條主義。難怪薄一波1943年春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就問他:“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得很好,你讀過沒有?他講‘修養’,我講‘整風’,意思是一樣的。”
為了檢查土地革命后期的政治路線問題、系統地批判教條主義以及改組中央、準備召開黨的七大,毛澤東很需要劉少奇回延安幫助他。從1941年10月開始,毛澤東就給華,中局發電報:“中央決定劉少奇來延安一次,并望能參加七大,何時可以動身盼告。”陳毅等人覺得劉少奇一走會使華中“失掉中心”,但毛澤東堅持劉少奇回延安。而且,劉少奇的延安之行,毛澤東僅有關安全的電報就發了十幾封,這在黨內十分少見。
10月9日,劉少奇尚在途中,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就全文發表了劉少奇的《論黨內斗爭》一文。毛澤東親筆為此文寫了編者按語:“這是劉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于黨內斗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期間,特為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讀。”
1943年元旦,劉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楊家嶺大禮堂舉行盛大新年團拜會,歡迎劉少奇從華中歸來。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幾乎全數出席,毛澤東和朱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第二天,《解放日報》又在頭版頭條發表了劉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舉行盛大活動歡迎劉少奇的消息。這樣高規格的歡迎儀式在延安非常罕見。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精簡書記處,劉少奇提議書記處應設主席,其他兩名書記是主席的助手,書記處要能夠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工作。會議接受了這些意見,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書記處,以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這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雛形。從此,毛澤東才在黨內正式成為“毛主席”。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第一次被寫進黨章。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