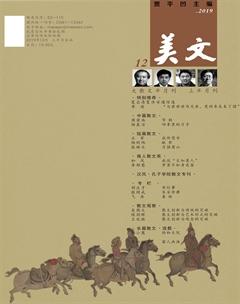散文創新與觀念的突破

王兆勝
從“五四”算起,新文學走過百余年的征程;從改革開放算起,新文學已過40載;進入21世紀,新文學也有近二十年的時光。應該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新文學具有引領作用,這在“五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改革開放初期,文學都以獨特的敏銳與理性自覺對時代起到引領作用,并取得巨大成就。但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尤其是21世紀以來,文學開始出現退守甚至滯后于社會時代發展的狀況。作為相對保守的文體,散文更是如此。在21世紀前二十年即將收官,馬上進入第三個十年之際,散文應更新觀念,發揮其獨特功能作用,成為包括詩歌、小說、戲劇等在內的文學發展的輕騎兵。
一、參與國家社會戰略發展進程
整體而言,新時期散文具有探索性、創新性和發展性,它與其他文體一起參與了改革開放的發展。不過,放在百年中國新文學特別是近二十年中國社會飛速發展的進徑看,散文具有明顯的滯后性。這主要表現在背對時代、沉溺歷史,歷史文化散文呈泛濫之勢,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視和參與不夠,更不要說關注國家民族命運和戰略發展。散文創作整體呈疏離、遠離甚至背離時代、社會、政治的趨向,在所謂的審美“向內轉”和歷史的回望中,有自我迷失甚至自我喪失的局限。未來散文發展必須突破這一瓶頸,成為時代、社會、文化、精神的風向標和巨大引擎。
與時代、社會、政治同呼共吸,直接參與到國家的戰略發展進程,這是散文創新的基本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論是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還是楊朔、劉白羽、秦牧的為祖國歌唱,都是站在時代制高點為國家和人民發聲。然而,新時期以來,“楊朔模式”受到質疑甚至批判,散文與政治的關系受到挑戰,宏大敘事不斷貶值,于是出現個人化敘事、碎片化寫作,甚至零度寫作,而無價值判斷則成為不少作家學者的追求。一方面,散文不是關注現實,而是熱衷于歷史書寫;另一方面,知識寫作代替價值追問,于是書齋化、一地雞毛式的散文大行其道。與有限的關注現實的散文相比,太多的散文缺乏現實感、時代性、政治意識,而進入一種名之為“審美”個性化的書寫。有的散文甚至羞于談論現實主義、宏大敘事和政治意識。這必然違背“文學當隨時代”的基本準則,也會失去讀者,喪失文學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許這些遠離現實和時代的散文,在藝術技巧上有所探索創新,也有借古鑒今和吸取社會人生智慧的功用;但很難產生楊朔等人散文的巨大影響力,因為不接地氣,人民性不足,國家、民族、社會意識不強。因此,要真正獲得觀念創新,散文必須面對現實和時代,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于其外,以文學的獨特方式和魅力彰顯時代、社會、政治的風采。
關注社會重大問題,尤其是對人類命運要有思考,這是散文觀念創新的要義所在。讓散文關注社會現實并不是無所作為,或作表面文章,而是要真正有穿透力,為時代、社會把脈,尤其能把握國家、民族、人類的發展命運,這是時代賦予敏感的文學的特殊使命。目前,歷史文化散文、鄉土散文、學者散文往往都缺乏這樣的理性自覺,也難對時代和社會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預想與構想,也就不可能指出前行的方向。比如,不少鄉土散文仍醉心于傳統文化的審美趣味,對都市文明采取簡單、機械甚至非理性的拒斥和反對態度;底層寫作雖有一定的問題意識,但缺乏現代意識、方向感和預見性,往往被細部和現象困擾,在消極寫作中充滿唉嘆、抱怨、否定和絕望。今天,我們特別缺乏能為這個時代和社會把脈的散文,尤其缺乏以超前性眼光穿透時代和社會,并給國家、民族、人類提供價值參照和指明進路的散文。從這個方面說,這是散文最大的遺憾和失職。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既需要理性自覺和使命擔當,又需要認知能力水平和文化自覺意識,更需要有前瞻性眼光和超常的智慧。
充滿積極進取、奮發有為、明朗健康的時代氣息,而非低沉悲觀甚至虛無主義的個人寫作,這是散文觀念更新的理想狀態。在新文學初期,像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李大釗的《青春》、魯迅的《救救孩子》等都是熱情洋溢、流光溢彩的政治文化散文,直到今天它們仍不失時代風骨。新時期特別是21世紀以來,我們缺乏這樣的散文作品:能把握時代脈搏、有現實主義分量、充滿浪漫主義理想、震撼人的靈魂。相反,更多的是站在“小我”甚至一己感受所進行的自我表達。真正有創新性的散文,應通過“個我”的鼓與呼,穿越現實的大地天空,在時代回音壁上回蕩著關于國家、民族、人類的思考的最強音。
我不反對在藝術技巧上進行創新,也不反對將歷史作為鑒鏡,甚至用傳統文化的自信與優雅反思現代化局限亦無不可。但無論如何,散文離不開時代和社會,也不可能與政治無關,更不能無視現實存在的重要重大問題,還不可不顧國家民族和人類的發展走向。至于如何以審美方式進行反映,而不是簡單地進行時代與政治的表達,這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關鍵問題。
二、以“天地之道”修正“人的文學”
縱觀一個世紀以來的新文學,我們基本遵循的是“人的文學”觀,即堅信“人是萬物的主宰,是天地的精華”。應該說,“人的文學”觀對突破中國傳統文學文化對“人”的異化,是有益也是有價值的;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失去了對于天地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將人的個性、欲望強調得無以復加,致使文學受到異化。散文寫作也是如此,在“人的文學”觀念下,我們很難真正獲得創新性發展。
過于強調“人的文學”,忽略天地自然尤其是天地之道的規約,極易導致散文創作的傾斜,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將筆力主要放在寫“人”上,忽略了更廣大、豐富、復雜的天地自然。其實,天地宇宙包羅萬象,是遠不能用“人”的認知進行解釋和抵達的。如天地萬物就無法在“人的文學”觀底下得到更好的描寫和闡釋,這也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散文貧乏無力的原因。即使有的散文寫“物”,往往也多用擬人手法,難以真正潛入其內在本性,理解其獨特價值魅力。
其次,難以抵達天地自然的道心,即“萬物有道”的層面。其實,即使是一塊石頭,它也有“道”存矣,不要說其生命是人所無法比擬的,就是它的智慧也值得人類好好學習。因此,從“物”身上能格物致知,進入“道”中,并獲得智慧,這是今后散文觀念創新應努力的方向。以杜懷超為例,他曾寫過一句話:“每一棵植物都是一盞燈,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它的光照里。”這是句智慧語,是超越了“人的文學”觀,進入天地大道的全新感悟。可惜,當前這樣的散文太少了。
再次,缺乏天地情懷,尤其失去了謙卑與敬畏之心。在“人的文學”觀牽引下,許多散文的個人主義思想膨脹,有的甚至成為暴力化寫作,溫暖、仁慈、博大、優雅等也就無從談起,這勢必影響散文的境界與品質。有了天地情懷的散文寫作則不同,它會進入綠色的審美狀態,也成為一個帶著謙卑與愛心的智者。如朱以撒的散文《進入》是寫釘子的,他發現我們目及所到之處,樹木、墻壁、木板上都被釘上釘子,于是為萬物感到傷痛。最重要的是,朱以撒將矗立的高樓大廈比成釘子,它釘在大地之上,于是發出了悲憫的感動。還有,寫宣紙、墨汁、毛筆以及與人心的融匯、對話與創造,朱以撒散文都進入一種天地境界,于是超出了“人的文學”觀,有了新的觀念變革。遺憾的是,整體而言,當下散文仍受制于“人的文學”觀,即使是諸多生態環保散文也不例外,它們在天地自然尤其是“大道”面前多是失語的,也是缺乏生命的智慧的。
在此,最重要的是,應辯證理解“人的文學”與“天地大道”的關系,以突破當前散文的困境,從而解開許多散文存在的死結。“人的文學”強調的是人性解放和個性解放,“天地情懷”重在天地自然之道對人的規約,二者辯證融通后的再造,才是未來散文觀念突破創新的要點所在。
三、將人類健全幸福作為宗旨
中國古人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又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理想,講的都是由“小我”升華為“大我”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們的散文也包含著這種精神,像“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誰是最可愛的人》對英雄的贊頌,都可作如是觀。然而,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許多散文的境界和品位開始走低,呈現出“小我”被放大,“大我”貶值的不良傾向。
在不少著名散文家那里,有的斤斤于個人得失,停留于歷史暗角的書寫和關于“小人”的評說不能自拔;有的進入百無聊賴的阿貓阿狗描摹,失去了最基本的作家情懷和人文精神;有的遵循叢林法則,相信強力與蠻橫為天理,于是使散文充滿暴力情結;有的形成金錢至上和權力崇拜,從而陷入世俗化與虛假的散文寫作;還有的被淹沒于歷史的碎片與邏輯概念的纏繞,更有以創新和突破禁區為名渲染性愛,于是使散文變得呆滯死氣。總之,在散文家自己內心變得封閉與粗劣,于作品也就日益下滑甚至墜落,散文的異化也就在所難免。
其實,橫亙于新時代散文創新面前的最大障礙還是作家自己,即他們如何從自我修養和自我革命開始,擺脫低級趣味和世俗功利,進入“大我”、民族精神、國家發展和人類命運的思考。如有的底層散文寫作,在敘述經由自己努力,從煤礦工人變為作家的苦旅中,自有一種值得珍視的奮斗精神;然而,當作者對這種角色轉換懷有慶幸,卻看不到礦工勞作的意義,甚至以擺脫其困境為榮和快心之事,那就被“小我”甚至“私心”束縛了,作品的價值也就大打了折扣。又如有的散文寫到敦煌壁畫的輝煌燦爛不被重視,于是發出急切召喚:“我國的作家、畫家、藝術家和考古學家們,你們都在哪里呵?你們難道聽不到大西北在對你們的殷殷呼喚嗎?你們難道看不到古西域藝術在向你們頻頻招手嗎?你們都躺到哪個鬼旮旯去了?”這種吁求當然無可厚非。然而,作者又說,當她看到日本學者井上靖在《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西域敦煌的文章,卻有這樣的話:“他老人家愜意了,我卻窩下了心病。”(王英琦:《大唐的太陽,你沉落了嗎?》)這個“心病”就是民族主義情結在作怪,是缺乏人類文化情懷所導致的結果。因為從文化的意義上說,日本學者有了對于敦煌的研究成果是好事,作家應高興才是,應有開放的心態,不能用狹隘的心理對待人類文化。當然,有的散文是有人類情懷的,像季羨林的《喜雨》,因北京喜降甘霖,于是他表示,“我的幻想,從燕園飛到故鄉,又從故鄉飛越了千山萬水,飛到了非洲”。這是一種希望干旱的故鄉以及非洲都普降“喜雨”的愿景。
以往,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甚至以GDP為絕對追求目標。今天,我們應以環保生態、文化發展、人類美好生活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中心,推動國家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中國夢。這就要求散文改變觀念,進入一個像馬克思所說的“一切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追求和價值遵循,即立足長遠、重視人的身心健康、幸福指數、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富裕,以及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福祉。與此同時,讓散文克服狹隘的功利主義,特別是擺脫以西方為價值旨歸、進入一個更具價值合理性的人類理想境界。沒有這樣的宏大視野,散文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創新,也不可能超越自我的狹小格局。
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必然與世界進步發展連在一起,中國的前途命運當然也離不開人類正確的價值選擇。也許中國和世界都處在探索中,有些問題至今還不明確,特別是不一定有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西方特別是美國道路一定不是中國的正確選擇,也未必是人類健康幸福的希望所在。關于這一點,林語堂等許多智者在半個世紀前都做過系統闡述。在中國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散文不能置身事外,而應參與其中,并發揮特殊的價值功能。要達到這一點,改變散文觀念就變得尤其重要,這主要包括:超越長期以來散文的狹小格局,確立中國立場,強調問題意識,抓住戰略發展機遇,放眼全球,有人類視野和天地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