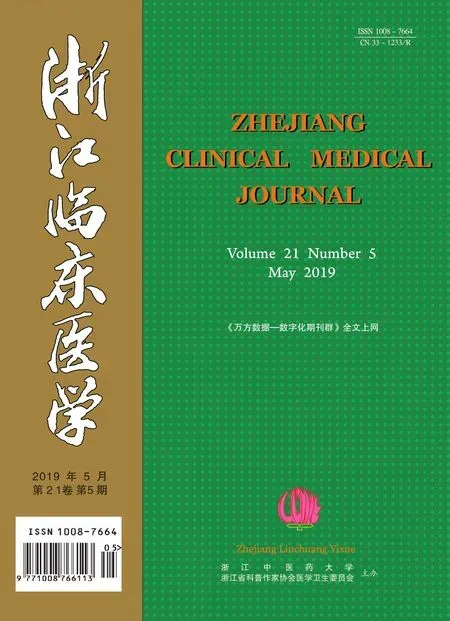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進展
張倉健 鄭智茵* 胡通林 劉淑艷 王淵文 沈建平
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DS)是一組異質性克隆性血液病,以造血功能紊亂和外周血細胞減少為特征,并有向白血病轉化的危險[1]。近年來,對MDS與自身免疫性疾病(AID)的相關性研究認識逐漸加深,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2-3]。從臨床的角度看,部分MDS患者在起病前后出現不同的AID的表現[4]。本文對MDS合并AID的研究進展作如下綜述。
1 發病情況
在一般人口中,每年每10萬人中約有5例患有MDS,通常MDS發病中位年齡65~70歲,而<50歲的患者中,其發生率<10%[5]。20~70歲,MDS的年發病率呈對數增長,從每百萬人中<1.0人增加到每百萬人20人。男性發病率大約是女性的 1.5 倍[5]。
1992年Hamblyn描述104例MDS患者中2例合并惡性貧血,2例甲狀腺功能減退,3例類風濕關節炎[6]。研究發現在所有MDS人群中,MDS 患者中既往病史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為10%~28%[7],有10%~15%的患者存在自身免疫異常表現。MDS患者診斷時常伴有血清學免疫指標異常,如抗核抗體(ANA)異常為 23%~35%,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ANCA)異常為 5%[8]。有研究發現,MDS患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率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23%vs.4%,P<0.0001)[9]。
自身免疫疾病的臨床表現具有高度多態性,包括急性全身或皮膚血管炎、關節炎、結腸潰瘍、腎小球腎炎、周圍神經病變、肺浸潤、雷諾現象,以及典型的結締組織疾病,如復發性多軟骨炎,干燥綜合征和系統性紅斑狼瘡。血清學異常包括高或低γ球蛋白血癥、直接Coombs試驗陽性、單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癥和不同自身抗體的陽性[4]。最常見和研究最多的AID包括類風濕關節炎(RA)、多發性硬化(MS)、銀屑病、炎癥性腸病(IBD)和系統性紅斑狼瘡(SLE)[10]。
AID在MDS亞型中的分布:在一項研究中[11],合并AID的MDS患者中86%是原始細胞過多性難治性貧血(RAEB)。患者多為男性(70%),年齡78~83歲,這可能與一般人群中以女性和年輕患者為主的AID有所不同,除白塞病染色體+8和MDS患者相關,兩者間尚無其他細胞遺傳學異常報道。
2 MDS與AID的相關性
既往研究認為MDS和AID具有相關性,近來新的臨床研究進一步證實這一結論。多項研究表明AID患者出現MDS的概率增加[9]。美國一項大型流行病學研究[9],通過(Seer)-Medicare數據庫對13486例髓系惡性腫瘤患者和160086例對照者進行比較,AID患者患MDS(OR 1.5)和急性髓細胞白血病(AML)(OR 1.29)的風險增加。MDS和AML與血管炎相關最密切(OR 6.32)、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OR 3.74)、系統性紅斑狼瘡(OR1.92)、血清陰性和陽性關節炎(OR分別為1.73和1.52),提示MDS可能是慢性炎癥的晚期表現。在一項病例對照研究中[12],診斷>10年的AID的患者患MDS的風險增加16倍(OR 2.1,95% CI 1.4-3.2)。
2014年 Wilson AB 等[13]對 GPRD(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base)數據巢式病例對照研究,選取849例MDS病例和3417病例配對對照,患有AID的患者患MDS的風險略有增加(OR 1.5,95% CI 1.1-2.0)。按AID的持續時間分層,只有診斷為自身免疫紊亂>10年的患者,OR值明顯增加(OR2.1,95% CI 1.4,3.2)。患病的年齡和病程均可能導致MDS風險的增加。
AID影響MDS患者的疾病進展和生存預后,2016年Komrokji RS等[14]回顧性對MDS患者(n=1408)進行統計,合并AID患者中女性多見,主要是RA和RCMD患者。合并AID的MDS患者的生存期中位值為60個月(95%介于50~70個月),轉白率23%,而無AID的MDS患者的生存期中位值為45個月(95%介于40~49個月),轉白率30%,多因素分析提示是否合并AID、IPSS評分及年齡是影響MDS患者總生存的獨立預后因素。
3 發病機制
MDS合并AID的發生是一個多因素多步驟作用結果,具體過程和機制仍不完全清楚,一般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機制。
3.1 免疫功能失衡 AID主要被認為是針對體內抗原的免疫反應的結果,免疫失衡可能是MDS及自身免疫病的共同發病基礎 。機體免疫反應可分為天然免疫和獲得免疫,細胞因子、免疫細胞、及炎癥相關信號傳導通路能經過調控炎癥反應及天然免疫應答,從而影響造血祖細胞凋亡、增殖與分化[15]。MDS患者存在B細胞及調節性T(CD4+CD25+)細胞數量下降及功能減弱,CD4和CD8細胞亞群向TH1和Tc1極化,這可能與骨髓造血細胞衰竭有關[3]。同樣MDS腫瘤細胞在細胞因子及其他免疫細胞的共同作用下,可激活T細胞為主體的獲得性免疫,導致造血祖細胞凋亡及腫瘤逃避免疫監視,作為免疫失衡也參與到MDS發生發展過程[15]。
3.2 細胞因子異常 現在研究證實有30種細胞因子與MDS發病相關,如TNF-α、IFN-γ、IL-6、IL-10等。這些細胞因子會影響炎癥信號通路及干細胞分化,是參與信號轉導的轉錄因子,被認為是MDS患者自身免疫現象的潛在調節因子[16]。TNF-α表達上調,激活依賴TNF的凋亡途徑,引起MDS患者無效造血。血清TNF-α水平高是MDS患者預后不良的因素[17]。免疫耐受及逃逸相關的細胞因子(IL-10)在MDS患者中表達上調,導致惡性克隆細胞逃避免疫監視[18]。
3.3 骨髓源性抑制細胞擴增 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s)的主要功能是抑制自身反應性效應物CD8+T細胞的應答[19]。證據表明,MDS中T細胞克隆的擴增具有自身抗原識別的潛力[20]。這已證明在染色體8 MDS患者的體內,位于8號染色體上的Wilms腫瘤抗原被過表達并刺激細胞毒性CD8陽性 T細胞對惡性和正常造血細胞的反應[20]。基于T細胞受體-CDR3復合物的互補區域的基因重排研究發現,≥50%的MDS患者可能表現出T細胞克隆性,這可能是由抗原自身反應性介導的。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的特征在于淋巴細胞浸潤和對甲狀腺自身抗體的自身反應以及MDSCs的積累。因此,在如甲狀腺AID誘發器官損傷的類似過程可能最終導致骨髓發育不良的變化。
4 MDS合并AID的治療
目前對于MDS合并AID的治療并無統一標準。近年來,盡管治療策略有所改善,但MDS合并AID的治療仍然是具有挑戰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通常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治療,常導致自身免疫系統表現暫時性的緩解,但并不能治愈血液病,且副作用較大。這類患者通常具有較高的激素依賴率和感染風險[21]。雖然激素能取得一定的療效,但對各種免疫抑制劑的治療策略和療效的報道卻較少。
AID的系統性治療包括各種免疫抑制劑。生物制品是最新的一類藥物,包括腫瘤壞死因子-α(TNF-a)拮抗劑和干擾素等。新的藥物如雷那度胺、去甲基化劑和鐵螯合劑,有助于減緩疾病的自然病程,并改善不符合移植資格患者的生活質量[8]。以往研究顯示,單用TNF-α拮抗劑對MDS的治療反應不足,但安全性相對較好[22]。
2017年 Mekinian A 等[23],分析 29例合并有 AID 的MDS患者使用生物制劑治療反應,利妥昔單抗總體上反應比較好,但不同表現形式的反應似乎各不相同。以關節表現為主的TNF-α拮抗劑是有效的,而在全身血管炎中,應選擇利妥昔單抗。降低激素依賴是治療的一個重要目標,只有使用利妥昔單抗和5-氮雜胞苷才能顯著降低。
有研究指出5-氮雜胞苷可以免疫調節作用,尤其是在骨髓移植過程。DNA甲基轉移酶抑制劑5-氮雜胞苷已證明能提高高危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患者的生存率[24],也可以改善血細胞減少,降低白血病進展和提高生活質量。大量研究表明,5-氮雜環素抑制T細胞的增殖和活化,阻斷細胞周期進程G0到G1期,減少免疫因子的產生[21]。
Costantini B等[25]報道使用5-氮雜胞苷對3例MDS合并免疫性疾病的患者治療,5-氮雜胞苷75mg/m2,7d/1個月,10個療程后,免疫性疾病的癥狀消失,停止使用類固醇激素,骨髓和血液系統獲得緩解。在之后18個月的隨訪中,患者仍保持正常的血液系統和全身癥狀緩解。
5 展望
MDS與AID已經被發現20余年,MDS可以合并各種AID,AID會增加患MDS的風險,影響MDS患者的生存預后,生物制劑利妥昔單抗和5-氮雜胞苷對治療這類患者有一定的療效。目前其免疫失衡機制仍未完全認識清楚,其機制需要進一步研究,深入了解兩者間的關系對后續的治療方案選擇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對MDS發病機制及疾病進展過程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