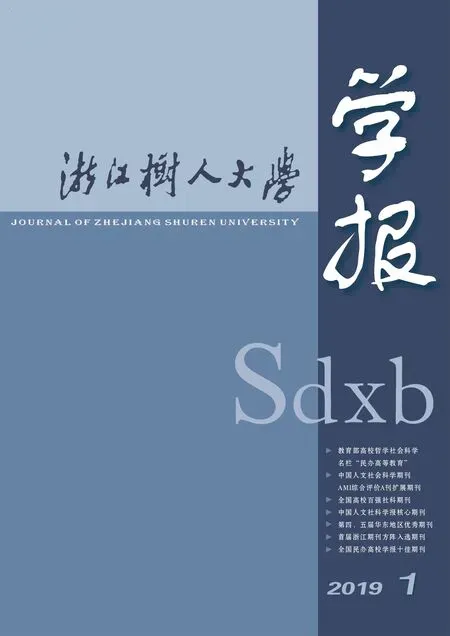中國文學“走出去”之翻譯策略
——以美國漢學家華茲生的禪詩英譯為例
李紅綠
(懷化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南 懷化 418008 )
近年來,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如胡安江(2010)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英譯莫言的小說為例,從譯者模式和翻譯策略的角度探討中國文學應如何“走出去”①胡安江:《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中國翻譯》2010年第6期,第10-16頁。;張倩(2015)以童明的小說譯本為例探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策略與模式②張倩:《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飛散譯者模式探索——以童明英譯木心短篇小說集〈空房〉為例》,《外語教學》 2015年第3期,第105-109頁。;魏清光(2015)分析中國文學“走出去”面臨的問題、現狀及應采取的策略③魏清光:《中國文學“走出去”:現狀、問題及對策》,《當代文壇》2015年第1期,第155-159頁。。
美國當代漢學家華茲生譯介中國典籍30余部,涉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學、哲學和佛學等領域,為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尤其是英語國家的推廣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各種文學作品翻譯中,漢詩的翻譯難度最大。因此,在翻譯漢詩時,華茲生既十分注重譯文的可讀性,重視譯文譯者的審美品位和文化背景,也十分注重譯文的忠實性,重視保留原語文化,通過適當的翻譯策略,在譯文的可讀性與忠實性之間維持平衡,從而使中國古典文學順暢地“走出去”,為更多讀者所接受和喜愛。在多個譯詩序言中,華茲生均對其詩歌翻譯策略作出解釋,如譯文在內容、語言表達特點、譯文風格和文體等方面應如何忠實于原詩,應采用什么樣的語言譯詩等。從他的譯詩譯論中可以發現,華茲生的詩歌翻譯策略主要集中在譯詩用語與譯詩詩體兩個方面,下面分而論之。
一、翻譯用語策略:運用當代美國英語翻譯
翻譯用語決定譯文的通達和流暢,是影響譯文可接受性的一個主要因素。古今中外學者、翻譯家對此都非常重視。我國早期佛經翻譯的“文、質”之爭就與譯語行文風格有關。質派以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為依據,主張譯文語言質樸,翻譯才忠實可信;文派則以孔仲尼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為依據,主張譯文語言須有文采,譯文才易于為信徒所接受而流芳百世。玄奘提出“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譯經標準。所謂“喻俗”就是要求譯語符合大眾的口味。清代翻譯家嚴復提出的翻譯三大標準“信、達、雅”,可謂影響深遠,其中“達、雅”都是對譯語的要求。魯迅先生提出“寧信而不順”[注]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9頁;第294-299頁;第327頁。的譯法,強調譯語表達的忠實性比譯語的流暢性更為重要,這樣才有利于從西方語言中引進新的表達法,輸入新的血液。與之相反,趙景深先生則提出“寧順不信”②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9頁;第294-299頁;第327頁。。林語堂先生提出翻譯的三條標準,即“忠實標準、通順標準、美的標準”③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9頁;第294-299頁;第327頁。, 其“通順、美”的標準與嚴復先生的“達、雅”一脈相承。可見,中國傳統譯論對譯語的流暢性極為關注,只是在采取何種翻譯策略實現譯語的流暢性方面,翻譯家們見仁見智。
華茲生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實現譯語的通暢和文采上。在其譯著《中國抒情詩:從二世紀到十二世紀》的引言中,他明確提出了翻譯用語策略:“我把原文譯成當今美國英語。毫無疑問,這種語言是我最熟悉的語言。因此也是我能取得成功的語言,成功的機遇最大。這也就是說,我做翻譯的時候,好似我在用自己的語言寫作,而且是以我最仰慕的當代美國詩人為模范進行的創作。”[注]Watson B, 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4.他認為,以當代美國詩人為模范,用現代美國英語翻譯詩是最佳的翻譯用語策略。這是一種典型的歸化翻譯策略。勞倫斯·維努蒂(Lawence Venuti)曾說:“在英美翻譯傳統中,歸化翻譯策略一直占據主流,譯者通過把原文譯成流暢的英語,使表達符合英文習慣,就可以產生可讀性較高的譯文。”[注]Jeremy M,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Routledge, 2001, p.146.歸化的翻譯策略會降低原文的異質性特征,使讀者感覺不到譯者的存在,即譯者隱形(invisibility)。但在譯詩過程中,華茲生并沒有考慮這種譯詩策略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考慮的是盡可能使譯文符合現代美國英語的行文習慣,以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因為可讀性差的譯本難以獲得讀者的認可,那是譯者或譯作更大的“隱形”,譯者不僅會面臨讀者的質疑,而且需應對譯作失敗的各種困局。
華茲生的翻譯用語策略顯然是對西方傳統翻譯規范的堅守和遵循。18世紀英國著名翻譯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提出翻譯三原則:譯作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譯作的風格和手法應和原作屬于同一性質;譯作應具備原作所具有的通順[注]轉引自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29頁。。華茲生的翻譯用語策略是對泰特勒第三條原則的發展,是對如何實現譯文通順提出的可操作性策略。20世紀英國翻譯理論家西奧多·賀拉斯·薩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提出十二條翻譯指導原則,其中第八條是“譯文讀起來應該像譯者同時代的作品”[注]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與華茲生的譯詩策略不謀而合。當代著名翻譯家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給出了翻譯的定義:在譯語中,用最自然最貼切的方式再現原文的信息,首先是意義方面的,其次是風格方面[注]Eugene A N, Charles R 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2.。在華茲生看來,奈達所追求的最自然、最貼切的翻譯方式,可以通過運用當代美式英語翻譯得到最佳解決。
縱觀西方翻譯史,從西塞羅·圣哲羅姆(Cicero St Jerome )的“譯意論”(sense-for-sense)、德國宗教改革運動領袖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用普遍民眾的語言翻譯”、多雷(Dolet)的翻譯五原則,到當代功能學派目的論所主張的流暢性原則(coherence rule),都將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視為非常重要的翻譯原則。可見,華茲生的譯詩策略與西方翻譯傳統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傳承性。在接受John Balcon的采訪中,華茲生坦承自己的譯詩策略受龐德(Era Pound)和韋利(Waley)的影響很深,尤其是后者。他說:“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我發現最好的方法是盡力多讀優秀的當代美國詩歌。我希望把當代美國英語中的習語運用到詩歌翻譯中去。我從來沒有想過把詩譯成英語古代詩歌的形式或風格。”[注]Balcom J, An Interview with Burton Watson, Translation Review, 2005, No.1, pp.7-12.龐德所主張的“英文譯文應用地道的表達”[注]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討》,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和“在譯詩中放棄原詩詞句的推敲,抓住細節,突出意象”[注]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在華茲生的譯詩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下面以華譯寒山詩為例對其譯詩用語策略加以說明。
My father and mother left me a good living;
父母續經多,
I need not envy the fields of other men.
田園不羨他。
Clack-clack-my wife works her loom,
婦搖機軋軋,
Jabber, jabber, goes my son at play.
兒弄口喎喎。
I clap hands, urging on the swirling petals,
拍手摧花舞,
Chin in hand, I listen to singing birds.
支頤聽鳥歌。
Who comes to commend me on my way of life?
誰當來嘆賞,
Well, the woodcutter sometimes passes by.
樵客屢經過。
這是華茲生《寒山:唐代詩人寒山詩百首》譯詩集中的第一首譯詩。寒山詩是典型的禪詩,大多用通俗的白話寫成,寓哲于俗,意近旨遠,讀起來淺白如話,但詩意雋永。在翻譯這首詩時,華茲生采用了大量口語化的詞匯,如a good living,at play, listen to, come, pass by等當代美式英語詞匯。此外,詞法、句法表達也非常口語化,如leave me a good living, need not envy, go at play,以及由who所引導的一個簡單疑問句等,微妙地再現了原詩的風格。
華茲生的譯詩用語策略不僅影響了譯文的行文風格,對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產生積極的影響,也對其譯詩選本產生一定影響。在多部譯作序言中,他反復提到因為部分漢詩更適宜譯為英文,所以選譯較多,如在《中國賦:漢魏六朝賦體詩》序言中,他寫道:“我選擇的十三篇賦體詩,除一首外,其余都出自《文選》中的賦篇……我選擇的這些賦體詩除了我喜歡外,它們更適宜譯成英語。”[注]Watson B, 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y Perio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0.對于在《哥倫比亞詩選》中較多選譯白居易的詩,華茲生這樣解釋:“我覺得白居易的詩似乎比其他任何重要的詩人都更能有效地譯成英語。在這一點上,我與韋利(Arthur Waley)有同感。因此,他的詩我選擇的比較多。”[注]Watson B,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42.在接受巴克利采訪時,華茲生表達了對白居易的仰慕,稱“白居易是我最喜歡的中國詩人。他的詩相對來說容易閱讀,容易翻譯,常帶有一種幽默感。很多時候,我對他所說的話都能感同身受。”[注]Balcom J, An Interview with Burton Watson, Translation Review, 2005, No.1, pp.7-12.對《蘇東坡詩選》中的譯詩選本也作了類似說明:“我的譯詩選集《蘇東坡詩選》包括112首詩,2首賦,以及從上述信件中節選的部分內容……我選擇的詩歌都是適合譯成英語,我所喜歡的詩歌。”[注]Watson B, 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 Copper Canyon Press, 1994, p.12.在《中國抒情詩》一書序言中,華茲生進一步說明他譯詩選本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原詩適于譯成當代美國英語:“《中國抒情詩》大約選譯了200多首詩,選擇這些詩不僅受我個人偏好的影響,而且根據我的判斷,也最便于譯成英文,能夠代表某一個時期最好的風格和詩學傾向。”[注]Watson B, 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華茲生堅持運用當代美國英語翻譯,并將原文本是否適于譯成當代英語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條件,因此他的譯詩符合西方當代英語讀者閱讀品味,容易被接受和認可。可見,華茲生在翻譯漢詩時具有強烈的母語意識,非常關注讀者的審美品位,這使其譯詩在可讀性和可接受性方面脫穎而出。
二、詩體翻譯策略:緊貼原文結構,放棄韻律
華茲生主張譯詩應緊貼原文結構,放棄韻律。他在譯著《哥倫比亞詩選:從早期到十三世紀》的譯序中說:“譯者只有將英詩傳統中的節奏和韻律以及西詩的措辭與主題放置一邊,才可能成功地將古典漢詩譯為英詩,創造一種能夠傳達原詩表達與力量的更為自由的形式。這種創造行為已眾所周知。通過龐德、韋利等人的筆墨在本世紀的前幾十年中已大放異彩。至今,我們耕耘在此領域的譯者仍受益匪淺。”[注]Watson B,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3.他明確提出放棄保留原詩韻律的翻譯策略,且認為,由于中英兩種語言在讀音上的差異,原詩歌的韻律在譯文中是無法保留的。在《早期中國文學》一書譯序中,他也提出了韻不能譯的觀點:“我要求讀者牢記,詩歌比散文尤甚,其美與音樂性存在于原文本中,一經翻譯成其他語言,就無可奈何地丟失了。”[注]Watson B,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01.在一次接受采訪時,狄蕊紅問他:“在翻譯中國古詩時,您是否考慮韻律,如何保持詩歌語言的優美?”華茲生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韻律,我翻譯的時候,強調的是字對字的意思表達、實意表達,沒有考慮平仄。”他進一步解釋采取這種策略的原因:“開始我非常擔心會影響中國古詩的優美,但當時在英語世界已經不考慮詩歌的韻律了,所以我一直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譯,現在英語詩歌里面,很少有人側重韻律,這是現實情況。所以翻譯中國古詩變得很容易,讀者也容易理解。在19世紀的英語詩歌中有很多還在采用韻律,韻律在20世紀的美國英語詩歌中幾近舍去。”[注]狄蕊紅:《訪漢學家、翻譯家巴頓·華茲生》,2015-06-01,http://world.gmw.cn/2013-09/02/content_8770060_2.htm。從這一段對話中可以看出,華茲生反對因韻害義,主張以散體譯詩。在其譯作《莊子全譯》序言中,華茲生再次就放棄原文韻律的翻譯策略作了解釋:“我并不打算再現原文的押韻方式。在當代英語中,執著于押韻技法的詩歌,對我而言,聽起來似乎有一種詼諧滑稽的傾向。”[注]Watson B,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0.因此,在譯詩時,他對原文的詞語游戲和聽覺效果僅予以暗示或通過注釋指出其存在的方式,而沒有考慮在譯文中加以保留。
華茲生對詩體結構極為關注。在《杜甫詩選》序言中,他就漢詩中平行結構的翻譯發表看法,提出詩體結構的翻譯策略。他說:“杜甫以純熟的方式在律詩中創作了許多平行結構。這是他詩歌藝術的奇跡之一。這些平行結構也在他的其他詩體中廣泛應用。但一經翻譯,譯文讀起來要么矯揉造作,要么顯得死板,尤其是現代詩歌中已很少采用這種修辭形式。而且律詩語言高度濃縮,全無句法,一經翻譯就成了一堆意象,顯得死板而無活力。有些譯者通過有意打亂原詩平行結構的對稱形態,減少其矯揉造作的效果,或者通過把某些詩行譯成跨行句(run-on line),延續到下一行,改變原詩詩行末尾停頓結句的方式,從而擺脫原詩的單調感。雖然我理解這些處理方式后面的動機,但在我的譯文中,絕大多數情況下,我盡量緊貼原詩的措辭與詩行結構。”[注]Watson B, The Selected Poesm of Dufu,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50.華茲生的這番話道出了漢詩英譯時兩種不同的詩體結構翻譯策略:一是打破中詩結構,采用符合西方詩學理念的跨行句對譯;二是緊貼原語結構翻譯。第一種策略在西方用得較普遍。如葉維廉先生所言:“幾乎所有中國古詩的英譯,都忽略了中國古詩特有的句法結構,即中國古詩特有的表達模式,千篇一律地變成了英詩的結構。”[注]轉引自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頁。華茲生采用了第二種策略。如果譯詩時既打破原詩結構,又不保留或再現原詩的韻律,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譯文不過是改造了的西詩。華茲生雖然沒有保留原詩韻律,但保留了原詩的結構,在忠實與變通之間維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下面以華譯禪詩《鹿柴》為例來加以說明:
原文:
鹿 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譯文1:
The Form of the Deer
So lone seem the hills, then is no one in sight there.
But whence is the echo of voices I hear?
The rays of the sunset pierce slanting the forest,
And in their reflection green mosses appear.[注]Eliot W, Octavio P,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wei, Asphodel Press, 1987, p.8.
W.J.B. Fletcher, 1919
譯文2:
Deep in the Mountain Wilderness
Deep in the mountain wilderness
Where nobody ever comes
Only once in a great while
Something like the sound of a far off voice.
The low rays of the sun
Slip through the dark forest,
And gleam again on the shadowy mess.[注]②③Eliot W, Octavio P,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wei, Asphodel Press, 1987, p.22;p.24;p.25.
Kenneth Rexroth, 1970
譯文3:
Deer Fence
Empty hills, no one in sight,
Only the sound of someone talking;
Late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wood,
Shining over the green moss again.②Eliot W, Octavio P,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wei, Asphodel Press, 1987, p.22;p.24;p.25.
Burton Watson, 1971
對比以上3首譯詩結構可以發現,華茲生的譯文雖沒有用韻卻最貼近原詩結構,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和帕斯(Octavio Paz)在對比王維詩《鹿柴》的17個譯本后作如此評價:“華茲生表達的意象像漢詩原文一樣直接。一起用了24個英語單詞(每行6個)對譯漢詩20個漢字。他既翻譯出了原詩中的每一個漢字,也不顯得放縱拖沓。與其他譯者不同,他采用電報式的翻譯將字數控制到了最少。翻譯詩歌,最難做到的就是簡潔。華茲生毫不費勁地保留了原詩中的平行對稱結構(parallelism)。”③Eliot W, Octavio P,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wei, Asphodel Press, 1987, p.22;p.24;p.25.由此可見,緊貼原文結構翻譯,在譯詩中保留漢詩簡潔的風格,是華茲生漢詩詩體翻譯的主要策略。
三、結 語
華茲生是當代著名的漢學家、翻譯家,曾三度榮膺美國翻譯金筆獎。他有多部詩歌譯作被收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翻譯集·中國系列叢書,其禪詩譯作寒山譯詩在美國成為經典,寒山成為美國嬉皮士的精神偶像。華茲生出版了10多部詩歌譯作,為中國文學的傳播與推廣作出了巨大貢獻。本文根據華茲生本人的詩歌翻譯論述,結合其禪詩翻譯實踐,整理和闡發了華茲生的詩歌翻譯策略。通過研究發現,在翻譯漢詩時,華茲生主要運用當代美國英語翻譯,確保譯文語言明白暢曉,增強譯文的可接受性,獲得讀者的認可。同時,華茲生放棄保留原文韻律,力求保留原文的結構,力爭在結構方面再現原文的美感,在詩歌翻譯的韻律與結構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可以看出,華茲生在漢詩英譯時采取的策略是變通的,既維護了譯文的忠實性,也考慮了譯文的可接受性,對中國文學“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