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暖者-煤場-卡車-煤礦
南方周末記者 楊凱奇 發自北京、山西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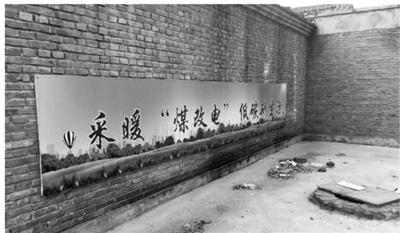

2005年,南方周末記者從北京循著一塊燃燒中的煤出發,回溯它從挖出、運輸到燃燒的輾轉路線,試圖在這條復雜的鏈條中,提供一個與煤有關的社會圖景的縮影。
這是煤炭“黃金十年”的一瞬。14年后,在去產能、能源消費結構調整、環境治理、金融縮緊的合力下,煤炭產業遭受夾擊,從高峰一路下跌。利益之旅上的“取暖者-煤場-卡車-煤礦”,都在艱難轉型。
南方周末記者 楊凱奇 發自北京、山西大同
南方周末實習生 姚瑤
2019年的第一天,北京市區最低氣溫零下9℃,空氣優良但能見度一般,看不到遠山。
不過,北京延慶區西屯村村民馬福泉感到,這個冬天的霧霾天數好像又少了一些。老馬的理解是,“為了環保,普通人也得付出點代價。”即便享受了補貼,為了達到同樣的取暖效果,從散煤改燒煤球,一個冬天他得多掏兩千塊錢。
2018年,北京平原地區已經基本實現“無煤化”,這可能也是西屯村用煤炭取暖的最后一個冬天。老馬也許漸漸連煤球都不能燒了,延慶作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主辦地,賽區周邊也將“無煤化”。
曾經的煤炭“黃金十年”里,煤場、卡車再到煤礦,人人都能喝一勺肉湯,利益逆著老馬家的暖炕上滾;而今,塵肺病、超載事故乃至霧霾……負面影響順著煤礦揚起的煙塵下行。
在去產能、能源消費結構調整、環境治理、金融縮緊的合力下,煤炭產業遭受夾擊,從高峰一路下跌。2018年12月27日,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在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提出,2019年,煤炭消費比重要下降到58.5%左右。和2013年相比,下降了將近十個百分點。
“富煤、少油、貧氣”的資源稟賦下,取暖者-煤場-卡車-煤礦,每個人都在艱難轉型。
“2019年基本 不可能掙錢”
剛過立冬,馬福泉就一次性攢了十噸煤球。“一麻袋煤是50斤,一天要燒6麻袋。”
散煤是不規則的大煤塊兒,燒起來濃煙滾滾,嗆人,但“溫度起來得快”;煤球則像黑色的大饅頭,比散煤環保,但沒有燒散煤暖和。
在老馬的賬本里,以前燒散煤,500元一噸;現在燒煤球,補貼以后370元一噸,但要想暖和些,量是散煤的1.5倍。
在西屯村,并非人人都愿意為降低PM2.5濃度犧牲家里的溫度。散煤仍有市場,只不過轉入地下。
“以前在大街上吆喝著賣,現在偷偷賣。”馬福泉聽說過河北曲陽燒散煤被拘留的烏龍新聞,他留意到,主要進村道路上也有散煤車輛檢查站。
南方周末記者以幫親戚打聽為由聯系到一位散煤老板,見記者是外地手機號,他加強了警惕。“我們的煤是內蒙古來的,明天讓你親戚直接聯系我。”隨后掛斷了電話。
老馬家的煤球來自一公里外的西關煤場,老板孟華從夏天就開始儲備煤,加工成型煤(煤球),到了12月,西關煤場的煤堆已經賣了大半。
“煤炭現在變得人人喊打,我們感覺快被淘汰了。”在這里,孟華更早感受到行業冬天的到來,她常常懷念做散煤那幾年。“從煤礦拉來我們這兒,我們直接倒一手分銷給周邊的農戶,賺個差價,雖然利潤不高,但投資不大,也省事兒。”
2002-2012年煤炭的“黃金十年”里,在煤場買賣煤炭就像逛超市,沒人討價還價,掏錢爽快。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顧問楊富強介紹,中國加入WTO以后,煤炭消費隨經濟一同起飛。2000年,煤炭消費總量為12億噸,之后每年增長一億多噸,到2013年的十三年間,翻了近兩番。
拉煤車司機也曾是高收入職業。孟華一家是延慶當地人,有陣子,政府要求在每個鄉鎮配置一個煤場,她的愛人和小叔子一起,在山西、內蒙古拉煤,攢了錢,就辦了西關煤場。
北京市的燃煤污染治理始于1970年代,興于1990年代。《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實施后,煤改清潔能源提速。孟華記得大概就是那時候政府要求煤場要加工成型煤,“我們投資設備就花了700萬,還多雇了運維設備的工人。”
2017年,北京完成了PM2.5年均濃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標,孟華感覺煤場依然被“重點盯防”。要求一直在提高,抽查力度也在加大,最近的頻率是一星期來兩次。
這不僅是為了降低PM2.5,《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也要求,推進農村能源消費升級,大幅提高電能在農村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孟華感到,“2019年基本不可能掙錢。”
全延慶的供暖煤總需求量已從十數萬噸跌到2018年的七八萬噸,她預測,2019年可能不到兩萬噸,這個數還得延慶的七家煤場共同分配。
“反正就是反復地往里投資。”孟華嘆了口氣,“本還沒賺回來,明年就沒得做了。”
“到處打聽哪個煤礦 需要送貨”
深冬的北京,下午6點天就黑了。晚上偶爾還有卡車來西關煤場拉煤,運往更偏遠的村子。
越來越多的城市正成為大卡車司機難以抵達的禁區。27歲的山西朔州人李漢,黑色幽默般地親歷了這個過程。
北京的火力發電廠曾仰仗山西大同和內蒙古,那里是動力煤的主要產區。2010年前,李漢就跑過大同到北京的拉煤線路。那是令大車司機神往的年代:買一輛40萬左右的斯太爾大卡車,跑六七趟長途就能回本。
轉折來得很快。2017年3月,北京最后一家煤電廠停機,在此之前,李漢已與老鄉們一起往天津港工業區送煤。沒想到兩個月后,按照《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天津港停止接收公路運輸煤炭。
李漢不得不轉戰江蘇。又沒想到,2018年江蘇中小企業需求不振,李漢從每個月跑兩趟江蘇減少到一趟。
他常感慨沒遇上好時候。
許多籍貫晉北(大同、朔州、忻州)的大車司機有相似的入行經歷,李漢也不例外。高中畢業后在家無所事事,家里人逼他去拜大車師傅學藝,早點掙錢娶媳婦。
“十年前煤炭銷路好,是煤礦求著大車把煤運出去。”李漢回憶,“現在反過來了,我們到處打聽哪個煤礦需要送貨。”這種局面下,產生了以專門販賣拉煤業務信息為生意的群體,被司機稱為“信息部”或“信息販子”。
“信息販子”一部分由消息靈通的大車司機轉型,一部分是煤礦內部的人。他們從每單業務里抽一到兩成,處于煤炭鏈條里最舒服的位置,司機對他們既羨慕,又怨恨。
長期高度緊張,飲食睡眠沒有規律,大車司機落下了胃病、頸椎病等職業病,還要為挨罰提心吊膽。
李漢說,自從高速公路有了治超辦后,超載現象少了許多,“現在最讓人頭疼的是環保,常因為揚塵和尾氣排放超標挨罰。”
他的車的貨柜里裝了兩個小籃子,每個籃子放了一塊藍色氈布,蓋在煤炭上防止揚塵。放一塊氈布還是兩塊,可以鑒別這輛大車是跑周邊短途還是長途。“跑長途的到了外地,容易因為揚塵問題挨罰,所以要蓋兩層,更小心一點。”
大同市西水磨村密集分布著數十家大車維修鋪,往來卡車掀起的煙塵遮天蔽日。一個剛入行的司機俯下身,仔細看著修車師傅維修他租來的新車。他指了指車頭與貨柜連接處一個顯眼的白色設備。“這是個環保設施,能讓尾氣出來是白色的。不裝這東西尾氣就達不了標,不讓上路,現在出廠的新車都得裝。”
經歷了煤炭產量總體下滑的低谷,如今市場回暖,又推高了煤價。許多大車司機都抱怨,運輸價格反而在下跌。李漢分析,拉煤是賺快錢的捷徑,仍源源不斷有人入行,僧多粥少。
有礦工到大城市,成為外賣騎手
李漢在大同拉的煤,都源于中國第三大煤炭企業——大同煤礦集團。
50歲的崔海,曾經是同煤三礦的礦工。老礦開采的是淺層煤,資源接近枯竭,有效益的是利用新技術開采的深層煤礦。2016年三礦關閉,崔海以勞務派遣的形式被分流,無事可做,出來跑出租,穿梭于市區和恒安新區之間。
恒安新區堪稱同煤財務狀況的晴雨表,大同人沿襲從前的叫法,繼續把這里稱為“棚戶區”,甚至車站站牌也這么寫。同煤集團礦工們原來住在礦井附近的生活區,由于那里房屋老舊破敗,被稱為棚戶區。
雖然棚戶區生活簡陋,煤炭效益好的時候,“女孩兒都喜歡找同煤的,覺得私企的都是臨時工,瞧不上。”一位同煤老礦工說,以往同煤不對外招工,只考慮礦工子弟。子弟接班還必須到軍隊服役,為此許多家長寧可花錢打點關系,送孩子去當兵。
“家庭好的都想到二線,不用下井惹一身臟。家庭不好的都想下井,多掙點錢。”時移勢遷,崔海覺得新一代的礦工們,少了父輩的獻身精神。
1990年代末,棚戶區拆改,統一搬進了“恒安新區”,一個類似北京天通苑的地方——模樣雷同的住宅樓,居住著近40萬人口,號稱“亞洲第一大居民區”。
脫下污跡斑斑的工服,礦工們轉身撐起了一個燈紅酒綠的城鎮。恒安新區除了住宅樓外,多是飯店和KTV,比大同城區里還要熱鬧。
崔海說,現在棚戶區40萬人口中約有一半是外鄉人。做生意、開飯館,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汲取煤炭的養分。
曾經,更多的外鄉人是來自四川、湖北、陜西等地的礦工。在同煤集團之外,還有難以計數的私營小煤窯見縫插針地密布于此。它們絕大部分沒有取得探礦權,遑論采礦權,但彼時中國高速膨脹的能源胃口顧不得那么多。
除礦難頻發、虐待般的工作條件接連引起輿論聲討外,據新華網2011年一篇報道,小煤窯粗放開采,給山西每年造成300億元的生態價值損失。
2009年,同煤集團開始對私營煤礦整合,外地礦工隨著小煤窯一起消散了。
有的因為塵肺病,在病床上度過余生;有的繼續以挖礦為生,或是回到老家做建筑工人,還有的到了大城市,成為外賣騎手。出路不一而足,但他們都沒有在大同留下什么印記。現在,大同的礦工絕大部分是本地人,同煤的國企職工。
在煤炭“黃金十年”里,兼并意味著做大做強。高潮結束,這些兼并而來的產能和數以萬計礦工的分流安置壓力卻成了包袱。
據楊富強介紹,中國煤炭消費走入下行軌道后,整個山西煤炭行業從2014年盈利28.7億元,跳水至2015年虧損94.25億元。商業區熱鬧不再,崔海記得,那幾年的出租車生意也不好做。“拿不到工資,大家都把錢包捂緊了。”
至2018年底,同煤集團已經為“去產能”關閉了9座礦井,整個山西省已關閉88座。同煤關閉效益低下的老礦井后,盈利能力有所回暖,恒安新區也重新歌舞升平。
即便自己被分流了,崔海也認為“擠掉老礦”的新礦給同煤帶來了積極改變。“原來挖淺層煤的時候,把地表打得像老鼠洞,到處都是。現在深井用上了液壓設備,工人可以操作車輛直接深入地下,安全性高得多。”
他還記得,1980年代,礦井里普遍用木架子支撐。有一天,一塊大石頭突然落下,砸中了他面前的一位工友,拖出來時,人已經咽氣了。
從“煤都黑”到“大同藍”
從源頭去產能到末端治理,轉型,沿著煤炭產業鏈多米諾骨牌般倒推。洗煤廠去除煤中的硫成分,鋼鐵廠、火電廠加裝設備,都努力讓煤更干凈一些。
據北京市環保局數據,2013-2017年,與燃煤直接相關的二氧化硫的年均濃度已從2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8微克/立方米,接近國際大都市年均值,屬中國冬季采暖大城市中最低。PM2.5源解析結果中,本地排放貢獻中,燃煤源下降幅度也最為顯著,已降至3%。
但要讓PM2.5年均濃度下降到10微克/立方米的世衛組織指導值,或是按IPCC報告建議,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楊富強認為煤炭用量還需繼續削減。
雖然還沒有通往北京的高鐵,大同城中村和城鄉接合部正在和3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樣搞著“煤改電”“煤改氣”。城區里,一座座燃煤鍋爐被拆除,替代者是發電廠流過來的帶有余熱的循環水,燃氣公交車則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
“聽說大同藍天指數超過全國80%的城市呢。”崔海自豪地說。大同一度是全國空氣質量最糟糕的城市之一,從“煤都黑”到“大同藍”,對藍天的向往被抑制了太久太久,轉型期陣痛似乎也更易接受,大同人正在嘗試消化這份悲欣交集。
“別的也不會干了。”李漢這么表示。他剛剛娶了媳婦,為了養家,一刻也不敢停歇。他向往著,賺了錢能自己組一個車隊,雇幾個司機,就不用自己東奔西跑。
孟華認為西關煤場當年是政府引進的,未來不能做也是政策原因,“以后怎么退出,也沒給我們一個說法。”
她更惆悵以后該做什么行當。做煤場這行要和村民打交道,需要深厚的本地關系,在還能燒煤的地方再辦一個煤場的想法并不現實。投資天然氣等其他能源,又沒有人脈,難以進入。
西屯村的命運,可能會更接近鄰村老白廟。
老白廟是延慶城區周邊最早完成“煤改電”的村子,裝上“新能源”(村民對空氣源熱泵的俗稱)以后,不用再半夜起床給鍋爐添煤,每當室內溫度不足時,“新能源”會自動重啟加熱,確實干凈和方便不少,價格比燃煤還便宜。
當然,這背后是北京市的巨額補貼。按延慶區政策,每戶“煤改電”人家可享受取暖設備、暖氣片安裝上的補貼,最高可達13500元。此外,電價亦有優惠。
“你瞅,那個就是‘新能源。”順著老白廟村民馬國玉手指的方向看去,在對面鄰居土黃的平房前,充滿科技感的白色空氣源熱泵像是天外來客。
鄰居女主人打開大門,迎接她老漢。老漢騎著電三輪吭哧吭哧地進門,車里裝滿了他從田間地頭拾到的柴火。“讓一讓誒!”老漢喊道。車尾突出的樹枝刮到了站在一旁的馬國玉的臉,這是北京農村的干燥冬天,刮得生疼。
法拉第發明了發電機,改變了老白廟村民的取暖方式。但他們還要生火做飯,生火燒炕——熱泵的產物是熱水,進不了炕底。“尤其老人過冬,離不了炕。”馬國玉說。在這些需求上,村民們與幾千年前祖先的解決方案并無不同——點著那些干枯的樹枝。
(文中李漢、馬國玉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