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格局中,內容行業必須要有技術的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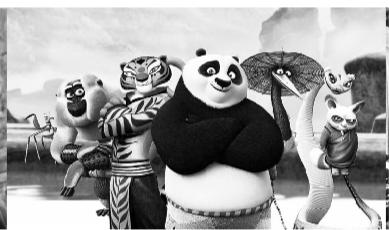


“中國的文化娛樂產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交界地帶厘清彼此邊界,包括建立行業監管、自律和協同機制,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既服從政府監管又能保護投資人的利益,需要進一步探索,并及時根治行業內部某些亂象。”
南方周末記者 朱強 發自北京
2018年12月10日,當代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大江大河》開播。這部以改革開放為背景的電視劇,在播出后口碑持續上揚,豆瓣評分目前已超過2017年最具話題性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
《大江大河》出品方之一的正午陽光,曾成功制作了膾炙人口的《歡樂頌》《瑯琊榜》《偽裝者》等熱播劇。2016年,在被蜂擁而至的資本追逐五年后,正午陽光的核心人物侯鴻亮、孔笙等,選擇了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并出讓第一大股東的席位。
作為華人文化集團公司(CMC)掌舵者,黎瑞剛對好作品的涌現抱持樂觀的態度——“影視娛樂行業考慮的首要問題,是把人性的價值拍透,把自己的作品拍好。未來,好的中國影片一定會不斷涌現,這是大趨勢。”
華人文化也正在影視娛樂行業不斷做“加法”,并計劃成立自己的影視公司。
2012年,中方控股的東方夢工廠在上海成立,黎瑞剛開始整合中美動畫資源。2016年《功夫熊貓3》成功大賣,全球票房超過5億美金,中國內地票房也近10億元。2018年2月,黎瑞剛和接手美國夢工廠動畫的NBC環球就股權出讓達成協議,CMC全資控股了東方夢工廠。
經過和美國好萊塢五年的深度合作,東方夢工廠成為“目前國內唯一具備出品世界級動畫電影能力的公司”。2018年6月,東方夢工廠宣布,將與香港喜劇導演周星馳合作首部動畫電影《The Monkey King》(中文暫名“齊天大圣”)。
2017年,黎瑞剛主導了兩筆重要的投資,基本完成了CMC在影視全產業鏈的布局。當年4月,CMC入股全球最大的經紀公司——美國CAA(全稱“Creative Artists Agency”),同時將與CAA共同組建合資公司——“CAA中國”,進一步發展中美跨境藝人經紀業務,并拓展在電影、電視、現場娛樂等相關領域的布局。9月,CMC完成了對國內UME影院的收購,加上之前投資的在線票務網站格瓦拉等,從而在影視制作、宣發、藝人經紀、影院等建立了完整的商業閉環。此外,CMC還成為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的大股東。
除了傳媒和娛樂板塊,黎瑞剛涉及的投資領域還包括互聯網科技和消費。CMC旗下有兩個平行的板塊,被外界稱為黎瑞剛的左右手。一個是以CMC資本(CMC Capital Partners)為主體的投資板塊(前身是成立于2010年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其中傳媒和娛樂領域的投資比重占50%左右,另外50%集中在技術和消費領域,但即使這另外50%,也很少投純內容的公司,偏重技術和內容結合,比如愛奇藝、快手、B站等平臺。
另一個板塊則是華人文化集團公司(CMC Inc.),偏重戰略性投資,以內容運營為主,收購后自己運營,或者尋找團隊,孵化新業務。通過集團公司,CMC得以深度參與到一些內容企業的運營之中,使其得到資源加持和穩健發展,公司估值得以不斷提升,其中包括梨視頻、財新傳媒、正午陽光等。
對黎瑞剛來說,內容產業,包括其中的頭部內容,如果缺少技術基因或模式變革,已經很少成為CMC投資或運營的目標,也相應開始在這個領域做減法。
“傳統媒體出來的團隊大部分是做內容的,而今天在數字媒體時代,另一類有話語權的是有技術基因的團隊。”不過,黎瑞剛也表示,有內容優勢的團隊,如果尊重技術的價值,能夠創造出新的模式,仍然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他看來,梨視頻創立的全球拍客系統,就是內容嫁接技術的模式創新。
具有原創內容基因的財新傳媒,2018年開始推行內容付費,也得到了黎瑞剛的鼎力支持。“媒體廣告往下走,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行業趨勢,未來肯定要有一些模式創新。”他說,“內容付費并不適合所有的媒體,只有品牌媒體,或者高附加值的品牌媒體才有機會。”
黎瑞剛認為,中國的文化娛樂行業正在經歷一個深度調整的過程:從過去的管制與封閉,逐步走向開放和市場化,資本熱錢不斷涌入,又造成行業普遍存在公司估價偏高的問題;同時,互聯網科技發展和技術變革,不斷創造出內容生產的新模式和新業態,這對行業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過去的很多游戲規則都不適用了”。
“持續地創造爆款, 需要持續的體系塑造”
南方周末:華人文化集團公司已在傳媒和娛樂產業有廣泛的布局和運營,并對泛文娛產業有清晰獨特的投資邏輯,最近幾年成功投資了數十家線上線下優質內容公司。但是最近你提醒,文化產業投資需要回歸五個常識,包括回歸產業規律、健康的價值觀、體系化運營、尊重消費者、完善的創業環境等等。你認為,目前文化和娛樂行業究竟存在哪些問題?為什么?
黎瑞剛:首先是資本的問題。國家去杠桿、銀行資管的政策、對外匯的管制等,都對整個資本市場有很大的結構性調整的影響。事實上,這些宏觀政策的調整,對所有行業都有影響。除此之外,文娛行業自身的問題,比如演藝人員的稅收問題、影視行業收視率(票房)數據造假的問題等,這些問題長期存在。
行業階段性的政策調整,包括稅收大趨勢的變化。一個健康的企業必須按照國家(法定)的游戲規則運營,比如數據造假的問題就讓文娛行業深受無序競爭的困擾。數據都不對,怎么來評估,怎么來投資,怎么來運營?
在健康的市場經濟國家,一個行業經過多年的發展之后會自然而然形成健康的體系化的做法,這是娛樂工業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影視行業還是體育行業,藝人或者運動員的薪酬都有體系,是行業工會和經紀公司等組織之間長期形成某種平衡才達到的。
中國的文化娛樂產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交界地帶厘清彼此邊界,包括建立行業監管、自律和協同機制,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既服從政府監管又能保護投資人的利益,需要進一步探索,并及時根治行業內部某些亂象。
還有一個是市場的開放與管制。相較其他行業,整個娛樂、體育行業都得不斷開放,很多東西都在逐步放開,很多制度也在不斷搭建。其中有些規則不能僅僅由政府制定,還要靠行業自身在市場化過程中逐漸形成。
南方周末:你在2018年國際文創產業合作伙伴大會上表示,國內文娛行業普遍存在公司估值虛高的問題。據你的觀察,這種估值泡沫有多嚴重?有觀點認為,內容創業的風口已經過去。目前的投資是否正在日趨理性?
黎瑞剛:互聯網的技術驅動改變了整個技術和產業格局,創造出很多內容生產的新模式和新業態,有一些過去的游戲規則不適用了,政策監管也遇到新問題。再加上這些年資本熱錢不斷涌入,推高了文娛行業的資產價值,有些公司的市場估值出現了泡沫,這些問題是存在的,市場的理性調整早晚會擠破這些泡沫。現在,這些問題與行業大環境遇到的問題交集在一起,深度調整也就成為必須經歷的過程。
積極的一面是市場的真實需求仍然存在,而且被不斷地發掘出來。政策的驅動、城鎮化的因素、大量的新消費群體的出現,這些剛性的市場需求不斷產生。在這種深度調整之中,整個行業需要梳理,政策的監管是必要的,政府的強出手也是必要的。到一定時候,要知道政府不能包辦一切,事實上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行業自身的機制要建立、孵化起來。作為行業主體的企業,無論做投資還是運營,需要從作坊式的、小而全的經營走向規范化、體系化的運營。我認為,體系化運營是中國文化娛樂產業接下來必須面臨的課題。
南方周末:我們回到文化娛樂行業自身,為什么你最近特別強調要回歸體系化運營,而且強調這是個“常識”?
黎瑞剛:在市場亂象得以收斂之后,政府的作用更多的是引導,還是要鼓勵市場主體發揮作用,并得到尊重和保護,尤其是中介組織和專業機構的作用。整個行業自身,必須從作坊式的創業模式,走向更體系化的運營。有了這樣的體系,人才和資本才會源源不斷地進入,內容產品才會穩定而持續地產出。創建這樣的體系,我們才能形成我們自己的行業標準、行業操守、行業規范。美國今天的娛樂工業為什么如此繁榮,其實就是行業體系化,甚至工業化的實踐。
文化與娛樂產業要往前發展的話,需要一個體系化的運營,一時一地,有時候創造一個內容的爆款是容易的,但是你要可持續地創造爆款,不斷創造精良的內容,在用戶中獲得持續的影響力,這需要一個持續的體系塑造。
“技術強驅動是 今天產業格局的 基本主題”
南方周末:一份資料顯示,目前CMC參與投資或運營的相關公司達到98家,但是內容資訊類的,特別是有傳統媒體背景的卻僅有財新傳媒、華尓街見聞、華生傳媒等幾家,對內容性公司,你如何篩選和投資?
黎瑞剛:確實,類似財新傳媒,有傳統媒體背景的越來越少。我們早年成立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2010年)曾經投資了一些內容性公司,比如綜藝領域的燦星制作、動畫領域的東方夢工廠等等,這兩年又投資了喜劇領域的笑果文化,但是后來這類內容偏重公司就很少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偏重技術驅動的,內容和平臺結合的公司,比如愛奇藝。
傳統媒體出來的團隊大部分是做內容的,在數字媒體時代的今天,另一類有話語權的是有技術基因的團隊。有一些技術創新的團隊可以說不關心內容,只是做一個平臺,技術驅動平臺、技術抓取內容、技術分析用戶消費習慣,在后臺做很多算法,他們成為行業中間新的主要的驅動力和贏家。美國也一樣,迪士尼(1926年成立)干了多久,時代華納(前身1903年由華納兄弟創立)干了多久,奈飛(1997年成立)又干了多久?這些公司的估值目前又是多少?。
南方周末:既然傳統的內容公司不再是投資重點,那么未來CMC的投資和運營如何做加法和減法?
黎瑞剛:技術強驅動是今天產業格局的基本主題。往平臺業務走,如果是從內容基因出發的話必須完成蛻變,徹底擁抱技術,自己要變成技術上的狂人;如果你做不到,就要招一批技術的強者,幫你做驅動,做產品創新、后臺技術的創新,才可能往平臺做;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的話,認識到技術的價值和意義,能夠發揮自身的內容優勢,在一些模式上進行創新,也有一定的機會,當然,這是不同的等量級。
南方周末:你剛才說的這兩類平臺,技術驅動型和內容+模式創新型,核心都是技術,你的意思是,模式創新也是帶有技術驅動的創新?
黎瑞剛:純技術的驅動可以做一個非常大的平臺,大量的用戶被吸附;另外一種平臺,是有一定的技術驅動,但本質上還是內容基因,這種媒體模式有創新的可能,邱兵他們做的梨視頻就屬于這種類型:內容基因,技術上不斷進行革新,一端是產品的用戶友好性,另外一端是后臺技術;最有價值的是他們的全球拍客系統,不僅有模式創新,還有門檻和壁壘,這個系統目前管理六萬多個拍客,包括注冊和收費服務,背后是機器、算法系統在驅動。
南方周末:“快手”的草根色彩很濃,也“制造”了不少平民網紅,不過有些內容曾經受到爭議和批評,這筆投資主要是看重它的技術?
黎瑞剛:“快手”主要是一種內容消費模式,大量的內容上傳背后有很強的技術基因,它創造了一個去中心化的短視頻的社區結構,用戶創建內容,后臺做算法,社區很有生命力。當然,有些內容需要一些調整和管理,事實上,他們對內容的調性、監管,包括對內容反映的社會價值,也在不斷反思。
如果違反了社會道德甚至國家法律,內容造成了社會危害,肯定要接受批評、整改甚至取締。有些內容涉及年輕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趣味,也許未必有多少價值,但是如果不違反國家法律,不對社會造成危害,今天的社會應該包容它的存在。就像當年我們讀金庸、王朔的作品,社會上剛開始也有不少意見,我當時說,像王朔,就是用嘻嘻哈哈的方式,瓦解了一些傳統、陳舊的觀念性的東西。?下轉第20版
?上接第17版
任何一個媒體都有一個成長過程。技術、年輕人、新的消費市場,在驅動社會發展。“快手”通過技術創新,讓千百萬沒有發布內容創新渠道的人獲得了平臺,讓他們的才智獲得創造,變為價值,也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這是很有價值的。
南方周末:作為投資人,你會對“快手”這樣的公司提一些內容方面的建議嗎?
黎瑞剛:我們是基金投資。基金投資獲取少數股權,一般不會介入到投資項目的運營。但我很樂意與這些被投的企業團隊交流。集團公司的項目,我們才會強運營。
“商業邏輯的背后 還需要人文的邏輯”
南方周末:2018年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上,傳統的好萊塢電影不再一枝獨秀,華人文化主導的暑期中美合拍片《巨齒鯊》,全球票房突破了5億美金,國產現實題材電影《我不是藥神》《無名之輩》等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中國導演講故事的能力是不是提高了?未來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收入還能保持高增長嗎?
黎瑞剛:《巨齒鯊》這部片子,華人文化有70%股權。美國電影對全球市場有要求,現在已經變成標準化的全球產品,可它首先是拍給美國觀眾看的。中國電影成長速度很快,但影視娛樂行業考慮的首要問題,是把人性的價值拍透,把自己的作品拍好。未來,好的中國影片一定會不斷涌現,這是大趨勢,對此我非常樂觀。
電影最重要的是故事。對故事的結構,老一輩電影人接受的電影美學教育偏文藝片,而商業片的故事結構是有模板的。現在,年輕的這一波電影人已經成長起來,其中有些在國內受過專業教育,有些在美國等海外高校學習后慢慢回來,有些通過研究國外電影、英劇美劇等自學,再加上目前香港的電影導演在內地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當中國內地的導演在接受蘇聯電影美學教育的時候,香港導演則在邵氏兄弟、嘉禾這些電影公司消化西方商業片的做法,做港片,典型的商業化模式。他們將這種模式帶進來,主流的元素加上商業片的制作邏輯,產生了不少爆款作品。
另外,不要低估今天在學習內容創作的年輕人以及在海外留學的人,他們對內容的理解已經跟老一輩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很會講故事,也能夠生產出很多有正能量價值觀的影片。
南方周末:知識付費正在成為新的風口。作為一家機構媒體,財新傳媒也開始進行原創新聞內容付費。對此,你和財新的運營團隊是否有討論?國外一些知名媒體更早進行內容付費的研究和嘗試,比如《紐約時報》、《經濟學人》,數字付費收入都相當可觀。你如何看待媒體內容付費的前景?
黎瑞剛:財新傳媒做付費服務我是全力支持的,這個制度開董事會時我們也討論過,有很多的業務交流,具體產品的開發是他們團隊做的,我也提了很多意見。用戶體驗,包括產品的適用度、便捷度是否更符合互聯網的特性,他們還要多動腦筋。有時候做內容的,和做互聯網產品的人群不太一樣,對產品的敏感性、用戶的體驗,感覺也不太一樣,但是對內容付費,我絕對贊成。
我當時也說過,媒體廣告往下走,不是偶然現象,是行業趨勢的問題,未來肯定要有一些模式創新。當然,內容付費并不適合所有的媒體,只有品牌媒體,或者高附加值的品牌媒體才有機會。目前,國內能夠做內容付費的媒體不多,只有那些持續擁有影響力、受眾高度認知的媒體;內容有獨特性、稀缺性的媒體,用戶才愿意埋單。
南方周末:無論過去做傳媒,還是現在做文娛、科技和消費,你都特別關注頭部內容,而且強調頭部內容要有三個元素:專業精神、人文關懷、理想主義。為什么?
黎瑞剛:過去這幾年關注內容產業,我和我的團隊經常講,要關注技術驅動的、平臺性的內容企業。中國在發展和進步,互聯網技術創造了一個新的內容生態環境,從最早改造內容傳播的模式,到今天用算法推介、用戶分析,到人工智能等等,都使內容的傳播方式、用戶跟內容的互動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這是今天中國傳媒業、娛樂行業內容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主題。
除此之外,我們非常關注頭部內容、頭部內容企業、生產頭部內容的團隊。因為我們相信頭部內容永遠對于內容產業的發展、社會進步,有積極的正向的推動作用。而對于這些頭部內容,我們一方面關注它的商業價值,這些內容需要有好的票房、好的點擊量、好的用戶反饋,包括廣告價值等等,這些都是商業的邏輯。但是,商業邏輯的背后還需要人文的邏輯。也就是說,這些內容在價值觀、人文關懷、理想主義的層面,或者是背后,能夠傳遞人類共同的一些價值和情感,它的影響應該是持久的,它對人類心靈的影響力和打動力,能夠長時間延續下去。
這些頭部內容以及生產這些內容的團隊,是我們在過去這幾年中間努力發掘、培養、孵化的對象,我也希望這些內容慢慢成為行業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些優質內容能不能在中國成為一種支柱性的產業,成為一種軟實力,甚至在國際上形成影響力,一定要靠技術。
未來的格局中,內容行業必須要有技術的基因。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傳遞的內容,它的價值觀、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你如何詮釋和表達,在未來也是文化競爭力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