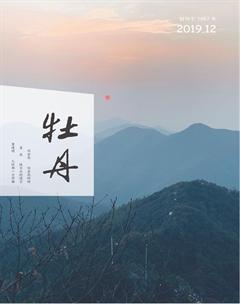談高建群的“作家地理”

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標志,甚至一位作家重要的藝術才能,往往表現在對鄉村生活經驗和地域文化哺育的書寫、對土地的迷戀和對鄉愁的難以割舍等,這幾乎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多數中國當代作家都是“地之子”。高建群無疑也是這樣的作家。評論界對于高建群的研究,也多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立論,把他視為地域文化的表現者。但事實上,僅僅認識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高建群的文學已經形成了獨具美學意義的“作家地理”,進而構成了一個自足的文學世界。
一、所謂“作家地理”
高建群曾提出“作家地理”的概念:“這幾年,我在創作中的許多思考和歸納,用現成的文學理論都不能予以指導和解釋,于是腦子里陡然有了一個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學意識。比如《白房子》中那個我生活過5年的白房子;我的長篇小說《穿越絕地》中的我呆了13天的‘死亡之海羅布泊;我的代表作《最后一個匈奴》中的陜北高原。我覺得除了賦予這些地方以理論家所解釋出的文學含義外,它還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學意識甚至是支撐思考、支撐一本書的主要框架……‘作家地理是個有些奇怪的名詞組合,我給它下的定義是:一本作家個人化了的地理圖書。再展開來說,就是寫作者獨特視角中的地球一隅,寫作者主觀意識下的第二自然。再要打個比方,可以舉出福克納筆下的那一張郵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縣;哈代筆下的英國德比郡,等等。”(此處說法不盡準確,福克納筆下的“井底之蛙縣”,公認的說法為“約克納帕塔法”。而哈代筆下的地理背景為“威塞克斯”,而非“德比郡”。但考慮到并不影響本文觀點,下文仍以高建群的說法為準)
無論如何,這種“哲學意識”,這種“框架”,福克納筆下的“井底之蛙縣”和哈代筆下的“英國德比郡”,都不僅僅是單純的一個“地理概念”,作為“作家地理”,它是“寫作者主觀意識下的第二自然”。它不能是純粹地理學意義上的新疆白房子、陜北高原或渭河平原,它應該是在純粹地理學意義基礎之上的一種哲學的抽象、一種美學的創構。當把文學作品最終還原到地域文化層面時,韓偉認為,《最后一個匈奴》“以一種詩意的浪漫的方式,書寫了四個家族、三代人的命運沉浮,勾勒出陜北一個世紀的歷史風貌。這為我們了解陜北,研究陜北歷史文化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文學寫作的視角”(《高建群小說創作論》);王寶偉認為,《大平原》“描寫了渭河平原上高村半個世紀以來的滄桑巨變和高村人的生命走向,尤其是高氏家族三代人所經歷的世事變幻和命運沉浮”(《地域文化視野下的高建群小說創作研究》);楊梅霞認為,《大平原》“通過高氏家族的典型經歷寫出了中國大地上農人的生存史,亦是對農耕文化百年歷史的一次記錄”(《多種文化背景下的高建群小說創作》)。這種看法本身就是對于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對于“作家地理”的粗淺認識。文學畢竟不同于“地方志”,不能僅僅滿足于對地域文化的書寫和再現。
二、“作家地理”的具體表現
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一個屬于“作家地理”的概念,超越了具體的地理所指,而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地理哲學意識”。這一概念就是在其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北方”一詞。作為意象的“北方”以事實上的地理方位為基礎,但在哲學、美學的意義上又遠超于此。正是借助這一概念,高建群就從一個地域文化的再現者,變身成為藝術世界的創造者——他創造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北方”,正如福克納創造了“井底之蛙縣”,哈代創造了“德比郡”。
高建群《大刈鐮》的題詞是:“揮動大刈鐮,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將這收割打包,慷慨地獻給人類!”而“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這句話正是高建群一部散文集的名字。其早期作品《愁容騎士》中就出現了“北方憂郁”的概念:“誰的一生,如果到過北方,并且有幸與一匹馬為伴,那么,自此以后,不論他居家哪里,工作如何,他的身體停止顛簸了,他的思想,將仍然顛簸不停。他會染上一種奇怪的病癥,這種病叫北方憂郁……”《高建群詩選》中有一篇名為《關于北方的沉思》的詩歌,比較典型地體現了他對于“北方”的感受和思考。里面有這樣的句子:“昨天晚上,我夜觀天象/看見北斗七星,正君臨我們頭上/今天早晨,我憑欄遠望/看見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于是,我偷偷地哭了/我感受到了我們居住的北方/它的神秘,它的奇異,它的魔幻/它的詩一般夢一般的力量”;“我的北方是古老的/從祖國最北方的那根界樁起/我走著,像讀一部民族興衰史/一直讀到與南方的接壤”;“詩歌太貧乏了,應當用一曲交響樂/來表現北方的博大和雄壯/表現這大自然奇特的一隅/表現這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北方”;“北方人的性格,正在這冷與熱的交替中/象淬火的生鐵,變得異樣的剛強”;“北方啊,我親愛的北方/我們在你懷里出生,又在你懷里死亡/假如有一天離你而出走/你會用北斗星夜夜為我導航”。散文集《你我皆有來歷》更是用“向北方三叩首”這樣的句子,作為第一輯的標題……相信不用再多舉例了,在高建群的文學作品中,幾十年如一日地強調著一個概念——北方。
三、北方的“憂郁”
總體而言,高建群筆下的“北方”是憂郁之地。這種“北方憂郁”在其作品中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英雄的受難
高建群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懷和英雄主義情結,是喜歡塑造英雄人物、又善于塑造英雄人物的作家,其作品塑造了大量英雄人物,如《遙遠的白房子》中的馬鐮刀、《雕像》中的女英雄蘭貞子、《最后一個匈奴》中的楊作新、《六六鎮》中的張家山以及《統萬城》中的赫連勃勃和鳩摩羅什等。但同時,這些光輝的英雄主角無一例外又都是受難者的形象,具有強烈的悲劇彩色甚至荒誕意味。這是典型的“北方的英雄”“北方的人物”。
(二)胡羯之血的沒落
以早期的代表作《最后一個匈奴》為標志,直到后來的《統萬城》以及《我的菩提樹》等作品,高建群在書里書外形成了一種“匈奴情結”,甚至在生活中都以“長安匈奴”自稱。曾經在北方不可一世的匈奴最后卻神秘地消失在歐亞大陸的茫茫歷史、滾滾黃沙之中。這讓生活在現代城市文明中的作者和讀者都有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和對于當下胡羯之血、匈奴精神沒落的惆悵。
(三)故鄉的消亡
從《最后一個匈奴》開始,高建群的作品似乎已經具備了某種挽歌的性質——“我把每一件作品都當作寫給人類的遺囑”。《最后的民間》《最后一次遠行》,《大平原》《大刈鐮》《我的菩提樹》等都訴說著一個種族、一種精神、一個時代……總之,這是一種精神家園、一種“審美烏托邦”的消亡。高建群的大部分創作,都帶有挽歌的性質,由此也具備了某些悲愴和憂郁的氣質。
(四)饑餓和苦難書寫
中國的北方是多災多難的北方,這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著令人觸目驚心的描寫。例如,《大平原》的敘事主要是饑餓敘事:從花園口像蝗蟲一樣蜂擁而來的逃難人群中,有一個饑餓的小姑娘叫顧蘭子,她因為饑餓而搶奪高二饅頭的事件也必將成為文學作品中描寫“饑餓”的經典場景之一。在高建群大部分的作品中,北方之地都是“豪邁的、不安生的、富有犧牲精神的”,但同時也是“荒涼的、貧瘠的、蒼白的”,北方就是一片憂郁之地。
四、結語
對于高建群來說,從新疆邊陲到陜北高原,再到渭河平原,從詩歌到小說,再到散文,從作家的青年直到老年,他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是關于北方的書寫。高建群以深廣的悲憫情懷、浪漫主義的文學精神和充盈著詩意的筆調,為讀者建構起一個關于中國北方的“作家地理”。這一“作家地理”立足于大西北的地理方位,但又成為一種美學和藝術建構,自足為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
(延安大學西安創新學院)
基金課題:本文系陜西省教育廳科研專項“當代陜西文學中的鄉村形象及其表征意義”(項目編號:17JK1175)、延安大學創新學院科研培育項目“陜西文學中城鄉二元對立敘事研究”(項目編號:2017XJKY-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李冠華(1980-),男,河南扶溝人,碩士,講師,高建群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文藝理論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