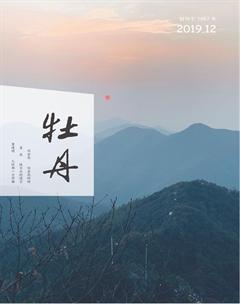花烏世界
中國詩壇和英國詩壇人才輩出,分別出現過兩位偉大的隱逸詩人:中國東晉時期著名的田園詩人陶淵明和英國18世紀浪漫主義代表、湖畔詩人華茲華斯。兩位詩人對自然描寫的方法及最終指向上的不同,反映出他們之間既存在著風格上“古典”和“浪漫”的區別,又存在著哲學指向上“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的差異。這些差異又從深層上反映出中西方哲學思想之間的差異。
一、概述
在中國和英國的詩壇上,分別出現過兩位偉大的隱逸詩人。兩人都醉心于自然:一個飲酒賞菊于田園,一個漫步沉思于湖畔;兩人都以日常生活作為創作題材:一個與尋常百姓把酒話桑麻,一個以深廣的博愛精神體恤著貧苦農民;兩人都突破當時詩歌的樊籬,開辟了一種清新自然的詩歌風格:一個“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一個摒棄了“戴著鐐銬跳舞”的英雄雙韻體(歌德在形容寫格律詩時,說其是“戴著鐐銬跳舞”。英雄雙韻體是一種英國古典詩體,由十音節雙韻詩體演化而來,每行五個音步,每個音步有兩個音節,第一個是輕音,第二個是重音。句式均衡、整齊、準確、簡潔、考究),奠定了現代詩的大眾化基礎;兩人都在本國乃至世界的詩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一個被朱光潛稱贊“可以和之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一個被普遍認同為英國文學史上“繼彌爾頓和莎士比亞之后最重要的詩人”。
這兩位詩人分別是中國東晉時期著名的田園詩人陶淵明和英國18世紀浪漫主義代表、湖畔詩人華茲華斯。兩位詩人選擇了相似的歸隱生活,全身心地謳歌著自然,吟唱著相似而又不同的景物,流露著相通而又相異的情感。
二、差異比較
陶淵明和華茲華斯這兩位詩人都不約而同地將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木,流云飛鳥融入自己的詩中,在草木飛鳥之中,抒發著各自的情懷,有相通之處,卻更有差異。
(一)描寫自然的方法不同
陶淵明愛菊,他的詩賦予了菊花新的內涵,塑造了菊花新的意象。菊花在中國文化中的經典意象可以說就是陶淵明奠定了基礎。自陶淵明以后,文人詠菊成風。元稹在《菊花》中詠嘆“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梅堯臣《殘菊》也贊道“零落黃金蕊,雖枯不改香。深叢隱孤芳,猶得車清殤”。然而無論人們如何詠菊頌菊,其意境內涵終超不出淵明詩中所塑造的“清”“貞”“隱”三種。淵明亦愛鳥。據統計,陶淵明現存詩126首,其中提及鳥的詩就有34首之多。同樣,英國詩人華茲華斯也表現出極其相似的喜好。華茲華斯愛花,卻不限于菊,在他的詩中,野薔薇、水仙、玫瑰、白屈菜,甚至無名小野花,凡鄉間所見,皆可成為其詠贊對象。華茲華斯也愛鳥,僅以鳥命題的詩就有多首,如《致杜鵑》《綠山雀》《詩人與籠中斑鳩》等。
雖然二人都描繪花,描繪鳥,但是描繪手法有一定差異。陶淵明《飲酒》(其五)曰: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在這首詩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短短四句二十字,就包含菊花、東籬、南山、山氣、日夕、飛鳥眾多景物。陶淵明在描繪這些景物時,沒有焦點,也無所謂背景,一切都是悠然之中的偶然相遇,卻構成了渾然天成的整體,和諧、靜穆且悠遠。正如蘇東坡所言:“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由此可見,陶淵明之詩,美在意境。
華茲華斯對景物的描寫,與陶淵明不同。以《詠水仙》為例。在這首詩中,詩人目光顯然一開始有所聚焦,“驀然舉目/我望見一叢/金黃的水仙/繽紛茂密”,接下來詩人的目光顯然一直停留在水仙上,“一眼便瞥見/萬朵千株/搖顫著花冠/輕盈飄舞/”。縱然出現“湖面”“樹蔭”等其他景物,卻只是作為背景陪襯,“在湖水之濱/樹蔭之下/正隨風搖曳”。緊接著,詩人觸景生情:“水仙的歡悅卻勝似漣漪/……/詩人怎能不心曠神怡。”全詩的最后一節,似乎為彌補“我凝望多時/卻思考甚少”的缺憾,融入了詩人的沉思“那是我孤寂時分的樂園”。縱觀全詩,人們不難發現兩位詩人寫景時的巨大差異,陶淵明塑造的是整體意境,華茲華斯描繪的是獨立個體。陶淵明在景中沒有感情的抒發,情與景卻自然融合,不著痕跡,華茲華斯寫景之余不忘抒情,抒情之余不忘思考,與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差別何其之大!
由于兩位詩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著對自然的熱愛,有研究者據此得出結論:陶淵明的詩和華茲華斯的詩一樣,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風格。事實上,人們不難發現,陶淵明的詩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風格,他不像屈原、李白那樣善用奇特瑰麗的想象,抒發著或悲或喜的濃烈情感。德國詩人、文藝理論家席勒在比較“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內涵接近于“古典的詩”和“浪漫的詩”)時指出,素樸的詩源于有限的自然,它是客觀的,不帶個人色彩。而感傷的詩源于無限的觀念,是主觀的,帶有自我反思的;素樸的詩摹仿現實,感傷的詩表現理想。在陶淵明的詩中,菊是菊,山是山,山氣日夕在宇宙中靜穆,飛鳥在歸巢。沒有悲喜,沒有感傷。人們看到的是一幅意境優美的水墨畫,畫中有“真意”,只能意會,卻不能言傳。而華茲華斯筆下的水仙在輕盈飄舞,舞姿瀟灑,水仙的歡悅勝似漣漪。著名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華茲華斯“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屬于典型的“移情作用”,水仙的歡悅實際上是詩人自己的歡悅。德國作家席勒認為,自然賦予素樸詩人“總是以不可分割的統一精神來行動,在任何時候都是獨立并完整的整體”;而對于感傷詩人,自然“從他內心深處恢復在他身上所破壞了的統一,在自身內部,使自己日臻完善,從有限的狀態進到無限的狀態”。陶淵明詩不僅使他筆下的景物構成了統一完整的意境,就連詩人自己也消融在這個意境之中。而華茲華斯不僅用雙眼凝視自然,他的心靈也在感受自然,而且詩人更在借助自己的心靈和頭腦,將更多的內涵賦予他所見到的自然。
因此,筆者認為,陶淵明詩意象完整優美,塑造的是靜穆、典雅的古典藝術形象,具有古典主義的和諧之美。而華茲華斯的詩則偏重“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屬于典型的浪漫主義風格。
(二)描寫自然的最終指向不同
鳥兒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們靈動,自由,充滿生機,自古就承載著人們的夢想與追求。陶淵明詩中,有“日暮猶獨飛”的失群之鳥,有在“冽冽氣遂嚴”時紛紛歸還的飛鳥,有“戀舊林”的羈鳥,也有“欣有托”的眾鳥。陶淵明筆下的鳥兒與詩人的內心、詩人的隱逸世界有著怎樣的關聯?下面以《飲酒詩其七》為例進行分析探討。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壺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這首詩中,有陶淵明最愛的“菊”“酒”和“鳥”。菊與酒是詩人的“忘憂物”。十三年的仕途生涯讓他“久在樊籠里”,因此選擇“復得返自然”的田園生活。然而,詩人畢竟是讀書之人,靠躬耕不足以謀生。“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是陶淵明貧困生活的真實寫照。貧窮,是詩人的一個苦悶之處。讓兒子們“幼而饑寒”,他常常覺得“良獨內愧”。詩人的另一苦悶之處是“雖有五男兒,總不愛紙筆”,所以他也常常嗟嘆自己的“天運”。可見,陶淵明與普通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憂愁,甚至比普通人的憂慮更多更深。然而,詩人又與普通人不同,他最終能夠沖破自己的小世界,發現了“樊籠”之外另一個更加廣闊的天空,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自由,靈魂得到安放,終于實現了調和。“歸鳥趨林鳴”正是詩人質性自然、回歸真我的體現。“歸鳥”即是詩人,“歸鳥趨林”即是詩人歸隱自然。歸鳥在林中才能鳴叫,詩人也只有在自然之中才能發出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歸鳥與詩人物我泯一,歸鳥意象正是陶淵明超逸淡泊的形象,詩人與歸鳥、自然世界與詩人的精神在“歸鳥”的意象中實現了高度統一,詩人描寫歸鳥的最終指向是實現人、精神與自然的調和,最終達到天人合一。
華茲華斯也寫鳥,《致杜鵑》即是名篇之一。詩人從杜鵑的啼鳴聲入手,先是聽到了“歡暢的新客”的“飄忽的聲音”,“這聲音從山崗飛向山崗/回旋在遠遠近近”。接著,詩人從咕咕啼叫聲中尋找到了這聲音對于詩人的意義:“這歌聲卻仿佛向我講述/如夢年華的故事……/至今,我仍然覺得你/不是鳥,而是無形的精靈”。第五、六小節里,詩人回憶了童年時聽到的杜鵑啼鳴以及這聲音對于幼小詩人的意義:“那時,你們的啼鳴/使我向林莽、樹梢、天上/千百遍瞻望不停……/你是一種愛,一種希望/被追尋,卻不露痕跡”。最后,詩人回到現實,邊回憶“往昔的黃金歲月”,邊感慨“如今,我們腳下/仿佛又成了縹緲的仙界/正宜于給你住家”。杜鵑之于華茲華斯,顯然有別于歸鳥之于陶淵明。對于華茲華斯來講,杜鵑已經不是鳥兒,它是一個謎,是詩人童年時就不斷追尋的一個謎,是一種愛,一種希望,因為有了它,腳下的大地成了縹緲的仙界。詩人在描寫杜鵑時,顯然不像陶淵明那樣物我兩忘,而是始終保持自己獨立的視角,無論是兒時,還是現在。人們可以看到詩人對于杜鵑的崇拜、仰慕及追隨,杜鵑不是杜鵑,杜鵑不是純粹的自然景物,杜鵑更不是詩人,它是謎,身上顯然承載了崇高的神性,有一種神秘而仁慈的力量。華茲華斯顯然將自己對自然、對宇宙的思考融入詩句中,認為自然可以開啟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情操,凈化人的靈魂,給人們以希望,自然是道德存在和靈魂的“保姆”“導師”和“家長”。由此可見,華茲華斯描寫自然的最終指向是用自然的神性來啟迪、教導和凈化人們的靈魂。
三、原因分析
以上分析了陶淵明和華茲華斯在描寫自然景物時兩個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存在的原因不是偶然的,不是表面的,而是個人經歷、生活背景、哲學思想乃至宗信仰等綜合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
中國的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觀念長期占主導地位,在這種觀念中,主體與客體不需要區分,人與自然宇宙不存在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人只是自然宇宙的一部分,萬物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因此,在陶淵明的詩中,人們可以發現陶淵明表達這種順化的思想:“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與自然融為一體,是陶淵明秉承的精神追求。在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下,人的主體性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和認同,個體在中華民族中從來都是湮沒在整體之中,或泯然于眾,或消融于自然。在陶淵明的自然詩中,人們可以看到自然萬物的和諧,體會到詩人也融入其中,但人們很難見到景物之外的詩人,獨立的、反思的詩人。對于陶淵明來說,自然是用來欣賞、感受,體驗、愛與順化的,從來不是用來分析的、認識的。因此,詩人明知“此中有真意”,卻“欲辯已忘言”,其實詩人又何嘗“欲辯”?
西方長期以來的哲學思想是“主客二分”的,自然是客體,人才是認識自然的主體,所以西方自然科學比中國要發達得多。華茲華斯歸隱湖畔,從本質上來講是對工業社會種種殘酷黑暗的不滿,是對人道德淪喪的控訴,是對純凈淳樸的自然和崇高精神的回歸。因此,華茲華斯看自然,并不是用“科學”的眼光去認識自然,相反,他骨子里深深痛恨自然科學的發展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在他的人生選擇和詩歌中對自然謳歌、對貧苦人民的同情方面都有所體現。然而,“天人相離”“主客二分”這種思想,這種看待自然的角度,華茲華斯還是毫無保留地傳承下來。在置身自然、贊嘆自然一草一木的同時,華茲華斯從來就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存在。無論是《瀑布于野薔薇》《綠山雀》還是《詠水仙》,“我”都是獨立于風景之外的:“我真害怕——/唯恐它方才說的那番話/會是它的最后遺言”“弄得我眼花繚亂/錯把它看成綠葉一片”“驀然舉目,我望見一叢/金黃的水仙”。在這些例子中,人們都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詩人看風景時的靜觀態度,自己和風景顯然是互相獨立的,詩人的情感雖是由景而生,卻終不像陶淵明與自然之間那般默契。
中國的美學思想是講求含蓄婉轉,是一種模糊的遠景思維模式,任何過于直白具體的描述就會破壞“意境”,所以國畫多留白,詩歌也講求語言情感上的留白,一旦表述圓滿或直接道破,反而喪失了“意境美”。陶淵明的詩即具有這種“意在言外”、人與自然合一的高遠境界。而西方的美學思想恰恰相反,它直接具體,是一種清晰的具體思維模式,通過對具體細節的刻畫塑造形象,所以西方畫多人物豐滿立體,傾向于寫實。了解了這一點,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華茲華斯不惜筆墨用一首詩來詠贊一種生靈,而陶淵明卻擅長用眾多景物來構建一個意象,為什么華茲華斯在詩歌中會直抒胸臆,快樂就是快樂,憂傷就是憂傷,留給讀者深刻的共鳴,而陶淵明卻只能“借景寫意”“情在意中”,留給讀者的是無盡的回味。
四、結語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能夠平等共存的今天,對文化、文學進行比較無疑對促進各國交流和溝通、增進彼此理解、消除民族隔閡和偏見,增強文化自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需要人們摒棄兩種不良傾向:一是一味地仰望他人文化,用一種自卑心理來看待本土文化。這種視角勢必會扭曲自己傳統文化,使自己走向“文化侏儒癥”;另一種是以自我為中心,拒絕接受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在對陶淵明和華茲華斯這兩位東西方詩人(一個生在文化燦爛、歷史厚重的中國,一個長在文藝理論哲學思想高度發達的歐洲)進行比較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對兩位詩人尤其是華茲華斯有了更加理性、更加客觀的認識。對兩位詩人和作品意象的比較,旨在加深認識,增進文化互補和交流,在世界文化多元性和多樣性的背景下,弘揚優秀的中華文化,彰顯其個性和特色,使中華文化能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
(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基礎部)
作者簡介:耿小敏(1976-),女,上海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