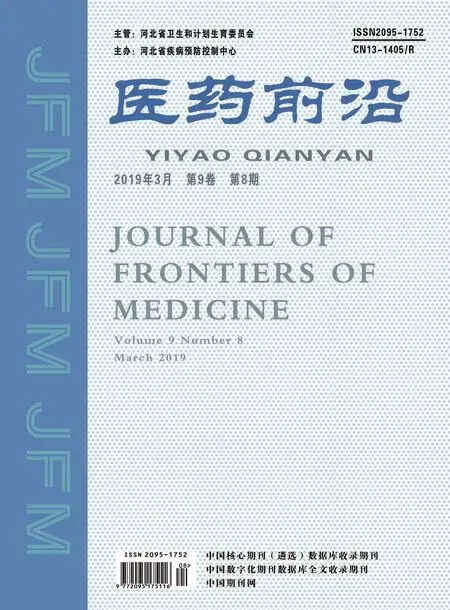國內外微出血研究現況及分析
吳紹怡 沈比先, 許首英
(1廣東醫科大學研究生學院 廣東 湛江 524019)
(2深圳市南山區人民醫院 廣東 深圳 518000)
1.研究背景
CMBs的釋義:微出血(Microbleeds)初步得到國內外共識是在2009年,Greenberg SM[1]在《Lancet》發表《CMBs的檢測和解讀指南》。目前CMBs也被懷疑發生在關節、腎臟或其它組織中,但大多數文獻只涉及腦微出血(Cerebral Microbleeds,CMBs)。CMBs的臨床定義為腦內微小血管病變所致,以微量出血為主要特征的腦實質亞臨床損害(目前認為在腦干部位也可有急性表現)。國外的影像定義為各種MRI序列出現的圓形低信號的定義明確的病灶,排除較大的血腫或出血、特定的繼發性出血原因,以及非出血性信號缺失的其它原因。我國根據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最新標準[2],把CMBs影像定義為在T2*加權梯度回波序列(T2*GRE序列)和其它對磁化效應敏感的序列顯示出以下變化:①小圓形或卵圓形、邊界清楚、均質性的信號缺失灶;②直徑2~5mm,最大不超過10mm;③病灶為腦實質圍繞;④T2*GRE序列上顯示“暈染效應(blooming effect)”;⑤相應部位的T1、T2序列上沒有顯示出高信號;⑥與其它類似情況鑒別,如鐵或鈣沉積、骨頭、血管流空等;⑦排除外傷彌漫性軸索損傷。
2.CMBs的組織病理學改變及發生機制
CMBs的病理學主要表現為小血管損傷引起血液不同成分的微量聚集。發病機制可能為血管內皮細胞功能和血腦屏障損害導致小血管結構改變(血管壁增厚、結構破壞甚至最終破裂)和血管周圍改變(水腫、周圍間隙擴大、組織損害)。其中高血壓患者CMBs病理改變主要表現為小動脈玻璃樣變性引起的動脈粥樣硬化,腦淀粉樣血管變性(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CAA)患者CMBs主要表現為淀粉樣物質在小血管壁沉積,導致血管彈性喪失、管腔變窄或擴張、血管脆性增加;放療后CMBs主要由血管源性水腫、細胞毒性水腫引起的血管內皮損傷,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MRI磁敏感序列(T2*GRE或SWI序列)低信號主要是含鐵血黃素或吞噬含鐵血黃素的單核細胞沉積在變性的小血管周圍 。最新研究[3]顯示CMBs的組織病理學是可變的,包括含鐵血黃素的順磁性作用、紅細胞和血管病變,具體機制仍需要放射學--病理學相關性的進一步證實。
3.CMBs的檢測方法及影響因素
3.1 檢測方法
現階段檢測CMBs的常用MRI序列以Simenz公司的T2*GRE 序列和SWI序列多見,GE公司隨后也推出ESWAN序列、SWAN序列,均是利用不同組織間磁敏感性的差異產生信號對比的原理,其中后三個序列均是在T2*GRE序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已有大量文章證實其磁敏感度和對比噪聲比(CNR)都較T2*GRE序列顯著提高。CMBs在磁敏感MR序列SWI重建圖像上表現為圓形低信號,相位圖在左利手MR系統表現為正向位移,呈現呈均勻高信號,周圍環繞低信號環,在右利手MR系統則相反。
3.2 影響因素
磁敏感序列掃描CMBs具有暈染效應,即圖像顯示CMBs的體積比實際體積更大,且不同磁場強度、不同層厚、不同回波時間(echo time,TE)、不同時期的放大效應相差甚遠。磁場強度越高,越依賴于最佳體素縱橫比(1.5T以下機器除外,具有各向同性體素),放大效應越顯著。層厚越薄,放大效應越顯著。使用較長的TE可以檢測到更多的CMBs,但小的CMBs越難與背景噪音區別。MRI對超急性期及急性期的CMBs磁敏感放大作用較弱,對亞急性期及慢性期的CMBs存在較強的磁敏感放大作用,可能與強順磁性物質含鐵血黃素的沉積有關。因此,MRI檢測到的CMBs總數依賴于MR成像技術,較小的層厚和較高的磁場均可使CMBs的病變對比度明顯增加。
4.CMBs相關疾病的發病率及研究方向
據現有國內外文獻報道,CMBs的患病率在健康人群中為3%至15%,患病率具有地域性且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從40歲至45歲的6.5%增加至≥80歲的患者的35.7%[4]。CMBs相關疾病研究主要集中在廣泛應用MRI的神經影像學領域,不同疾病群體的發病率均與臨床相關癥狀有一定的統計學意義,提示CMBs可能參與該疾病的發生或進展過程。其中,在腦卒中群體中,不同類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CMBs發生率約為26%~69%,CMBs在腦出血患者中的發生率平均為60.4%[5]。高血壓患者中CMBs的發生率平均為30.2%[6]。阿爾茨海默病[7](AD)患者中含ApoE4者有17.5%發生CMBs,而不含ApoE4的患者為10.1%。輕度創傷性腦損傷[8](TBI)患者有86.7%的皮質或皮質下CMBs,但存在間期改變。
5.CMBs國內外研究共識
5.1 CMBs與30多種病癥有關,現國內外學者大部分臨床實驗結果均對老年、男性、高血壓、攜帶載脂蛋白E4(ApoE4)基因是CMBs的獨立危險因素持高度共鳴,Igase、Fan等的研究提示CMBs與收縮壓、舒張壓均呈正相關;位于19號染色體上的純合子ApoE4基因與CMBs的發生密切相關。
5.2 CMBs皮質下位置分布特點有助于特定疾病的診斷,CAA、AD患者CMBs多位于腦葉皮質下,高血壓患者多位于深部腦白質(基底節、橋腦、小腦)、SVaD患者多分布在丘腦、腦干、小腦,伴皮質下梗死及白質腦病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CADASIL患者通常CMBs位于丘腦、基底節、腦干;TBI患者通常位于胼胝體和灰白質交界處。
6.CMBs的臨床意義與臨床決策
6.1 CMBs是引起老年人首發皮層-皮層下顱內出血(Intracranial Hemorrhage,ICH)與溶栓治療后的ICH的獨立危險因素。馬林等人的研究顯示CMBs與老年人深部ICH密切相關,同時有CMBs的患者卒中復發或短暫性腦缺血(TIA)發作的風險增加,但卒中復發與缺血性卒中的關聯性較小,提示腦卒中復發有CMBs的患者自發性腦出血的風險可能大于缺血性的風險。影像學評估罪犯血管(BBB)通透性和側枝循環是預測出血轉化的核心問題,目前聯合動脈自旋標記(ASL)技術可預測腦卒中后再灌注和側枝循環狀態,若出現高灌注提示腦梗死后出血轉化的保護性因素,可預測潛在出血風險,指導臨床決策。
7.結論
高場強MRI及磁敏感成像技術的使用使CMBs的檢出率增高,我們在分析和解釋CMBs前需要熟悉相關指南,除了警惕CMBs假陽性,CMBs空間分布特征亦有助于相關疾病的鑒別診斷。CMBs是無癥狀社康老年群體ICH和卒中患者再出血的警示,并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臨床治療的決策,但具體疾病需要具體分析,以做出最有利于提高患者生命質量和遠期預后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