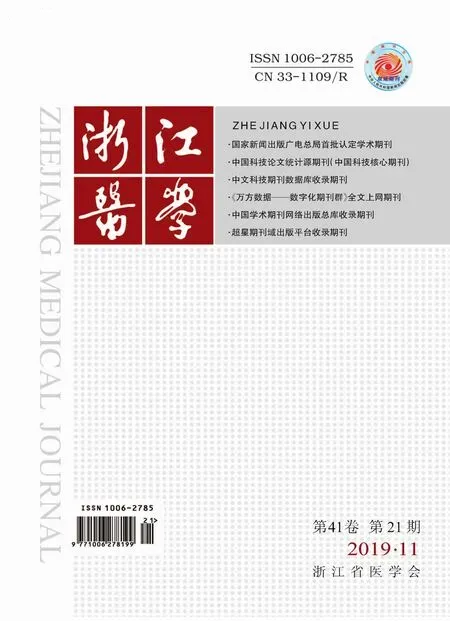血管因子與子癇前期研究進展
王正平 薛夢玲 王玉慧
子癇前期是一種妊娠相關的疾病,特點為孕20周以后出現高血壓、蛋白尿等臨床癥狀,嚴重影響母嬰健康,是引起孕產婦死亡、早產、宮內生長受限、胎死宮內的主要原因之一,發病率約為5%~7%[1]。關于子癇前期的發病機制至今仍不明確,因此治療手段有限,終止妊娠才是防止母胎并發癥進一步加重的根本解決方法。很多學者致力于研究子癇前期的發病機制,目前普遍認為胎盤的異常發育是子癇前期發生、發展的關鍵環節,其中血管因子失衡在胎盤的發育異常、子癇前期發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關注。本文就血管因子與子癇前期的研究進展作一述評。
1 子癇前期與血管因子及胎盤的異常發育
子癇前期癥狀可隨著胎盤的娩出而緩解,因此很多學者認為胎盤在子癇前期的發生中發揮作用。在正常妊娠中,胎盤形成的關鍵為螺旋動脈的重塑。這個過程有3個重要的階段:(1)與滋養細胞侵入無關的血管改變;(2)血管周圍間質絨毛細胞參與的血管重塑;(3)滋養細胞侵入螺旋動脈[2]。之后子宮胎盤血管發生一系列的改變:(1)血管彈性消失;(2)血管擴張,管腔增寬,不具有收縮性;(3)不受母體血管舒縮的控制。這些改變能夠降低胎盤血管阻力,增加胎盤灌注,保證母體血流至胎盤[3]。而在胎盤血管形成和螺旋動脈重塑的過程中,血管生成因子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研究發現,細胞滋養細胞以通過生長因子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分泌誘發早期血管的形成,并在妊娠早期控制著血管侵入子宮肌層。該研究提到,妊娠期間子宮胎盤血管形成的第一階段是第20~21天,而該階段胎盤是處于低氧狀態的,且該時期可見VEGF的高表達。因此可以認為在胎盤血管形成前,胎盤處于低氧狀態,從而誘導細胞滋養細胞產生生長因子(如VEGF),促進胎盤早期的血管形成、滋養細胞的增殖分化和入侵、螺旋動脈的重塑,以增加胎盤血流量[4]。而在子癇前期的發生中,由于胎盤異常發育引起的胎盤低灌注被普遍認為是其首要發病機制。曾有實驗室建立了一個“降低子宮灌注壓力”的小鼠模型,妊娠第14天(小鼠妊娠時間共21d)鉗夾主動脈和卵巢動脈阻斷其40%的胎盤血流,發現在妊娠第19天小鼠出現平均動脈壓升高,GFR降低,尿蛋白,內皮紊亂等類似于子癇前期的癥狀[5]。這與子癇前期患者胎盤低灌注的理論是相符的,而胎盤血流量的減少可能與血管形成不足、螺旋動脈重塑失敗有關。有研究發現相較于正常妊娠胎盤組織,子癇前期患者胎盤組織中的血管數量減少[6]。Lyall等[7]研究發現子癇前期患者子宮肌層血管壁內的絨毛外滋養細胞含量明顯少于正常組,子宮肌層螺旋重構存在缺陷,胎盤血流搏動指數增加,這提示可能是由于血管壁中滋養細胞侵入不足引起螺旋動脈重塑失敗,導致血管阻力增加、胎盤血流減少,從而誘發子癇前期癥狀的產生。由此可見,血管因子在胎盤血管形成、調控滋養細胞入侵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發現VEGF和胎盤生長因子(placenta growth factor,PLGF)在子癇前期患者胎盤組織中的表達較正常孕婦明顯下降[6,8-9]。Weel等[10]亦發現 VEGF和 PLGF 在子癇前期患者胎盤組織中表達水平明顯下降,且早發型者比晚發型者PLGF水平更低。VEGF、PLGF的低表達可能可以用來解釋子癇前期患者胎盤血管形成不足、螺旋動脈重塑失敗導致的胎盤血流量減少、缺氧。但也有研究發現VEGF在子癇前期患者胎盤組織中的表達是上升的,認為胎盤低氧狀態誘導VEGF的高表達,同時誘導周圍內皮細胞產生過量的可溶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 1(soluble fms-like tyrosine kinase-1,sFlt-1),其與血清中VEGF、PLGF共同參與子癇前期的發生[11-12]。不同研究結果的沖突可能與樣本量不足、檢測手段不同等因素有關,因此我們仍需要大量的數據進一步驗證血管因子在胎盤異常形成中發揮的作用。綜上可以推測胎盤在子癇前期發病中發揮的作用:子癇前期患者中,可能由于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PLGF表達水平的改變,滋養細胞侵入不足,胎盤血管形成受阻,螺旋動脈重塑失敗從而導致胎盤灌注減少。胎盤缺氧是子癇前期發生、發展的第一步。
2 子癇前期與VEGF
VEGF是一種45kDa的糖蛋白,是血管生成強有力的誘導劑。研究表明,VEGF能夠促進血管內皮細胞的生長[13]。體內模型中也可以觀察到VEGF誘導血管生成的反應[14]。Eremina等[15]的實驗發現,有VEGF-A基因雜合子或純合子缺失的小鼠均因為部分重要血管的缺失而死亡。由此可見VEGF對于血管的生成不可或缺。VEGF還可以與胎肝激酶-1/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2(fetal liver kinase-1/kinase insert domain containing,Flk-1/KDR)結合,通過相應的信號轉導通路誘導一氧化氮和前列腺素的產生,從而引起血管舒張[16],同時參與腎臟的正常發育過程。VEGF-A在成熟和發育中的足狀突細胞(位于有窗孔的內皮細胞間)上均有表達,表達水平的降低可導致內皮細胞窗孔的缺失或減少。Eremina等[15]的實驗發現,足狀突細胞VEGF表達水平異常的小鼠在出生時或18h內即死亡,同時出現水腫(全身腫脹)、腎臟衰竭、嚴重腎小球異常(缺少成熟的內皮細胞)。這可以表明VEGF對維持腎小球正常功能的重要作用。
VEGF 家族包括 PLGF、VEGF-A、VEGF-B、VEGFC、VEGF-D、VEGF-E 和 VEGF-F。VEGF 受體(VEGFR)包括 VEGFR-1(Flt-1)、VEGFR-2(Flk-1/KDR)、VEGFR-3(Flt-4)[17]。VEGF-A在大多數組織中都有表達,其通過與細胞上VEGFR-1和VEGFR-2的結合發揮相應的作用[18]。VEGF的表達主要受低氧誘導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s,HIF)調控[17]。低氧誘導因子-1a(HIF-1a)是對低氧環境作出反應的組分,在氧氣正常的情況下,HIF-1a亞單位被蛋白酶體破壞降解,因此無法與VEGF結合形成轉錄復合體;而在低氧狀態下,HIF-1a亞單位降解減少,與VEGF-A基因上的低氧反應組分結合,促進了VEGF-A的合成[19]。此外還有一些生長因子[如表皮生長因子、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uth factor,TGF)]致癌基因和某些炎癥因子(如 IL-1、IL-6)亦能促進VEGF的表達[14]。妊娠期間VEGF主要由絨毛外滋養細胞、合體滋養細胞、細胞滋養細胞合成[19],在妊娠早期輕度上升以促進血管的形成,孕32~35周左右達高峰,之后降至基線水平[1]。而在子癇前期中,大多數研究發現VEGF水平的降低[1,20-22],低水平的VEGF影響血管生成、血管舒張、腎小球修復等功能,從而出現高血壓、尿蛋白等子癇前期臨床癥狀;但也有研究顯示子癇前期患者血清中VEGF水平升高,根據前述低氧、氧化應激狀態等能夠誘導VEGF表達增加的理論,子癇前期患者由于胎盤灌注減少引起缺氧、氧化應激等反應,誘導胎盤組織中VEGF表達增加,VEGF釋放入血導致血清中VEGF水平升高。同時高水平的VEGF能促進體內sFlt-1的過量生成,sFlt-1與 VEGF結合阻斷 VEGF發揮作用[8,23-24]。Lee等[24]研究發現子癇前期患者體內總VEGF水平是升高的,而游離VEGF水平是降低的。Ben等[1]和Adu-Bonsaffoh等[22]研究發現游離VEGF水平的下降。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子癇前期患者體內VEGF最初的生成是增多的,但是由于sFlt-1的過量生成導致游離VEGF水平的下降,引起VEGF參與的血管舒張、血管生成修復過程受阻,腎小球功能受損,從而出現高血壓、蛋白尿等子癇前期臨床癥狀。
3 子癇前期與PLGF
PLGF是VEGF家族中的一員,和VEGF-A有53%的同源性,僅能與受體VEGFR-1結合。Carmeliet等[25]研究表明雖然PLGF本身不是血管生成的一個有效的誘導劑,但是它可能通過增加VEGF的生物利用度從而增強VEGF的生理作用。這一過程主要包括:(1)促進VEGFR-1和VEGFR-2之間信號的交流(PLGF激活VEGFR-1,隨后促進 VEGFR-2的激活);(2)PLGF 替換與VEGFR-1結合的VEGF,從而使其能夠與VEGFR-2結合;(3)PLGF同源二聚體可以打亂無效VEGFR-1和VEGFR-2異源二聚體的平衡,使更多的VEGFR-2能夠被利用[26]。而目前廣泛認為VEGF的促血管生成、促有絲分裂及促進血管擴張等作用是通過VEGFR-2實現的[13]。在妊娠期間,胎盤滋養細胞是PLGF的主要來源。正常妊娠中,PLGF水平和孕周非線性相關,在妊娠初期呈上升趨勢,孕30周左右達高峰,后逐漸下降至基線水平,協同VEGF參與胎盤血管形成、螺旋動脈重塑、血管擴張等過程[27]。而在子癇前期患者中,大多數研究提示胎盤組織中PLGF水平下降[6,28],血清中PLGF水平亦呈下降趨勢[20,26,29-30],同時由于 sFlt-1 的升高能夠與PLGF結合,可進一步導致PLGF水平的降低。PLGF水平的降低影響VEGF發揮促血管生成、血管擴張、腎小球功能修復等功能,從而出現高血壓、蛋白尿等子癇前期臨床癥狀。
4 子癇前期與sFlt-1
sFlt1是VEGF受體Flt1(即VEGFR-1)的游離形式,缺少跨膜區域和胞內域,能夠與VEGF、PLGF結合從而阻止其與相應受體結合發揮生物學功能,為VEGF、PLGF潛在的拮抗劑[19]。在體內,sFlt-1主要由滋養細胞合成,單核細胞也可以合成,它的作用包括促進血管收縮和加重內皮細胞功能紊亂[31]。動物模型中,sFlt-1的過量表達會引起高血壓、蛋白尿等癥狀,而血漿中sFlt-1的清除則有助于癥狀的改善,因此可以推測sFlt-1參與子癇前期的發生[11]。有學者認為sFlt-1在子癇前期發生中發揮的作用更多是由于對VEGF信號轉導的干擾。Maynard等[32]研究發現,在sFlt-1存在的情況下血清游離VEGF和PLGF水平是明顯下降的,尤其是VEGF水平下降更為明顯,因為Flt1與VEGF有更高的親和力。且游離VEGF和PLGF水平的下降與sFlt-1的上升是成比例的。Maynard等[32]研究的體外模型中,亦是發現sFlt-1能夠抑制由VEGF和PLGF介導的血管生成作用。由此可進一步證明sFlt-1主要與VEGF、PLGF結合降低游離水平,通過影響其發揮正常作用而參與子癇前期的發病。子癇前期患者胎盤組織中sFlt-1 mRNA表達水平是升高的[11,28,32],且血清中 sFlt-1 水平亦升高[11,24,30]。過量的sFlt-1能夠與血液循環中VEGF及PLGF結合,使其游離水平下降,從而阻斷VEGF和PLGF發揮作用,這是目前子癇前期發病機制中重要的一項。
子癇前期患者胎盤組織中sFlt-1表達上調的機制目前尚不明確。有研究表明,VEGF在母體蛻膜細胞表達增加,sFlt-1在相鄰入侵的絨毛外滋養細胞上的表達亦增加,這表明可能是VEGF的增加刺激了sFlt-1的生成。因此可以假設sFlt-1的增加是對VEGF水平增長的反應[11]。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VEGF本身也可引起sFlt-1的表達,通過VEGFR-2直接刺激sFlt-1的生成。一些其他的因子,如HIF-1、血管緊張素Ⅱ、腺苷也可刺激sFlt-1的產生,同時這些因子也被證實可以促進VEGF的表達或者加強VEGF的作用,通過VEGF促進sFlt-1的生成[11]。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在子癇前期中,由于VEGF的表達增加,低氧及氧化應激等作用,引起胎盤sFlt-1的表達增加,產生過量sFlt-1,增加的sFlt-1與血清中VEGF和PLGF結合,阻止其發揮正常作用,從而出現高血壓、蛋白尿等子癇前期臨床癥狀。
5 子癇前期與可溶性CD105淋巴細胞抗原(soluble endoglin,sEng)
子癇前期另外一個重要的機制是TGF和CD105淋巴細胞抗原(endoglin,Eng)間信號交流的異常。TGF有很多亞型包括 TGF-α和 TGF-β。Eng是 TGF-α和TGF-β的受體,在血管內皮細胞和合體滋養細胞表面均有表達,協同心血管的發育,通過一氧化氮合酶途徑,促進血管重塑,調節血管舒張[17]。Eng的編碼基因ENG的突變是遺傳性出血性毛細血管擴張癥1型的原因(該疾病是一種以動靜脈畸形和毛細血管局灶性損害為特征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疾病),ENG基因缺失的小鼠在中孕期因血管生成不良與心血管發育不佳死亡[33]。這些研究均表明Eng在心血管發育中的重要作用。sEng是Eng細胞外域的一個種類,能夠與TGF結合從而阻斷其與細胞表面相應受體的結合來影響Eng發揮相應的血管生成、血管擴張等作用[17]。Venkatesha等[33]研究發現sEng確實能明顯減弱TGF-β1和TGF-β3介導的血管擴張作用,對sEng發揮的作用進一步進行驗證。同時發現sEng能夠協同sFlt-1發揮作用:在sFlt-1和sEng兩種蛋白同時出現時會有比對照組更大幅度毛細血管樣結構的減少。相較于單純sFlt-1組,在sFlt-1+sEng組可觀察到胎盤上更廣泛的血管損傷,包括母胎界面血管的梗死以及更加明顯的炎癥反應。該研究發現在輕度子癇前期、重度子癇前期和HELLP綜合征患者血清中檢測出的sEng水平分別是正常妊娠組的3、5和10倍,胎盤組織中亦有sEng mRNA表達水平的增加。Nqene等[17]和Kleinrouweler等[30]研究也表明子癇前期患者血清中sEng水平是上升的。由此可以推測在子癇前期的發生中,血清sEng水平的增加可以拮抗由Eng引起的心血管發育、血管擴張作用,可以加強sFlt-1的抗血管生成作用,從而參與子癇前期的發生、發展。
6 血管因子對子癇前期的預測及管理價值
子癇前期患者血清中血管因子的變化可早于臨床癥狀的出現[17],因此可嘗試對孕婦血清相關因子進行檢測來預測子癇前期,以及時改善母嬰結局。曾有研究對PLGF、sFlt-1、sEng在預測子癇前期中的應用價值進行分析,發現其中PLGF是最好的預測指標,靈敏度為100%,診斷準確率為70.8%,與子癇前期的相關性分析中 AUC 為 0.684[34]。
Polliotti等[35]的一項病例對照研究結果提示,與相同孕周正常妊娠的孕婦相比,發展為子癇前期孕婦孕中期VEGF和PLGF水平更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與子癇前期發生的相關性分析中發現AUC分別為 0.773、0.799,若將兩者結合,AUC為0.923。提示可以將PLGF和VEGF作為辨別高危風險孕婦的指標,且兩者結合的價值高于任一單一指標。Kleinrouweler等[30]亦進行過相關的Meta分析,該研究中納入PLGF相關的研究有27篇,均可見發展為子癇前期的病例組中PLGF水平較正常妊娠組下降。在15篇評估PLGF檢測靈敏度和特異度的研究中,發現PLGF的OR值為9.0(95%CI:5.6~14.5),具有75%的靈敏度和特異度。19篇關于sFlt-1對子癇前期預測價值的研究提示子癇前期患者在疾病發生前均可見sFlt-1水平的上升,而在其中8篇評估sFlt-1檢測靈敏度和特異度的研究中,提示其OR值為6.6(95%CI:3.1~13.7),具有 72%的靈敏度和特異度。10篇關于sEng的研究提示sEng水平在子癇前期患者體內的上升,OR 值為 4.2(95%CI:2.4~7.2),具有 67%的靈敏度和特異度。3篇關于VEGF與子癇前期的研究發現發展為子癇前期的孕婦都有低水平的VEGF,但是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該項Meta分析提示PLGF、sFlt-1、sEng對子癇前期均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其中PLGF的預測價值相對較高,但3種均不具備足夠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來輔助子癇前期的判斷,因此該文章并不建議將它們單獨用于子癇前期的預測。在1篇分析sFlt-1/PLGF對子癇前期預測價值的文章中,認為將sFlt-1/PLGF設為38來預測短期內發生子癇前期及出現臨床癥狀具有較好的準確性。sFlt-1/PLGF≤38對子癇前期的陰性預測值(1周內未發展為子癇前期、子癇或HELLP綜合征)為99.3%(95%CI:97.9%~99.9%)[6]。Shokry 等[36]研究發現在子癇前期癥狀出現前,即有PLGF水平的降低和sFlt-1水平的升高。將PLGF臨界值定為90.2pg/ml時,對診斷子癇前期的靈敏度為81.5%,特異度為97.2%,陽性預測值為78.6%,陰性預測值為97.6%;將sFlt-1臨界值定為2 305.8pg/ml時,對子癇前期診斷的靈敏度為100%,特異度為98.6%,陽性預測值為90%,陰性預測值為100%。Chappell等[37]研究提出,對于孕35周前的子癇前期患者,低水平PLGF(<第5百分位或<100pg/ml)對于預測哪些女性需要在14d內分娩有較高的敏感性(靈敏度/特異度:0.96/0.55、0.96/0.56),可考慮將其用于對子癇前期孕婦的分層監測及管理。
廣泛的數據表明,sFlt-1、PLGF、VEGF等與子癇前期的發生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因此可考慮將它們作為預測子癇前期發病及輔助診斷的指標。但是單個指標對子癇前期的預測及診斷并不具備高靈敏度或特異度,因此可考慮將各因素聯合進行篩查。不同指標參考值的確定目前仍然需進一步的驗證。
7 小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血管因子的失衡參與子癇前期的發病機制。在子癇前期的發生中,由于螺旋動脈重塑不足(可能是由于胎盤組織上VEGF、PLGF表達水平的變化),引起胎盤灌注減少,誘導sFlt-1、sEng的生成增加。sFlt-1、sEng釋放入血后與母體循環中的VEGF、PLGF、TGF結合,降低血清中的游離水平,阻斷VEGF、PLGF、TGF與相應受體結合而影響它們發揮作用,導致血管內皮細胞功能紊亂,腎小球濾過屏障受損,影響一氧化氮介導的血管舒張等作用,從而出現高血壓、蛋白尿等子癇前期臨床癥狀。上述血管因子在循環中水平的變化可能在子癇前期癥狀出現前即出現,多項研究表明其水平的變化與子癇前期的發生有較強的相關性,故可用于對子癇前期的預測及輔助診斷。但由于樣本量比較少及臨床試驗數據的不足使相關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仍需研究者們更進一步的分析驗證。
此外,是否可以通過降低母體sFlt-1、sEng水平或外源性補充VEGF、PLGF來治療子癇前期,改善母嬰結局,目前并無相關的數據,亦需要進一步的試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