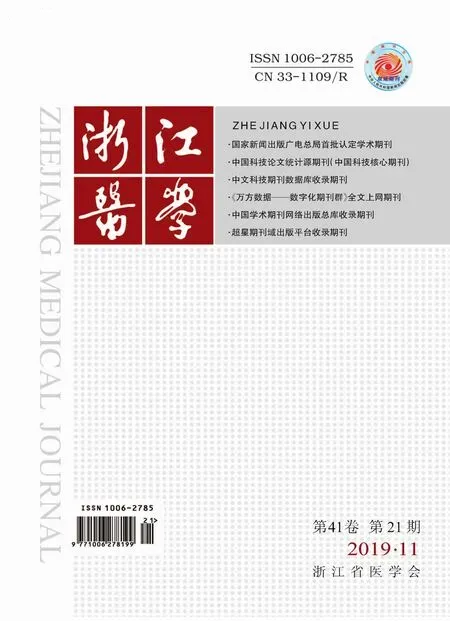上皮間質轉化與炎癥性腸病腸道纖維化研究進展
潘宜久 孟立娜
炎癥性腸病(IBD)是消化系統熱點研究的疾病之一,它主要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C)和克羅恩病(CD)。IBD是一種慢性復發性腸道炎性疾病,腸道纖維化是其嚴重并發癥之一。纖維化是器官或組織慢性損傷后的共同不良結局[1-2],也是最終引起器官功能障礙的最主要的病理生理基礎[3]。近年來有研究表明,上皮間質轉化(EMT)與IBD腸道纖維化之間有密切的關系[4]。
1 EM T的概念
EMT的概念首先由Greenburg等[5]在眼晶狀體上皮細胞的研究中提出來,EMT是指在某些病理、生理以及環境和免疫等因素的作用下,使上皮細胞失去細胞極性,丟失了細胞間連接如緊密連接和黏附連接,獲得間質細胞的表型特征[6]。在形態學上發生由上皮細胞向間質細胞轉變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上皮細胞的表面標志物如E細胞鈣黏蛋白(E-cadherin)、細胞角蛋白(CK)等逐漸減少或者消失,而間質細胞表面標志物如成纖維細胞特異蛋白 1(FSP1)、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A)等逐漸增多[7]。EMT根據其在病理生理學上的不同作用,可以分為Ⅰ、Ⅱ、Ⅲ3種亞型,其中Ⅱ型EMT在組織器官發生纖維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Ⅱ型主要與腸道持續性炎癥反應有關,即在腸道炎癥反復刺激的作用下,表達于上皮細胞中的E-cadherin數量大量減少,細胞間緊密連接遭到破壞,上皮細胞脫離上皮層,穿過炎癥過程中受損的基底膜,導致大量上皮細胞集聚于間質組織中,發生EMT。E-cadherin能維系穩定的細胞連接,其表達抑制或下調可啟動EMT并導致細胞轉移,這也是EMT的特征性變化[8]。
2 EM T與IB D腸道纖維化的關系
反復慢性炎癥刺激腸道導致EMT的發生貫穿于腸纖維化的整個過程。慢性炎癥刺激導致生理性的纖維形成,最終是發生組織修復還是纖維化的形成主要取決于細胞外基質(ECM)的降解與生成之間的平衡[9]。一旦EMT打破了ECM降解與生成之間的平衡,就會導致大量的ECM合成并且異常沉積于腸組織中,形成腸道纖維化。研究表明腸成纖維細胞是產生ECM的關鍵細胞,它的主要來源是組織中的間質細胞、EMT的間質細胞以及骨髓干細胞分化為存在外周血中的纖維細胞[10]。其中EMT而來的間質細胞來源是腸道纖維化形成最主要的細胞來源,也是目前研究者普遍接受的一條途徑[11]。在國外學者的細胞實驗中,采用晚期氧化蛋白產物[12]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13]分別刺激小腸隱窩細胞系(IEC-6),可以觀察到細胞形態由不規則多角形的上皮細胞變為細長紡錘形的間質細胞形態,同時還可以檢測到上皮細胞表面標志物如E-cadherin、CK等明顯下降甚至消失,而間質細胞表面標志物如FSP1、α-SMA明顯升高。由此可以知道EMT的確在腸道纖維化中發揮了作用。另外,Flier等[14]通過基因工程的方法構建出的雙轉基因小鼠,這種小鼠的腸上皮細胞可以表達β-半乳糖苷酶(β-gal,由上皮細胞分泌,通過基因構建得到的雙轉基因小鼠可以同時分泌β-gal+、FSP1+兩種蛋白質),接下來研究者通過三硝基苯磺酸(TNBS)誘導雙轉基因小鼠,使這些小鼠腸道發生炎癥反應進而產生纖維化,結果研究者發現實驗誘導組的小鼠不僅腸上皮區域出現了結腸β-gal+上皮細胞,而且在ECM沉積的區域也出現了大量的結腸β-gal+上皮細胞,為了進一步驗證,研究者統計出了β-gal+FSP1+細胞數大約占FSP1+總細胞數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腸成纖維細胞來自于EMT。同樣,在葡聚糖硫酸鈉(DSS)誘導的實驗性結腸炎的小鼠中也可以得出上述相似的結論[15]。因此,通過上述研究證實了EMT的具體過程以及在實驗性結腸炎小鼠腸道的纖維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為了進一步研究EMT是否也發生在人類IBD患者的腸道纖維化過程中,Flier等[14]將IBD患者的慢性炎癥腸組織標本進行免疫熒光染色,通過觀察可以看到同時含有E-cadherin+和α-SMA+兩種標志物的雙標細胞[16]。同時,CD患者腸道纖維化程度明顯比非IBD腸道纖維化程度重,而且可以觀察到CD患者上皮細胞標志物E-cadherin不僅見于上皮細胞層,還可大量見于黏膜下層以及在纖維化區細胞中也有表達[17]。通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在腸道纖維化區域同時有E-cadherin和α-SMA的表達,說明EMT與IBD患者腸道纖維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Yu等[18]研究可以發現EMT與肝臟的纖維化也有著密切的聯系。此外,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還發現EMT與肺纖維化、腎臟纖維化都有密切關聯[19-22]。因此可以充分相信EMT在IBD腸道纖維化過程中亦具有重要作用,可能是IBD患者腸道纖維化形成的重要機制。
3 EM T促進IB D腸纖維化發生的機制
EMT在分子、細胞、器官水平均參與了IBD腸道纖維化的形成,其中涉及到數量眾多及非常復雜的信號通路和基因調控過程,如TGF-β、Wnt、Notch等信號傳導途徑,其中TGF-β是纖維化形成過程中最為核心的一種因子[23],同時也是所有器官纖維化的強驅動因子,在IBD患者的腸道黏膜組織中TGF-β表達水平明顯高于正常人[24],而且在肺纖維化、肝纖維化的患者中也明顯高于正常人。TGF-β 包括 TGF-β1、TGF-β2、TGF-β3 3種亞型,其中TGF-β1是表達量最多的一種亞型,同時也是與腸道纖維化以及EMT關系最為密切的一種亞型。目前所發現的TGF-β信號通路主要有兩種信號傳導途徑:(1)Smad依賴的通路:Smad蛋白是 TGF-β 信號通路中的中心介質,同時也是EMT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調控因子[25]。Smad蛋白能夠發揮將TGF-β信號從細胞膜上轉入到細胞核內的重要作用,它和TGF-β1因子共同組成的信號轉導通路稱為TGF-β1/Smad信號通路。TGF-β1與其相應的受體結合后,與受體相關的Smad蛋白磷酸化,磷酸化后的相關Smad蛋白形成復合物進入細胞核內促進EMT的發生[26],并且可以誘導鋅指轉錄因子(Snail)、E盒結合鋅指蛋白以及基本螺旋-環-螺旋蛋白質3大轉錄家族。例如Snail可以通過TNF-α-NF-κB-Snail途徑調控腸 EMT,其中 TNF-α 是腸EMT發生的主要促炎因子,也是此途徑的啟動因子。TNF-α激活下游相關因子,啟動骨牌效應的信號傳導,促進核因子κB抑制蛋白(NF-κB)基因轉錄,Snail水平上調,靶向抑制E-cadherin、CK蛋白的表達,促進間質細胞表達 FSP1、α-SMA,最終發生 EMT。(2)非 Smad依賴通路:TGF-β不僅能通過Smad的通路促進EMT,它還能夠通過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如巨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ERK5/BMK1)、p38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c-Jun氨基端激酶(INK)/應激活化蛋白激酶(SAPK)促進EMT的發生。ERK被激活后可以磷酸化一系列蛋白及轉錄因子,并且可以啟動有絲分裂促進細胞增殖。蛋白激酶C(PKC)方式可通過調節基因轉錄來激活ERK信號通路。同時TGF-β還可以激活其他細胞因子和信號通路在腸纖維化中發揮作用。TGF-β可以促進其他促纖維因子(如表皮生長因子、結締組織生長因子等)的分泌,上調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mRNA的表達,從而促進了纖維化的進程。IGF1與TGF-β協同促進成纖維細胞增殖與膠原沉積,并共同參與纖維化過程中ECM的增加和重分布,其表達增加取決于炎癥浸潤的存在和部位,暴露在炎癥刺激中的膠原TGF-β和IGF1的分泌增加。在CD中,TGF-β和IGF1m RNA的表達為透壁性,而在UC中,它們的表達局限于黏膜固有層和黏膜下層。同時TGF-β對結締組織生長因子(CTGF)有明顯的調控作用,在TGF-β作用下腸成纖維細胞表達CTGF增加,CTGF作為TGF-β的下游因子,兩者的相互作用在纖維化中有重要的影響。目前,TGF-β信號通路被研究得較多的是S mad蛋白通路、MAPK通路和蛋白激酶C通路。其中,TGF-β活化的MAPK通路有很強的致纖維化效應。近年來,已經有MAPK抑制劑進行抗纖維化的研究,其抑制劑在對抗實驗性結腸炎小鼠腸纖維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4 小結與展望
EMT在IBD患者腸道纖維化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TGF-β因子及其信號通路是影響EMT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與發生腸纖維化的諸多因素有關聯。根據國外學者Seithel等[27]小鼠實驗研究表明腸道纖維化是一個“自動傳輸”的過程,一旦腸道纖維化發生,即使減少甚至消除炎癥刺激也只能延緩腸道纖維化的發生過程,最終不能夠扭轉腸道纖維化發生的結局。但是如果能夠明確腸纖維化發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具體機制,對預防IBD患者發生腸纖維化及腸道狹窄將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