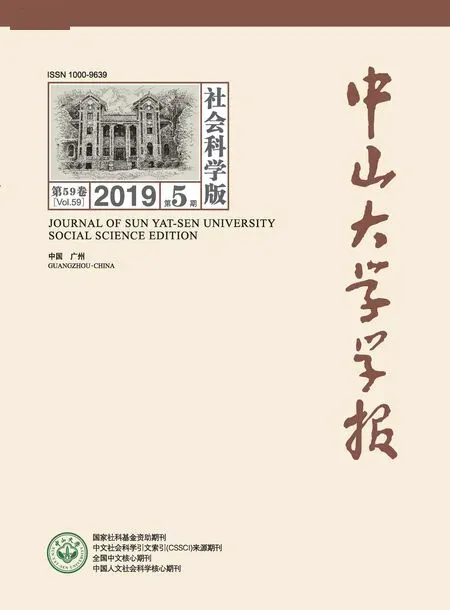新文學運動的邊緣回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
鄧 駿 捷
自明代中后期開始,由于歷史的原因,澳門文化的發展就走上了一條與中國內地不完全一樣的道路,因此具有了自身的獨特性。然而,同族同種,語言相通,交往密切,互相依賴,又使得澳門時時受到內地不同程度的影響。澳門文學是澳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亦應作如是觀。澳門文學的主體——華文文學,明清以來就是中華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其發展過程每每與內地息息相關,如澳門文學的三個繁榮時期,即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和抗戰時期,皆是受內地政治局勢的影響而產生的。另一方面,從文學本體發展而言,澳門文學所受的內地影響,最顯著的例子莫過于澳門新文學的出現。過往一般認為“迄今尚未有發現任何資料,可以說明新文學運動在它最初蓬勃的十年對澳門產生何種影響”(1)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福建: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100頁。;也就是說,澳門新文學的出現不僅較內地遲緩,而且也看不到與內地“新文學運動”間的影響關系,不過事實卻并非如此。
筆者近年整理研究民國時期的澳門文學史料,發現目前所知的澳門最早一首新詩(1920年)、最早的新詩集(1928年)以及第一個新詩作者群。這些發現有助于了解澳門新文學的起源和早期面貌,并可藉以探討新文學運動對澳門文學發展的影響。通過澳門早期新詩的情況,不僅說明澳門新文學的發軔與新文學運動關系密切,甚至可以說澳門新文學是在新文學運動興起的短時間內受其直接影響下的產物。不過,澳門新詩的發展過程卻是曲折的,它反映出澳門新文學的發展受到一定自身因素的制約,并與外來影響形成了復雜的張力關系。
一、澳門新詩發軔尋蹤
澳門雖一度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但地處嶺南一隅,所以華文文學的創作和發展,一直與中國內地大體保持一致。明清時期,基本上是古典詩詞的天下;進入民國,隨著一批清遺民的涌入(其中汪兆鏞是典型的例子(2)李杰:《“誰向虞淵挽夕暉”:汪兆鏞的遺民身份及其自我建構》,《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詩詞的勢力更形重要。而在中國內地,1917月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學。1918年,《新青年》上發表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陳獨秀、唐俟(魯迅)、陳衡哲、李大釗等人的第一批新詩(3)詳參劉福春:《新詩紀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2—3頁。。從此,新文學運動浪濤洶涌,席卷全國,使中國文學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一次革命性轉變。那么,當時以古典詩詞為主要創作手段的澳門文學界對于新文學運動,尤其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新詩,反應究竟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何為澳門新詩?鄭煒明在《澳門中文新詩史略》中,曾經指出“澳門中文新詩作為一個文學研究的概念,應包括兩大范圍:(1)澳門人創作的中文新詩,(2)以澳門為題材的作品”;并據之認為“最早期的一首作品,也許可以追溯到著名的新月派詩人聞一多先生所創作的《七子之歌之澳門》。這首詩為組詩《七子之歌》的第一首,發表于1925年11月”;“至于30年代的澳門中文新詩,我們現在能搜集到的資料仍然屈指可數,大抵有德亢、蔚蔭、魏奉盤和飄零客等幾位在30年代末的幾首作品”(4)鄭煒明編:《澳門新詩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頁。。陳遼亦謂“至少從30年代起,澳門即有詩人從事新詩創作,(如)出生于澳門的華鈴”(5)陳遼:《新詩·現代詩·新現代詩──論澳門新詩的發展軌跡》,廖子馨編:《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年,第98頁。。不過,鄭煒明所舉的例子──聞一多《七子之歌》中的《澳門》,充其量只符合他所指的澳門新詩的第二個范疇,即“以澳門為題材的作品”。因為聞一多先生畢竟不是澳門人,而且從未踏足澳門。故此呂志鵬在遍考眾說,卻困于沒有新史料的情況下,唯有同意鄭煒明的結論;但他又據劉登翰的觀點,指出《七子之歌》中的《澳門》“只是‘關于’澳門,而非本土創作”的新詩(6)詳參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1年,第33—40頁。。那么澳門本土詩人創作的第一首新詩,究竟產生在什么時候,又為誰所寫,是否早于《七子之歌》中的《澳門》?就成為澳門新文學史上一個有待破解的懸案,并且可能觸發對澳門新文學史的重新思考。
(一)《紙鳶》──澳門的第一首新詩
據今所見,澳門最早的白話新詩應是馮秋雪的《紙鳶》(擬題)。它寫于1920年1月,較聞一多《七子之歌》中的《澳門》最少早近五年。馮秋雪是澳門近代商人馮成之孫,馮成長子馮嘉驥之子,長期在澳門生活和居住,是地地道道的澳門人;而且《紙鳶》發表在澳門的文學刊物《詩聲》第4卷第8號的《詩聲附庸》上,因此它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澳門的第一首新詩。
馮秋雪(1892—1969),名平,又名宗樾,字秋雪,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三十年(1905)前后,馮秋雪與其弟馮印雪(1893—1964,名祖祺,號乙盦)、趙連城(1892—1962,名壁如,別名冰雪,后來成為秋雪之妻)一同就讀于澳門培基兩等小學堂。1910年,同盟會在澳門下環四十一號設立秘密支部,又組織“濠鏡閱書報社”。馮秋雪等人參加“濠鏡閱書報社”,成為同盟會在澳門發展的最早成員,并積極投身辛亥革命的各項活動(7)詳參馮秋雪:《辛亥前后同盟會在港穗新聞界活動雜憶》,陳夏紅編選:《辛亥革命實績史料匯編·輿論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第269—278頁;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02—322頁。。民國成立之后,各地同盟會組織日趨解體,“濠鏡閱書報社”不久亦告結束。1913年,馮秋雪與“留澳的當地同盟會幾位會員,便在澳門組織了一個‘雪堂詩社’,寄情吟詠,不談政治”(8)馮秋雪:《中華革命黨澳門“討龍”活動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十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頁。。雪堂詩社于1915年7月開始編輯出版社刊《詩聲──雪堂月刊》,社址設在“澳門深巷十八號”的馮家。自創刊至“庚申年伍月”(1920年6月)第4卷第10號為止,《詩聲》一共出版了4卷46期(9)過往學界對于《詩聲》雜志了解不多,不過近年隨著《詩聲》的重新浮現以及澳門文化局將之全面刊布,其面貌已經清晰地呈現出來了。詳參《雪社作品匯編》第1、2冊,澳門:澳門文化局,2016年。。
雪堂詩社是民國時期澳門第一個以本土居民為主的文學團體,他們結集同道,以“月課”形式進行詩詞創作,在澳門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0)詳參鄧駿捷:《澳門雪堂詩社考述》,《學術研究》2016年11期。。由于“雪堂”以提倡風雅、暢論古典詩詞為宗旨,所以過往不為治澳門新文學史者所注意,然而澳門最早的一首新詩卻出現在《詩聲》之上,不禁令人意外。
《詩聲》從第4卷第1號(1919年2月)開始,增加了附刊《詩聲附庸》,一共10期,分別刊載秋雪、連城合著的《并肩璅憶》、埜云的《云峰仙館讀畫記》以及琴樵的《鼎湖游記》。《并肩璅憶》是馮秋雪、趙連城對少年生活的回憶,每每談及二人相戀、相處等瑣事,情意綿綿。《并肩璅憶》共有兩章,分別是《畫月》(載《詩聲附庸》第4至7號)、《嗚呼紙鳶》(載《詩聲附庸》第8至10號)。《畫月》為馮秋雪所撰,前有趙連城的《憶江南》題詞。《嗚呼紙鳶》為趙連城所撰,前有馮秋雪的新詩一首:
西風起,紙鳶飛滿天,放哩!放哩!的聲,鬧成一片。/斜日照著林梢,好一個天氣已涼,時節又暖。/放紙鳶!放紙鳶!冰姉呀!我要她又高又遠。/不要和人割,恐怕他折我斷。/執定這線兒,注定那眼兒,空中嗎!任爾風云萬變。/紙鳶!紙鳶!你好得意呀!又高又低,又展又轉。/唉!風來了,雨到了,怎樣好呀?冰姉呀!/刮喇!刮喇!疏疏!疏疏!──/哎唷!線斷了,紙鳶呢?沒由尋見。/為什么弄到這樣呀?/都是他不知為人玩弄,翱翔天空,意滿心足。
(九年一月秋雪題)(11)《詩聲》第4卷第8號《詩聲附庸》第8號,1919年10月8日,第23頁。
落款中的(民國)“九年一月”,即是1920年。《嗚呼紙鳶》寫少年馮秋雪爬樹觀看兩只紙鳶空中飛翔,繼而相纏墜落;他在呼叫趙連城(詩中的“冰姉”)時,不慎失足墮地,觸傷頭面。此詩內容與之相應,當是《嗚呼紙鳶》的題詩。然因沒有詩題,暫可擬題為《紙鳶》。此詩結構完整,文字流暢,形象生動,配合《嗚呼紙鳶》的內容,更覺主題鮮明,是一篇較為成熟的新詩作品。
附帶說明的是,《詩聲》第4卷第8號的出版日期標作“夏正己未年八月望日”,即1919年10月8日;然該號附刊《詩聲附庸》上的馮秋雪新詩的題寫時間為1920年1月,兩者相差近三個月。考慮到民國刊物的實際出版時間,有時會較標示者略后,所以馮詩的寫作時間仍以定在1920年1月為宜。由此可見,恐怕不宜再認為新文學運動“幾乎沒有在澳門引起回應”(12)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第99頁。,而是確實有所響應,且速度不慢,至少較香港《小說星月刊》(1924年)上發表的新詩為早(13)參見葉輝《新詩地圖私繪本》,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年,第242頁。。
(二)《綠葉》──澳門的第一部新詩集
如果說只有一首新詩作品,其出現或屬偶然,仍不能反映澳門新文學的早期面貌。那么,在1928年3月出版的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三人的古典詩詞、新詩合集《綠葉》,則大體反映了澳門早期新詩創作的實績和水平。
雪堂詩社在出版《詩聲》第4卷第10號后,因“社友星散,尠獲聚首”(14)黃沛功:《雪社第一集·敘》,澳門:雪社,1925年,第1頁。,基本停止了文學活動。到1925年,馮秋雪重組詩社,并邀梁彥明等人入社,組成“雪社”,社員共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黃沛功、梁彥明、劉君卉、周佩賢七人。“雪社”與“雪堂”的活動基本一致,主要包括雅集、暢游、聚飲、詩課等,但不再編輯出版社刊,而是改為出版社集,“雪社”前后出版了詩集五種(15)《雪社第一集》,澳門:雪社,1925年;《雪社第二集》,澳門:雪社,1926年;《雪社第三集》,澳門:雪社,1927年;《雪花──雪社第四集》,澳門:雪社,1928年;《六出集──雪社第五集》,澳門:雪社,1934年。《雪社詩集》五種,現已全部收入《雪社作品匯編》第3冊,第8—284頁。。
在出版《雪花──雪社第四集》的同一時間,“雪社”還出版了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的合集《綠葉》,作為“雪社叢書之一”(16)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澳門:雪社,1928年。《綠葉》收入《雪社作品匯編》第3冊,第285—340頁。。此書前有古畸、黃沛功的《序》、馮秋雪的《序:我們底〈綠葉〉》和劉草衣(君卉)的《綠葉集題詞》。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分,“綠葉上”收馮秋雪詩10題21首、詞3題3闋、新詩7題9首,合共20題33首(闋);“綠葉中”收馮印雪詩14題22首、詞2題2闋、新詩3題3首,合共19題27首(闋);“綠葉下”收趙連城詩13題19首、詞3題5闋、新詩3題3首,合共19題27首(闋)。其中部分詩詞見于《雪社第二集》《雪社第三集》《雪花──雪社第四集》,當然也有一些新作,相信此書是三人的一部詩詞選集。
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綠葉》收有三人的新詩作品共13題15首,即馮秋雪的《心海》《我愿》《筆》《看書》《小花》《北嶺村口底新葉》《白蓮洞雜詩》(組詩,共3首)(17)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頁。,馮印雪的《梧桐》《天籟》《小詩》(18)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頁。,趙連城的《良夜》《人們底慈母》《記得甚么?》(19)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頁。。它們是澳門新詩史以及新文學史上的重要標志,即是早在20世紀20年代,澳門已經出現了一批新詩作品以及第一個關系密切的新詩作者群。同時也說明了“雪社”不僅是從事古典詩詞創作的文學社團,也是一個新舊文學兼有,嘗試創作多種形式詩歌的群體,這使得它在澳門文學史上的地位更顯特殊和重要。
二、澳門早期新詩作品析論
“綠葉”中的新詩作品,數量不多,而且明顯地帶有嘗試的性質,馮秋雪曾在《序:我們底〈綠葉〉》中寫道:
綠葉,是我們品格的象征;是我們著作的象征;所以拿牠來叫我這本書。
……
我們的詩,仿佛像綠葉。不見得牠有甚么別的色采,不見得牠有甚么可愛。遠看只見一片的蒙蒙地,近才知是一片一片底葉呢!這樣的樸素沖淡,或許是牠們底本色呢!(20)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頁。
由此可見,馮秋雪對于他們的詩詞,以至新詩創作,抱著一種嘗試和謙虛的態度,完全沒有大張旗鼓的意思。至于馮秋雪等人寫作新詩的緣起,古畸《綠葉的序》說道:
我的朋友秋雪先生,對于舊文學極有修養,同時對于近世的科學知識也很多通曉。所以他的為人,有和古人一樣的真摰的深情和照人的肝膽;他的思想和行動,卻又時時站在時代的前面,為一般時代落伍的人物所懷疑──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也是一個理智充實的改革者。感情和理智,在他卻盡量地得到平行的發展。
“抒情的文字大抵古人較今人好”,這句話秋雪也頗以為然,所以他每好作舊體的詩,但他也很相信社會蛻進的結果,今人也自有其古人所無的特殊情懷,不妨拿新的方法寫出來,所以他又作了不少的新體的詩。
……
秋雪深于情,很有詩的情緒修養;就是工具的驅遣,也經過了不少的訓練;宜其新體舊體無不工妙了!
綠葉是他和他的夫人連城女士,令弟印雪先生的合并詩集的一種。他們三人的見解和學問都大略相同;我所說的關于秋雪的話,移給連城或印雪,我覺得還都沒有不適宜的地方。(21)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頁。
馮秋雪等人熟讀古典,對詩詞時耽苦吟,同時又有寫作新詩的情懷,擁有寫作新詩的本領。而且,他們勇于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在新文化運動浪潮中作出嘗試,于是澳門詩壇出現了第一批白話新詩,成為澳門新文學的蒿矢,翻開了澳門文學史的新一頁。
(一)馮秋雪的新詩
馮秋雪的古典詩詞“以淡遠勝”(22)黃沛功:《綠葉集·序》,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3頁。,而其新詩的情感卻不一樣,似乎來得濃烈許多。如《心海》:
我的心海啊!/我深深地擁護著你,/待你也算不薄了!/你為甚的時起瀲滟底微波?/為甚的時起澎湃底洪濤?/使我不得一時的寧息呢?/我愿化作太陽,把心海曝干了,涸了!/要牠變做猶太底死海;/要牠變做蒙古底戈壁。/心海啊!/靜默些罷!
今天已不曉得馮秋雪當時受到了什么刺激,心緒似乎很不安寧,令他急欲讓自己平靜下來。這首詩的情感表達如此強烈且直接,特別是提到要“牠”變作猶太的死海和蒙古的戈壁,形容十分新鮮。
馮秋雪的小詩頗有哲理。如《筆》:
筆對紙說:/“我和你都是給人們役使著呢!/人家對著我們哭和笑,/都不是真的啊!”
此詩借筆對紙的一番話,說明人性的虛偽,同時也點出一切的文字、話語也許都帶著欺騙性。如果沒有深刻的人生體會,恐怕是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來的。
此外,《白蓮洞雜詩》也值得注意。它由《松》《石》《泉》3首組成,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首澳門新詩的組詩。全詩如下:
古松傲兀地立在路邊,/斜睨著過往的行人。/“行人啊!/你們印出底足跡雖是很多,/然而匆匆就模擬了!” (《松》)
兩塊太古底大石,/在一個小澄潭上來接吻;/我們立在他倆底吻下,/惹起了無限底美感! (《石》)
滴滴底流泉!/既滴在石上,/又滴到我底心坎里。/經過石上底雖是無限的清,/但不及滴到我心底無限的涼。/流泉啊!/你自擇吧! (《泉》)
1927年的冬天,雪社諸人相約同游位于香山吉大鄉的白蓮洞(今屬珠海市)(23)周佩賢(宇雪)有《冬日游吉大鄉白蓮洞同觀如臥雪》(二首),見《雪花——雪社第四集·雪花之外》,第55頁。。此處“芳樹陰森,饒泉石之勝”(《白蓮洞雜詩》自注),馮秋雪意緒襲來,寫下了這首既充滿情致,而又飽含哲理的組詩。其中,第一首《松》,從松樹的角度,質問行人——他們匆匆而重迭足跡,究竟有多少的不一樣?第二首《石》寫“我們”在小澄潭旁的“太古底大石”下,仿照它們的形態般“接吻”。第三首《泉》寫泉水的“無限的清”,滴到我心底的“無限的涼”。這組新詩不僅采用了擬人化的手法,更寫到“我/我們”與“物”的對話,反映出馮秋雪藉外物對人事進行思考,頗有一定的思想性。
此外,還有表現馮秋雪和趙連城“閨情”的兩首新詩,寫得十分生動、形象。如《我愿》:
我愿她做堤邊的水,/她愿我做水邊的堤;/朝朝暮暮底吻著——/天哪!她怎的不能變做水?/我怎的不能變做堤呢?
又如《看書》:
黃澄澄底燈光,/悄悄地偷進羅幃里。/手執書本的她,/一頁一頁的展讀;/她底媚眼也隨著一行一行的下去,/也隨著一頁一頁的翻去。/呵!究竟是她底眼隨著一行一頁轉動呢?/還是一行一頁隨著牠轉動呢?
這類新詩通俗淺白,直接表現了秋雪、連城夫婦的鶼鰈情深;而且細味之下,還會感受到句中清晰的節奏感。畢竟馮秋雪深諳詞章之學,精于古典詩詞,所以在寫作白話詩時,仍會自然而然地把握住句子的節奏。這是新舊文學交替時期的新詩特點之一,胡適的新詩如是,陳獨秀的新詩亦如是。
(二)趙連城、馮印雪的新詩
秋雪之妻趙連城,雖然是一位革命女性,深受時代新思潮的影響,但從整體風格看,應屬閨閣詩人一類。古典詩詞如是,新詩亦如是。如《良夜》:
簫聲遠遠地吹著;/月色低低地照著;/樹影沉沉地睡著─/呵!難得底良夜!/可使它和夢各做各的嗎?!
雖是新詩,不過仍是舊詩的作法:前三句寫景鋪墊,最后一句曲終奏雅,略具詩意。另一首《記得甚么?》則顯然屬于“閨情”詩:
黃昏近了!/悄悄地伏在窗闌上。/那年時底游蹤——/一樁一樁的回上心來!/使我永久不會忘記。/記得甚么?/西灣么?北郊么?車廂里底笑聲么?
此詩平白如話,詩意不濃,卻反映了馮秋雪、趙連城夫婦的生活片斷,與上引秋雪詩對讀,可見兩人感情之深。
至于馮印雪,生于澳門,多才多藝,詩書畫兼擅,與高劍父交摯。劍父在佛山創立春睡畫院時,聘印雪為秘書。馮印雪在澳門、香港、越南等地從事教育工作數十年,晚年參加澳門美術研究會,曾任副理事長。印雪逝世周年時,摯友黎心齋等輯其遺詩,劉草衣撰《馮印雪傳》,刊于澳門《華僑報》以為紀念(24)參見《馮印雪先生逝世周年遺詩選輯》,澳門《華僑報》1965年11月29日。。
馮印雪與兄秋雪一樣,性耽吟詠,既嗜古詩,亦嘗試新詩的創作。他有一首《小詩》,可以說是作詩的宣言:
沈悶的黑夜過去了,/燦爛的朝陽再來;/我的朋友,準備著你底柔曼的歌聲,/歌頌自然。
嶺南著名詩人黃節曾評馮印雪的古典詩詞“町畦自辟,造境冷峭”(劉草衣《馮印雪傳》),而新詩則清新可誦。如《梧桐》:
撐著傘似的綠葉——/在熱烈的太陽底下,/布置清潤的綠蔭,/表現牠的人格。
詩人用擬人手法,將樹蔭說成梧桐樹主動“布置”的,以此顯示其為眾生造福的“人格”,詩短意深。又如《天籟》:
人們睡了,/幽悄底雨聲依舊點滴著;/你休要嗔恨,/天籟不是給一般人們頌贊的啊!
這些新詩已經比較成熟,可見馮印雪的文學修養較深,無論舊詩新詩,同樣得心應手。
總之,馮秋雪、趙連城和馮印雪的新詩,數量雖然不多,但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各人的作品亦呈現不同的面貌。這恐怕與他們的舊體詩詞修養有一定的關系,可見澳門的早期新詩并不完全與舊體文學絕緣,甚或可以說,它們與舊體詩詞帶有一定的內在聯系。
三、馮秋雪等人與新文學運動的關系
民國初年馮秋雪等人創作了澳門歷史上的第一批新詩,然而他們的這種嘗試屬于獨立自發的呢?還是受到外來的影響,尤其是與當時中國內地的新文學運動關系究竟又是如何的呢?馮秋雪雖然居住在澳門,但時常往來穗澳兩地,與內地關系甚為密切,不僅很容易接觸到新文學運動的信息,而且的確也曾對新文學運動發表過的意見。馮秋雪曾藉評說胡適《沁園春·誓詩》,對新文學運動表達了一些個人的看法:
挽近文學革新之聲浪,愈唱愈高,此世界潮流之趨勢,無可抑制也。而提倡者,每矯枉過正,余竊病之。嘗于某報,見胡適《沁園春》云:“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月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閉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此詞上半闋,余頗不謂然。夫花何其好,月何其明,春何其麗,秋何其清。景物自景物人自人,惟吾人對之起哀傷愉快者,以所處境而定。人負景物,非景物負人,更非景物奴人……夫觸物興感,人之常情,否則,寡情者也。寡情之人,天性必涼薄,天性涼薄得謂之人乎?胡君見之,當韙余言。至換頭以下,吾無間然。或曰:是達觀語也,子何不察耶?曰:達觀者,傷心之極致也。愈作達觀語,越是傷心無可奈何者。雖然此語我不許,他人藉口代胡君辯護,胡君想亦不如是。蓋胡君張主奮斗進取之人也。主進取者,樂觀派也。既樂觀,則懷舊、幽憂、哀怨種種無由成立;而達觀者,則斯種種之結果也。胡君既無是種種,則達觀何由而生;達觀之念不生,則斯言又何為而發?質之胡君,應亦啞失笑曰:孺子可教也。(25)秋雪:《水佩風裳室筆記》(卅四),《詩聲》第4卷第6號,1919年7月12日,第5—6頁。
首先,在上文中,馮秋雪表示不同意胡適《沁園春·誓詩》上闋的作意,以為“觸物興感,人之常情”,故此“人負景物,非景物負人,更非景物奴人”,所以反對胡適所謂“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的“矯枉過正”之病。其實詞中的“景物”,是借指束縛中國文學的舊有思想(26)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說:“這首詞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胡適文集》第9冊《嘗試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5頁。,而非單純客觀世界的“景物”,秋雪頗有郢書燕說之嫌。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胡適的《沁園春·誓詩》寫于1916年4月13日,后載于1917年3月《留美學生季報》春季第1號(27)胡適:《嘗試集》附錄《去國集》,《胡適文集》第9冊《嘗試集》,第223頁。。其時他與友朋討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意興正濃(28)詳參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見《胡適文集》第1冊《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第148—149頁。。《嘗試集自序》稱它“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29)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文集》第9冊《嘗試集》,第74頁。,可見其于新文學運動上的地位。而從文中對胡適“樂觀”“進取”精神的評說,可以推測馮秋雪所看到的“某報”,應是《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上即載有胡適《嘗試集自序》。由此足以證明,馮秋雪十分注意新文學運動的情況,并很可能讀過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等新文學運動檄文;而在讀到《嘗試集自序》時,意有所感,遂寫下了這篇“筆記”,發表于1919年7月12日出版的《詩聲》第4卷第6號。
其次,馮秋雪肯定文學革新是“世界潮流之趨勢”,無可阻擋,且對胡適“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的呼喚表示認同(“吾無間然”)。這不僅與馮秋雪等人積極進步的政治主張和革命活動有著思想上的內在關聯,也與他們當時在澳門熱切追求各種新的文化思想相一致。如在民國三年(1914),世界語會會員鐘寶琦(俠隱)來澳門宣傳,發起世界語(Esperanto)夏令講習所。秋雪即往學習,并稱鐘寶琦為“傳播斯語于澳門之第一人,予亦為澳門世界語學者第一人。以沉沉長夜之鏡湖而此一瞥之電光,雖轉瞬即渺然亦足自豪矣”(30)秋雪:《水佩風裳室雜乘》(三),《詩聲》第1卷第4號,1915年10月1日,第4—5頁。。此外,馮秋雪又多次請鐘寶琦為宋人姜白石的《齊天樂·蟋蟀》、黃雪舟的《湘春夜月》、蘇軾的《念奴嬌》《水調歌頭》、李清照的《聲聲慢》等詞制作西式樂譜(31)詳見《詩聲》第1卷第5號,1915年11月1日,第7—8頁;《詩聲》第1卷第6號,1915年12月1日,第7—8頁;《詩聲》第2卷第1號,1916年7月1日,第5—6頁;《詩聲》第2卷第5號,1916年11月1日,第6—7頁;《詩聲》第4卷第3號,1919年4月15日,第9—10頁。,可見他們洋溢著以新的形式來改良中國傳統文學的熱情。馮秋雪的思想和行動“時時站在時代的前面”,“是一個理智充實的改革者”,“很相信社會蛻進的結果”(古畸《綠葉的序》);因此他在寫下這篇“筆記”后不久,即創作了澳門的第一首新詩《紙鳶》,切實地響應了胡適所倡導的新文學運動。不僅如此,秋雪還結集弟弟、妻子,不斷嘗試,創作出澳門最早的一批新詩作品,從而成為了澳門新文學的“弄潮兒”。
四、關于澳門早期新詩的思考
馮秋雪等人的新詩創作從1920年至1928年,前后約維持了八年的時間,共得13題16首,成果不算豐厚,而且目前也未發現他們此后有其他的新詩作品。這就形成了澳門早期新文學史上一個頗值得引起思考的現象,即澳門作家受到胡適等人的影響,在新文學運動的最初十年內,開始嘗試創作新詩,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卻淺嘗輒止,沒有堅持下去,更沒有形成風氣。
對于這個現象不妨從澳門當時的文學環境以及馮秋雪等人的文學觀念進行分析。民國初年,澳門文壇主要由汪兆鏞、吳道镕、張學華等一批清遺民詩人以及馮秋雪等本土文人所構成。前者成長于清季,思想上比較守舊,主要以古典詩詞為創作手段。而在“雪堂”和“雪社”中,除秋雪三人外,其他各人均沒有包括新詩在內的新文學作品;就算稍后的30年代,由高劍父、黎澤闿、張百英、張純初、周貫明等革命志士組成的“清游會”開始在澳門活動,也同樣是以創作古典詩詞為主。這就意味著當時澳門無論新舊文人,皆以傳統形式從事文學創作。另一方面,當時澳門沒有出版穩定的文學刊物(《詩聲》是一個異數,故此廣受重視),而報紙副刊也只刊登雜文、小說,或者古典詩詞之類較受一般讀者歡迎的作品。因此說民國初年的澳門文壇基本上還是舊文學的天下,應該是符合事實的。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下,馮秋雪等人勇于打破局面,追上文學潮流,嘗試新的文學形式,無疑更加值得肯定。不過,孤軍作戰,缺乏同道的支援,互相討論的促進,使得新詩創作僅僅是他們家庭成員之間的一種文學實驗,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澳門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
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馮秋雪等人受到自身的文學觀念所制約。他們創立雪堂詩社,主要是針對當時“詩學寖微,風俗人心亦隨之而日下,徒欣歐化,敝屣宗邦,而吾四千年之國粹,竟胥淪于冥冥中”;而出版《詩聲》亦以“專究詩詞,并征佳什以維國粹,庶免詩亡”(32)《雪堂求助小啟》,《詩聲》第2卷第2號,1916年8月1日,第11—12頁。為宗旨。至于重組“雪社”,仍在于“提倡風雅”(黃沛功《雪社第一集·敘》),可見馮秋雪等畢竟是舊學出身之人,對于古典詩詞有著深刻的繾綣,無法也無力完全割舍;而從事新文學活動,只是他們追求進步思想的一個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與此同時,馮秋雪等人雖然向往新的文學形式,但受新文化思想的熏染不深,徘徊于新舊之際,思想上不免時有矛盾。趙連城的新詩《人們底慈母》頗能反映出這種心理狀態:“科學!是自然底仇敵!/自然!是人們底慈母!/慈母啊!我愿永久的躺在你底搖籃里。”崇尚自然與科學精神本無沖突,趙連城卻將它們對立起來,歌頌“慈母”以抗“仇敵”,可見其于新文化的認識還是比較膚淺的。
最后,不能忽略的是,馮秋雪等人基本上沒有西方文學的素養,他們所創作的新詩雖然不是胡適的“白話詞調詩”(33)許霆:《中國新詩發生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7—289頁。,但還是有比較濃烈的古詩氣息。困于傳統文學的慣用手段和指導思想,缺少西方文學的滋養和沖擊,使得馮秋雪等人難以建立起新的文學觀,因而導致新詩創作裹足不前,后繼乏力。反觀稍后出生于澳門的華鈴(原名馮錦釗,1915—1992),1930年在廣州知用中學讀書時開始創作新詩,1935年入讀上海之江大學,同年轉至復旦大學外文系,師從李健吾,其后出版《向日葵》《玫瑰》《牽牛花》《滿天星》等新詩集(34)華鈴:《向日葵》,上海:五洲書報社,1938年;華鈴:《玫瑰》,上海:五洲書報社,1938年;華鈴:《牽牛花》,上海:五洲書報社,1939年;華鈴:《滿天星》,上海:五洲書報社,1939年。,孫玉石將其詩作歸為象征派、現代派作品(35)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04頁。。華鈴又寫作了不少抗戰詩,被鄭振鐸譽為上海“孤島”文學時期中的“時代的號角”(36)參見傅玉蘭《時代的號角——詩人華鈴的生命樂章》,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當然,時代造就了華鈴,但是西方文學的修養,師友的鼓勵,對華鈴的新詩創作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而這一切卻正是當時馮秋雪等人所最欠缺的。以上幾點,或可解釋為什么馮秋雪等人在出版了包括新詩作品在內的《綠葉》之后,就再沒有其他的新文學創作了。
澳門的新詩作品,繼馮秋雪等人之后,直到30年代末才開始再次零星地出現在澳門的一些刊物或文集之中(撇除上述華鈴的作品不算)(37)參見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第41—45頁。,這與馮秋雪他們的創作已經相距十多二十年了。因此,就形成了澳門新詩史上發軔早,起點高,中經停頓,再次起步的曲折過程。雖然如此,馮秋雪等人在澳門響應新文學運動的潮流,創作了澳門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作品,開啟了澳門新文學的局面。雖然受制于外部的文學環境以及個人的文學觀念,馮秋雪等人的新詩創作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但是他們勇于開拓新的文學世界,故此在澳門文學史上的功績不應湮沒無聞,而是需要充分揭示和高度贊揚。
結 語
早在20世紀20年代,澳門已經出現了第一批水平不俗的新詩作品(包括第一首新詩《紙鳶》、第一首新詩組詩《白蓮洞雜詩》、第一部新詩合集《綠葉》)以及第一個關系密切的新詩作者群。這不僅糾正了學術界過往對澳門新詩發軔的認識,使澳門早期新文學的面貌清晰地呈現出來;更加可以反映出在新文學運動的最初十年,澳門文壇對它的接受和響應,加深了解新文學運動在各地擴散和影響的一些具體情況。另一方面,由于澳門新詩的出現和發展,主要是基于外來的文學影響,而缺乏自身的文學土壤和文學環境,所以雖然出現較早,卻是電光一閃,隨即停頓。因此,從總體發展而言,馮秋雪等人的新詩創作在澳門新文學史上呈現出來的現象,正好說明文學發展的一個規律,即缺乏充足的內部主客觀動因(這里包括詩人的個人素養和具體的文學環境),外來力量的作用往往只能是短暫而不可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