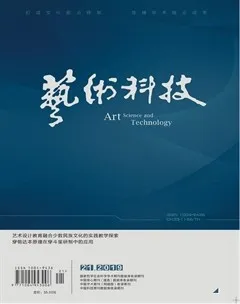淺析朱踐耳《3Y》第一樂章(ye)中核心三音集合的使用



摘 要:朱踐耳先生通過三音組集合將序列音樂寫作技法與音樂動機發(fā)展手法有機整合,以獨特的集合動機拓展了音樂發(fā)展的表現(xiàn)手段。本文從對在原始錄音與管弦樂音響中核心三音集合動機的互補使用方式為切入點,分析本曲集合動機的使用來研究集合動機式作曲發(fā)展手法。
關(guān)鍵詞:核心三音集合;集合動機;十二音序列;調(diào)性序列
0 引言
朱踐耳是我國當代作曲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交響曲10部,序曲、交響詩、小交響曲、協(xié)奏曲等20部,交響合唱《英雄的詩篇》,鋼琴曲,室內(nèi)樂,民樂合奏,等等。而10部交響曲更是朱踐耳先生最具代表性和藝術(shù)成就的作品。其中,《第六交響曲“3Y”》是朱踐耳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受20世紀現(xiàn)代派音樂中具體音樂的影響,將采自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民俗民間音樂與中國傳統(tǒng)樂器、女高音組合形成的Tape2以及西藏喇嘛誦經(jīng)Tape1這兩種原始錄音,通過剪輯、拼貼、變速播放等技術(shù)手段,使用十二音序列寫作技法配合管弦樂隊的交響音樂手法來發(fā)揮作品音響效果以及豐富作品內(nèi)涵而創(chuàng)作的。
1 Ye中原始序列的分析
1.1 十二音序列的分析
例1:
此三音列取自喇嘛誦經(jīng)和中國西南民間音樂的核心音調(diào),內(nèi)部包含大二度、小三度和純四度關(guān)系,有核心三音列3-7[0,2,5]的音程特征,是中國民族五聲調(diào)式音階的截段形式,具有鮮明的五聲性調(diào)性序列特征。
例2:
該作品的原始十二音序列由4個同構(gòu)的三音集合3-7[0,2,5]組合而成,組合順序分別是a原型、b逆行、c逆行倒影、d倒影。在樂曲發(fā)展中,三音集合3-7[0,2,5]起到了主題動機式的功能,其內(nèi)部包含的大二度、小三度音程關(guān)系作為動機因素對音樂的音高材料、結(jié)構(gòu)都起著控制作用。
1.2 十二音序列的移位關(guān)系
例3:
在作品中原始序列和變形移位序列的使用上,主要以核心三音集合為主,由于原始序列設計的巧妙性,移位序列每相隔增四度完全重合。上例是原始序列的移位P2、P8,用弦樂組的4種演奏方法顫音、近琴碼演奏、撥奏、弓桿演奏以自由時值的方式表現(xiàn)。三音列的排列順序為第一小提a、第二小提c、中提d、大提b。通過譜例,我們發(fā)現(xiàn)P2的三音列a、b、c、d和P8的三音列a、b、c、d互成逆行關(guān)系,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原始序列和移位序列P0至P11中只有6組是完全不同的,每隔三全音移位關(guān)系序列中的三音列只是變化重復形式,而沒有發(fā)生音的變化。
由圓號、C調(diào)小號、長號共同演奏出原始序列P0、純五度移位P7以及大二度移位P2。因為兩個相隔三全音關(guān)系的移位間是變化重復關(guān)系,所以我們可以把序列移位看成P0和P6、P7和P1、P2和P8這3對,而此處的序列使用順序具有模仿性,三組序列在排列使用順序完全一致,兩小節(jié)內(nèi)先出現(xiàn)d、a三度音程關(guān)系的縱向排列,再出現(xiàn)c、b二度音程關(guān)系的排列。因為相隔增四度關(guān)系的序列之間只是三音列之間的逆行變化,并沒有發(fā)生音的改變,在和聲中既有原始序列P0、P7、P2的音列順序,又有序列的移位形式P6、P1、P8,造成了我們在分析中只能確定序列屬于哪一對三全音關(guān)系序列。
2 核心三音集合的控制和使用
例4:三段體的變奏曲式
作品大量使用以三音集合為基礎(chǔ)的移位序列,以集合內(nèi)部控制力與主題動機結(jié)合作為樂曲曲式結(jié)構(gòu)劃分與發(fā)展動力的基礎(chǔ)。
例5:第一樂章第48小節(jié)至第52小節(jié)
由原始序列順序?qū)懗傻囊雍臀猜暎褂迷夹蛄幸莆蛔冃味]有加入新的派生序列強化了主題的一致性,三段中并沒有出現(xiàn)樂段的重復或者再現(xiàn)段落。而在段與段之間,錄音的音色加入成為劃分段落的依據(jù)之一,并且序列會以完整的演奏形式呈示出現(xiàn),形成結(jié)構(gòu)上的終止感,所以分析它為變奏形式的三段體曲式結(jié)構(gòu)。
2.1 作品中三音集合的使用
第一樂章中以原始序列的原型為全曲呈示性音響和收束性終止,一個引子一個尾聲,二者之間遙相呼應,其中的展開和連接性段落由核心三音集合為主要材料作為控制樂曲發(fā)展的手段,以類似于調(diào)性音樂主題動機的發(fā)展手法貫穿全曲。在作品中大篇幅使用大二度、小三度以及四度音程關(guān)系做聲部發(fā)展,看似音程關(guān)系的模仿中包含著三音集合的細碎化處理,縱向和聲間隱含著音程關(guān)系的緊張性和沖突性,其中原始序列及其移位序列以自由組合移位形式形成了橫向旋律與樂隊縱向和聲的音響基礎(chǔ)。
抽取核心三音集合的音程關(guān)系作為樂曲段落發(fā)展的基本材料,橫向旋律上以集合音和音程為發(fā)展基礎(chǔ),而縱向的樂隊和聲以核心集合的原始序列、變形以及序列移位作發(fā)展填充。上例中木管聲部用細碎化的音程模仿關(guān)系,在模仿發(fā)展的同時縱向和聲上又有三音集合在里面穿插,使用原始序列P0相隔三度關(guān)系移位的P4不斷做模仿寫作,同時序列內(nèi)部的三音列順序也按照相同的排列組合形式,音型在模仿發(fā)展的同時,序列內(nèi)部的排列順序也在模仿,打破了勛伯格十二音體系的寫作規(guī)則。橫向聲部發(fā)展的同時,縱向上的和聲也在交叉模仿,產(chǎn)生了片段性的橫向聲部變縱向和聲。這種橫向的旋律與縱向和聲、動機模仿與集合控制結(jié)合的寫作方式又表現(xiàn)出一些調(diào)性對峙、雙調(diào)性和復合調(diào)式的感覺,這在樂曲的可聽性和藝術(shù)性上做到了高度的契合。
2.2 動機式發(fā)展手法與集合控制力的結(jié)合
由弦樂組演奏集合中所包含的大二度、小三度音程關(guān)系做震音模仿下行,分別由第一、第二小提琴的第一聲部演奏大二度、小三度、大二度、小三度,第二聲部小三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二度做聲部旋律交替。在橫向發(fā)展以及縱向和聲結(jié)合構(gòu)成的音響效果中,由序列P2、P0、P1、P4、P5所含的三音列先后出現(xiàn),各序列的三音列之間順序已經(jīng)被完全打亂,所以按照十二音序列的創(chuàng)作方法來看作品中的序列變形已經(jīng)沒有實際意義。但從序列移位的音程關(guān)系來看,不僅僅是單純的音與音之間的關(guān)系有三音集合的控制力,使用的序列移位關(guān)系之間也隱含著核心三音集合內(nèi)大二度、小三度、純四度音程關(guān)系,在序列的使用上也存在著三音集合的影響。從內(nèi)容形式上看,它還屬于十二音序列的范圍,但實際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音樂發(fā)展手段已經(jīng)變成傳統(tǒng)調(diào)式音樂與集合動機相結(jié)合的手法,具有強大的動力性和樂曲推動力。
作品是在核心三音集合的基礎(chǔ)上運用類似傳統(tǒng)調(diào)性音樂主題動機發(fā)展的手法,通過提取三音列中二度音程關(guān)系作為動機進行模仿、移位,使作品中具有重復截段的序列間,如P0的a、b、c、d與P6的a、b(P0的a、b逆行)、c、d(P0的c、d逆行)發(fā)生了交叉重合現(xiàn)象。這種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序列組合形式,在旋律和聲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狀態(tài)。這種集合內(nèi)音程關(guān)系的模仿可以在多個序列移位中得到合理的解釋。從調(diào)性序列的角度來看,由于序列具有五聲性調(diào)式特征,是中國傳統(tǒng)五聲調(diào)式的截段,這種集合動機手法又隱含著調(diào)性對峙的元素。核心三音集合3-7[0,2,5]作為動機元素,對作品材料的發(fā)展起著控制作用,既有序列集合“強化了的主題一致性”,音與音程之間貫穿全曲的統(tǒng)一性和結(jié)構(gòu)力,同時又提取三音列中的音程關(guān)系作為發(fā)展的動機元素,具備了傳統(tǒng)調(diào)性音樂動機發(fā)展的推動性,具有推進音樂情緒、烘托音響效果的作用。在作品中,原始序列以自由組合及其移位形式交叉、融合,以集合動機的發(fā)展手法進行細碎化的處理,形成了一種密不可分的音響結(jié)構(gòu)。
3 結(jié)語
本文對《3Y》第一樂章(ye)的核心三音集合的使用為切入點,分析序列音樂創(chuàng)作中序列寫作技法與傳統(tǒng)調(diào)性音樂動機發(fā)展的結(jié)合點。通過三音集合將序列音樂寫作技法與調(diào)性音樂動機發(fā)展手法有機結(jié)合,在五聲性調(diào)性序列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以集合動機這種思維拓寬了中國傳統(tǒng)音樂元素在十二音序列音樂中的發(fā)展手法和表現(xiàn)手段,使音樂的藝術(shù)性和可聽性得到了高度統(tǒng)一。
參考文獻:
[1] 朱踐耳.朱踐耳交響曲集總譜(手稿版)激光唱片[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
[2] 鄭英烈.序列音樂寫作教程[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7.
[3] 蔡喬中.探路者的求索——朱踐耳交響曲創(chuàng)作研究[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
[4] 李波.異曲同工相映生輝——朱踐耳第六、第十交響曲比較分析[J].中國音樂學,2004.
[5] 姚恒璐.二十世紀作曲技法分析[M].上海音樂出版社,1997.
作者簡介:段煉(1993—),男,山東青州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復調(di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