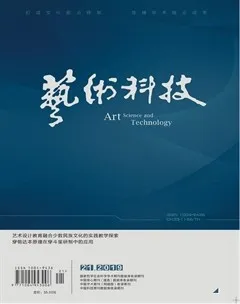美術(shù)界的“第三種人”
陳稼泠



摘 要:作為眾多現(xiàn)代主義社團的代表之一,決瀾社在上海文藝批評界掀起多方反響,又逐漸沉寂在時代洪流中。面對民族危機的客觀局勢,文藝作品逐漸開始擔負起反映社會現(xiàn)實與革命宣傳的使命,而決瀾社始終處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邊緣。本文通過將決瀾社與“第三種人”作家群體進行類比,探討該美術(shù)社團文藝觀的美學意義與文化屬性,以及在當時社會結(jié)構(gòu)中所面臨的多方困境,從而為其潛變與轉(zhuǎn)型提供闡釋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決瀾社;“第三種人”;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左翼美術(shù)
1 決瀾社:美術(shù)界的“第三種人”
1.1 決瀾社的藝術(shù)主張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獨特的文化空間中,多種藝術(shù)流派繁榮共生。雖說當局對文化藝術(shù)有過粗暴的干涉,但從總體上看,當時軍閥混戰(zhàn),各政治派別,革命思潮間的較量、斗爭,都削弱了對文化藝術(shù)的鉗制。[1]決瀾社活躍于1932~1935年的上海文藝界,它從這一“黃金時代”應運而生,在短短的5年時間里從藝術(shù)批評界的關(guān)注焦點逐漸走向銷聲匿跡,見證了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風格、文藝自由觀同以新興木刻藝術(shù)為代表的左翼文化的交鋒。其消亡預示了未來以革命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為主流的藝術(shù)走向。
作為一個先鋒性的藝術(shù)社團,決瀾社成員一致抵制當今畫壇“平凡與庸俗”的藝術(shù)現(xiàn)象——寫實基礎(chǔ)的學院派(如徐悲鴻)與商業(yè)美術(shù)(月份牌、布景畫、照相時以人物畫為主體……),追求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風格這一新的形式語言,致力于向大眾普及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他們在同時代的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流派(主要以印象派以來的后印象派、達達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為主)中進行圖式研究,融入中國本土化的含蓄韻味(如圖1)。《申報》的評價不失中肯:“立足于本國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和審美習慣,審慎地對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進行分類、采擷和發(fā)揮。”①借助其前身“摩社”主編的《藝術(shù)旬刊》《藝術(shù)》為首要平臺發(fā)表文章,《申報》(圖2)、施蟄存主編的《現(xiàn)代》雜志乃至《時代畫報》《良友畫報》等,皆有決瀾社成員們的繪畫作品與展覽訊息,可謂名震一時。
2 美術(shù)界的“第三種人”
“第三種人”這一作家群體主要出現(xiàn)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學界。以蘇汶、杜衡、施蟄存等人為代表,他們在政治立場上偏向左翼,在文藝上主張自由主義,試圖將兩者二分②[2]看待。該群體在政治立場上與左翼有或多或少的關(guān)系,如蘇汶、楊邨人等成員曾在左聯(lián)中共事,他們以承認無產(chǎn)階級理論的合理性為前提,提倡藝術(shù)真實論作為文學的價值體系,③[3]以作者之眼來審視這個客觀世界,具有超越現(xiàn)階段世界觀與意識形態(tài)的自由。“第三種人”對創(chuàng)作自由的維護于決瀾社成員們而言同樣適用,他們皆希望文藝作品能免受政治形態(tài)的限制。周多曾在《大眾畫報》中發(fā)表堅決反對將文藝用于宣傳的言論,繪畫就是繪畫,正同文藝作品就是文藝作品一樣。這與蘇汶等文學家堅決抵制將文藝作為政治的留聲機觀點一致。并且,決瀾社的大部分成員可以說是“左傾”立場的同情者,④[4]他們在美術(shù)界的位置正如“第三種人”在文學界的位置一樣,相信文藝與生活有直接聯(lián)系,與政治則是間接聯(lián)系,同左翼美術(shù)形成鮮明對比。
作為一個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社團,決瀾社力破停滯不前的西畫進程(以寫實主義為代表)與官僚風氣,以實現(xiàn)繪畫的新圖式變革。該藝術(shù)家群體在文藝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上追求傳統(tǒng)文人性質(zhì)的自由表達,在藝術(shù)自身的發(fā)展邏輯中探索其現(xiàn)代價值。倪貽德起草的《決瀾社》宣言如此寫道:我們以為藝術(shù)絕不是廣告主的奴隸,也不是文學的說明,我們要自由地、綜合地構(gòu)成純造型和色彩的世界。[5]可見,他們對色彩、線條和造型的探索往往訴諸形式層面,又非純粹的形式主義,而是將中國繪畫的傳統(tǒng)內(nèi)涵⑤[6]融入其中。倪貽德、周多、張弦等站在維護藝術(shù)本體價值的立場,反對“題材決定論”,相信繪畫的好壞不能由題材去判定。作為美術(shù)界的“第三種人”,決瀾社對創(chuàng)作自由的追求帶有藝術(shù)性的表達訴求。
3 民族危機中的決瀾社
3.1 “為人生”與“為藝術(shù)”兩種文藝觀
面對列強侵略與國內(nèi)外多方勢力的角逐,中華民族正處于內(nèi)外交困、生死存亡之際。1933年,《藝術(shù)》特辟一期關(guān)于“中國藝術(shù)界之前路”的專題討論。“鑒于近來國內(nèi)藝術(shù)界思想龐雜混亂,青年之彷徨歧途,無所適從;特仿效歐美雜志先例,辟文藝論壇一欄,由本刊按期擇一問題,公開征求各作家自由發(fā)表意見,或于摸索新路之青年,有所裨益。”[7]該期刊集合了8名文藝批評界人士與創(chuàng)作者,依次是王濟遠、李寶泉、倪貽德、徐則驟、曾經(jīng)可、傅雷、湯增歇和鄭伯奇。他們主要將問題聚焦于藝術(shù)本身,分為兩派,探討應當將藝術(shù)作為革命宣傳武器,還是繼續(xù)在其內(nèi)部深入研究。
左聯(lián)作家群體一致認為文藝創(chuàng)作者應擔負起時代使命,⑥[8]表現(xiàn)諸如“人民的疾苦,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以及東北義勇軍的腐敗,上海血魂除奸團的產(chǎn)生……”[9]這類題材。這背后是普羅派“為人生而藝術(shù)”的統(tǒng)一認知:選擇援用蘇聯(lián)的寫實主義直接匹配無產(chǎn)階級與唯物論,該藝術(shù)風格的引進必將順勢挾裹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tài)。而與大眾題材、寫實主義風格背道而馳的決瀾社則成了湯增歇在《時代的和大眾的》一文中批判的對象。與此同時,“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提倡者們要求首先專注于藝術(shù)自身的發(fā)展邏輯,站在維護藝術(shù)本體價值⑦[10]的立場上借鑒外來藝術(shù),磨煉技法,從而創(chuàng)造出真正具有藝術(shù)價值的作品。倪貽德提倡從寫實主義向現(xiàn)代主義風格邁進的藝術(shù)發(fā)展歷程,并在此基礎(chǔ)上肯定自我文化身份與藝術(shù)價值。他相信模仿只是發(fā)展中的一個步驟,而不是終點,最后必須從模仿中脫離出來再創(chuàng)造,那種藝術(shù)必須是代表著現(xiàn)代中國精神的藝術(shù)。[11]
3.2 決瀾社的調(diào)和與折中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逐漸臨近,這場社會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正促使文藝創(chuàng)作者的心態(tài)結(jié)構(gòu)與創(chuàng)作理念進行相應的調(diào)整,肩負起教化責任的文藝觀逐漸成為主流。面對日益嚴峻的社會形勢,決瀾社與“第三種人”群體正經(jīng)歷著維持自由獨立的創(chuàng)作人格同參與社會革命這兩種處世態(tài)度間的煎熬,他們難以在當下社會結(jié)構(gòu)中找尋到各自的身份定位。倪貽德曾發(fā)出感嘆:“是投了畫筆去從戎呢,還是仍舊安居在象牙之塔里面描寫那柔媚的女性肉體?改變了方向去畫那打倒帝國主義的宣傳品呢,還是仍舊表現(xiàn)那純粹個人主義的藝術(shù)?我是曾經(jīng)這樣的苦悶……”[12]從左翼對“第三種人”群體文學導向與政治立場的質(zhì)疑到后期將其視為革命道路上的同路人,再到1933年發(fā)生的一系列“轉(zhuǎn)向”事件,皆印證了魯迅的判斷:“第三種人”是做不成的。⑧決瀾社成員倪貽德也面臨著類似的身份問題,在這段時期之后,他在交代材料中聲稱自己為“第三種人”,是民族主義者。⑨[13]
在身份焦慮與內(nèi)心的煎熬中,決瀾社嘗試于“為藝術(shù)”與“為人生”之間開辟出一條中間道路,進而闡釋其文藝理論的合理性。藝術(shù)家同社會的關(guān)系在于,個體自我表現(xiàn)的行為源于對社會的關(guān)注,并將其訴諸美學層面,而反之亦然,這種藝術(shù)性的關(guān)懷能夠在美學領(lǐng)域內(nèi)部改造社會,借以美育啟發(fā)大眾的形式,直指人“內(nèi)心的革命”。[12]因此,龐薰琹認為自我表現(xiàn)的藝術(shù)不能說不是人生的,因為自我表現(xiàn)的藝術(shù),是自我情感的表現(xiàn),而情感不能脫離生活,生活不能脫離人生。[14]在此意義上,藝術(shù)革命與社會革命是兩條暗含交叉性質(zhì)的軌道,決瀾社對藝術(shù)本體價值的探索不應被簡單地定義為一個藝術(shù)家群體的避世行為或者與時代隔絕的“象牙塔”藝術(shù)。換言之,藝術(shù)的題材是否緊密直觀地貼近大眾現(xiàn)實生活并非衡量其存在意義與時代價值的唯一標準。因為在藝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部,這兩種文藝觀的結(jié)合是可以邏輯自洽的。而這正指向了該類文藝創(chuàng)作者背后的一套理想化的個人與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個體意識的覺醒能夠直接構(gòu)建出一個理想社會。這種觀念根植于新文化運動的整體意識形態(tài)——具有想象性的超現(xiàn)實政治。在個體人格獲得獨立的層面上,新文學運動的發(fā)起者圍繞自由民主的精神理想⑩[15]提倡新的社會進程,一如文藝創(chuàng)作者們可以自由地將內(nèi)部精神與情感借以新的藝術(shù)形式向外表現(xiàn)。
4 決瀾社的困境
4.1 藝術(shù)風格與現(xiàn)實的割裂
由于決瀾社與同時期左翼文化主導下的無產(chǎn)階級美術(shù)運動?在文藝觀上的差異,兩方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沖突,而往往這種核心差異會外化為對彼此藝術(shù)風格的不認可。魏猛克在《讀“決瀾”畫展》一文中評價了決瀾社的第二屆畫展,表示無法理解陽太陽君、丘堤君、王濟遠君等社員的繪畫作品(圖3),它們的造型與色彩不合常規(guī),唯有劉獅覺悟而復返于現(xiàn)實,到勞苦的大眾生活里去尋找藝術(shù)的新生命。[16]魏猛克代表著“大眾意識”的藝術(shù)批評理論,倡導木刻、漫畫、連環(huán)畫等大眾本身的、熟悉的、所感興趣的藝術(shù)作品,[17]這與決瀾社的藝術(shù)主張相悖,后者對文藝大眾化的態(tài)度是將自身所堅持的美學形態(tài)宣揚出去,以普及藝術(shù)教育、提高民眾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審美品位。決瀾社針對魏猛克不尊重師輩的行為予以回擊。[18]隨后這場爭論的焦點轉(zhuǎn)移至文學界,問題的側(cè)重點已然從兩種藝術(shù)風格的碰撞悄然轉(zhuǎn)移到施蟄存與于時夏關(guān)于“師說”的論辯。這與施蟄存作為《現(xiàn)代》雜志主編,在堅持文藝自由與中立態(tài)度的情況下成為左翼作家針對的對象存在一定聯(lián)系。
這場始于藝術(shù)風格的爭論直觀地展現(xiàn)出決瀾社與普羅派在文藝價值導向上的鴻溝,并側(cè)面反映了前者難以在現(xiàn)實社會中發(fā)揮引導大眾的實際性功能。左聯(lián)采取文藝風格與相應意識形態(tài)相互匹配的一元論模式,表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的寫實主義藝術(shù)風格對應著積極入世的進步思想,更能擔負起鼓舞大眾參與抗戰(zhàn)的職責(如圖4)。倘若以左翼美術(shù)的“形式?jīng)Q定論”傾向,?[19]馮雪峰在《關(guān)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一文中認為藝術(shù)的內(nèi)容與形式是相互匹配、不可分割的一體。與泛意識形態(tài)現(xiàn)象為參照,那么決瀾社的藝術(shù)實踐、文藝觀乃至創(chuàng)作意圖皆無法獲得立足之地。隨著這兩種不同的繪畫風格逐漸成為包含各自意象與經(jīng)驗的觀看物,藝術(shù)實際上無法在真正意義上作為一個獨立的形式對象進行欣賞與品評。左翼美術(shù)直指革命的社會思潮與意識形態(tài),決瀾社的現(xiàn)代藝術(shù)革新嘗試將中國傳統(tǒng)的文人品格?內(nèi)化地融入表達形式本身的美學中。而面對嚴峻的社會局勢,創(chuàng)作自由與文藝的獨立價值同個人的社會責任間呈現(xiàn)為一種孰先孰后的取舍關(guān)系,如同魯迅預見了“第三種人”的結(jié)局,文藝創(chuàng)作群體勢必無法全然脫離當下具體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tài),超越現(xiàn)階段的社會結(jié)構(gòu)而獨立。
4.2 藝術(shù)理論的局限性
決瀾社的藝術(shù)主張受到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的影響,這種圖式難以匹配中國該時期的社會環(huán)境,其源頭則具有超越風格層面的內(nèi)涵。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藝術(shù)批評的背景里,藝術(shù)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領(lǐng)域,?[20]以其自身的美學方式同社會發(fā)生反應,能夠改變社會現(xiàn)有的道德狀況與既定主導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而這樣一套從西方挪用而來的藝術(shù)風格并不適合中國的土壤,劉獅的自白已然揭示出這樣的客觀現(xiàn)實:巴黎畫壇的純藝術(shù)的傾向,完全由它們的社會經(jīng)濟背景所造成的,所以要把那種藝術(shù)移植到中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中國的大眾不需要這樣的藝術(shù)。[11]回歸自身,決瀾社的藝術(shù)運動主要是一場外化于風格層面的先鋒實驗,這個現(xiàn)代主義社團的成立始于一群有變革理想的藝術(shù)家們一拍即合,在激情與沖動中寫下了掀起藝術(shù)界波瀾的《決瀾社宣言》。
與之相比,左翼的文藝理論將藝術(shù)形態(tài)與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相統(tǒng)一,形成一套完整而穩(wěn)定的體系。文藝創(chuàng)作者應直接選取在工農(nóng)革命斗爭中所生產(chǎn)的內(nèi)容與被其所決定的形式,[21]這是基于對社會現(xiàn)實結(jié)構(gòu)的清晰認知、對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的充分把握,這樣的藝術(shù)形式方能積極地參與社會變革。文藝與社會生活的關(guān)系不僅僅止于像“第三種人”那樣反映現(xiàn)實,或者在美學的層面同傳統(tǒng)文人精神相對照,而是要作為革命精神的一部分,直接產(chǎn)生影響現(xiàn)實的力量。1930年,“中國左翼美術(shù)家聯(lián)盟”成立、創(chuàng)造社從“文學革命”轉(zhuǎn)向“革命文學”、魯迅呼吁青年投身于普羅文學的創(chuàng)作……這一系列的事件皆標志著“五·四”時期所未完成的啟蒙精神將重新在個人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間尋找到一條明確清晰的途徑。以對世界的整體性把握(歷史的立場)來超越個人認識的有限性,以客觀必然性代替?zhèn)€體選擇的逡巡不定,[15]在完備的理論體系與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導下,左翼美術(shù)家圍繞著統(tǒng)一的精神驅(qū)動力進行大量文藝創(chuàng)作,具備明確的創(chuàng)作導向,而決瀾社成員們卻在探索藝術(shù)內(nèi)部發(fā)展規(guī)律的過程中被動地陷入與社會現(xiàn)實相割裂的境況。
5 潛變與轉(zhuǎn)型
在第四次展覽會后,決瀾社便如龐薰琹口中的“石子”,很快地沉到池塘的污泥中去了,水面又恢復了原樣。隨著戰(zhàn)爭逼近,在時局動蕩、藝術(shù)家難以維持經(jīng)濟收入,與大眾的藝術(shù)趣味不合,乃至決瀾社成員的藝術(shù)主張難以統(tǒng)一等主客觀原因的內(nèi)外夾擊中,這場現(xiàn)代藝術(shù)探索之路草草收場,龐薰琹不得不承認,真正揪起一個時代巨浪狂瀾是困難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