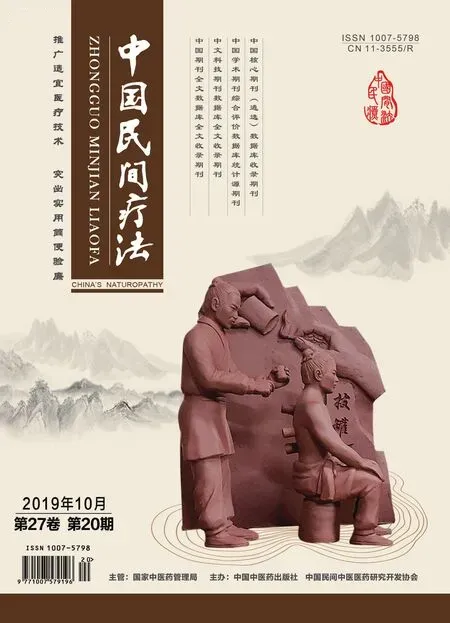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疼痛臨證舉隅
舒小妹
(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人民醫院,廣東 深圳518172)
疼痛是多種疾病的常見癥狀,也是患者個體的主觀感受,可因人因病不同而致疼痛程度、疼痛性質不同。中醫對疼痛的認知歷史悠久,而中醫多學科、多治療方案的整合對疼痛的治療有著巨大的作用。現筆者就近5年來采用中醫藥綜合方法治療疼痛的病例及體會介紹如下,以供同仁參者。
1 中藥內服配合艾灸治療胃癌根治術后之腹痛案
患者,女,23歲,2013年5月5日初診。主訴:胃癌胃大部切除根治術后腹痛3個月余。刻下癥:上腹痛,以脹痛為主,拒按,呃逆,乏力,無口渴口苦,無反酸、胃灼熱,納少,眠差,大便不化,每日1次,小便正常。舌質淡,苔白滑,脈沉緩。腹平軟,劍突下壓痛明顯。胃鏡示殘胃炎、胃內大量食物殘留。西醫診斷:胃癌胃大部切除根治術后、殘胃炎、食物儲留;中醫診斷:胃脘痛。給予附子理中丸合平胃散加味治療。處方組成:炮附片10 g(先煎),黨參片30 g,干姜10 g,麩炒白術20 g,炙甘草10 g,蒼術15 g,厚樸15 g,陳皮15 g,炒麥芽30 g,炒稻芽30 g,5劑。每日1劑,水煎煮,早晚飯后30 min溫服,配合中脘、神闕、足三里隔姜灸。2014年7月28日二診:患者因復查胃鏡來診,訴初診治療后癥狀大減,因就診不便,自行隔姜灸中脘、神闕、足三里等約半年余,期間有上腹脹痛,飽餐后明顯,無口干口苦,納眠可,大便軟,每日1次,小便正常。舌淡,邊齒痕,苔白,脈沉細。復查胃鏡示殘胃炎、吻合口炎。效不更方,繼以原方3劑做丸藥,緩而圖之,并囑其堅持艾灸。后隨訪未再復發。
按語:《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成形,陽化氣”,意為“陽動而散,故化氣;陰靜而凝,故成形”。目前諸多文獻均已報道了腫瘤的形成與機體陽氣受損、陽化氣不足而陰聚成形有關[1-2]。該例患者為年輕女性,為陽氣虧虛、陰寒內盛體質,加之術后氣血大傷,脾土虧虛,土不制水而致腹痛。腹脹、呃逆、苔白滑、脈沉緩及大便不化均為陽虛濕阻、本虛標實之證,故辨證屬脾胃陽虛,中焦濕寒。治以附子理中丸合平胃散扶陽散寒、健脾祛濕,加炒稻芽、炒麥芽消食、除有形之陰邪;并配合隔姜灸,借助艾灸與藥物的雙重作用,激發局部經氣,以溫陽健脾、逐寒除濕、行氣通絡止痛。
2 中藥內服配合中藥穴位貼敷治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身痛案
患者,女,26歲,2013年5月26日初診。主訴:身痛1周,伴鼻塞。刻下癥:周身酸痛,鼻塞鼻癢,頭昏,咽癢欲咳,乏力,畏寒,無發熱,無胸痛,口渴喜溫飲,心悸,眠差,二便調。舌質淡胖,苔白膩,脈沉細弱。既往服用抗病毒口服液治療3 d,癥狀無明顯改善。患者平素易感,畏寒神疲,勞累后即感心悸。查血常規、心電圖均正常。西醫診斷: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醫診斷:感冒。給予麻黃附子細辛湯加味治療。處方:麻黃10 g,炮附片10 g(先煎),細辛3 g,蒼術15 g,2劑。每日1劑,水煎煮,早晚飯后溫服,配合中藥穴位貼敷大椎。貼敷藥物組成:葶藶子10 g,芥子5 g,細辛5 g,肉桂3 g,麻黃5 g。諸藥搗碎研粉,陳醋調勻后均勻涂抹于10 cm×15 cm大小的無紡布帖內,貼敷于大椎處,每日1貼,每貼4 h。共貼敷2 d。2013年5月27日二診:訴身痛、頭昏、鼻塞、咽癢等癥已除,唯有乏力、畏寒同前,眠好轉。舌質淡胖,苔白,脈沉細弱。囑其外購中成藥附子理中丸口服2個月,溫中健脾,緩而圖之。
按語:患者平素易感、畏寒、勞累后心悸、舌質淡胖及脈沉細弱,均體現了患者陽氣虛之體質,周身酸痛、頭昏、白膩苔等癥狀乃外感寒濕引起,故辨證屬陽虛外感。治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溫經解表,加蒼術燥濕健脾解表;并選用葶藶子、芥子、細辛、肉桂、麻黃等藥物貼敷于大椎,具有宣肺解表止痛、溫陽祛濕通絡之效。大椎為人體陽經之匯,通過局部刺激可益氣壯陽,以助解表止痛,外感得解后以附子理中丸培土生金。
3 刺絡放血配合中成藥內服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炎之關節疼痛案
患者,男,49歲,2015年11月24日初診。主訴:左側跖趾關節紅腫痛2 d。刻下癥:跛行入診室,痛苦貌。左側跖趾關節紅腫、疼痛,呈撕咬痛,夜間痛甚,局部皮膚暗紅,口微渴,無口苦,無發熱畏寒,納可,眠差,大便正常,小便偏黃。舌質暗紅,苔薄黃,脈弦滑略數。觸診局部波動感明顯,皮溫高。既往有急性痛風性關節炎、高尿酸血癥病史,長期服用別嘌醇片及金水寶膠囊。西醫診斷:急性痛風性關節炎;中醫診斷:痹證。局部常規消毒后,采用三棱針于左側太白刺絡放血,每日1次,共2次。每次均引出白色絮狀物混合暗紅色血液約15 mL,后以中成藥四妙丸鞏固治療1個月,并囑其停用他藥,飲食有節。療程結束后電話告知諸癥皆除。隨訪至今,痛風未再發作。
按語:謝建祥等[3]認為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的中醫病機為濕濁毒邪滯留血中,痰瘀痹阻經絡;現代醫家朱良春亦指出,痛風多有先天稟賦不足或年邁臟氣日衰,若加飲食不節,可導致臟腑功能失調,脾腎清濁代謝紊亂,水谷不歸正化,濁毒內生,積漸日久,或偶逢外邪相合,終必瘀結為害[4]。故本病急性發作期治其標,以三棱針于太白刺絡放血。刺絡放血療法基于“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盛則瀉之,菀陳則除之”。太白乃足太陰脾經之原(輸)穴,具有祛邪扶正補虛的功效,該穴刺絡放血不僅能快速祛除瘀積于局部的濕濁瘀毒之邪,還能通達三焦原氣,調節臟腑經絡功能,從而發揮維護正氣、抗御病邪的作用。疾病緩解期則以四妙丸健脾祛濕清熱治其本而收效。
4 中藥內服配合火針治療帶狀皰疹之右脅疼痛案
患者,女,55歲,2016年10月19日初診。主訴:右脅部群集性水皰、疼痛6 d。刻下癥:右脅部群集性皰疹、灼痛,口苦,口渴喜涼飲,無發熱畏寒,納可,眠差,二便調。舌質淡紅,苔黃膩,脈弦數。西醫診斷:帶狀皰疹。中醫診斷:蛇串瘡。給予龍膽瀉肝湯治療。處方:龍膽草10 g,黃芩片15 g,梔子10 g,川木通10 g,車前子15 g(包煎),當歸10 g,生地黃30 g,澤瀉15 g,柴胡20 g,炙甘草10 g,3劑。每日1劑,水煎煮,分2次空腹涼服。配合毫火針多針淺刺阿是穴(皰疹處),使皮損部位完全暴露,并用無菌棉簽擠凈皰液。2016年10月21日二診:治療后排出極臭之糊狀便,每日2~3次,疼痛大減,無口苦,口渴喜涼飲減輕。舌質淡紅,苔薄黃,脈細略弦。查皰疹已結痂,給予一貫煎養陰柔肝鞏固療效。處方:生地黃30 g,北沙參15 g,當歸10 g,枸杞子30 g,麥冬15 g,川楝子15 g,5劑。每日1劑,水煎煮,分2次餐后涼服。2017年2月6日其子因病來診,訴患者治療后諸癥皆除,未再發作脅痛。
按語:中醫認為蛇串瘡多因濕熱邪毒蘊結,困阻肌膚經絡而發為皰疹。此案皰疹分布于肝經循行部位,灼痛感、口干苦及舌脈均為濕熱之象,故辨證屬肝經濕熱。急性皰疹期給予龍膽瀉肝湯內服以清肝膽、利濕熱、通絡止痛,火針局部點刺阿是穴以熱引熱使郁發之。火針是集毫針、三棱針及灸法三者為一體的治療方法,具有清濕熱、除火毒、通經絡、止疼痛的效果。研究發現,火針治療帶狀皰疹可明顯縮短帶狀皰疹急性期的疼痛時程,促進皮損愈合結痂,增加治療后疼痛消失率,減少后遺神經痛的發生[5-6]。待濕熱之邪從大便及局部清除后,患者即表現出一派肝陰不足之象,故予以一貫煎養肝陰、疏肝氣、柔肝止痛。
5 針刺配合拔火罐治療肋間神經痛之脅痛案
患者,女,26歲,2016年12月16日初診。主訴:生氣后左脅下痛3 d。刻下癥:左脅下痛,呈攣痛或掣痛,急走、深呼吸、大笑及轉身活動時痛甚,無畏寒發熱,無口干口苦,納眠可,二便調。舌質淡,苔薄,脈弦。左側腋前線第9、10肋間隙壓痛明顯,按壓左側章門疼痛完全消失。既往體健。查消化系統及泌尿系統彩超均無異常。西醫診斷:肋間神經痛。中醫診斷:脅痛。給予毫針針刺左側腋前線第9、10肋間隙阿是穴及左側章門。阿是穴采用瀉法疏通局部,每10 min行針1次,共行針3次;章門采用補法以榮養局部氣血,行針頻率同前,出針后給予拔火罐。治療結束后患者訴疼痛大減,已能轉身、深呼吸,唯有按壓阿是穴尚有少許疼痛。囑其注意休息,避免重體力活。次日清晨患者來電訴疼痛消失,未再治療。1個月后因感冒就診,訴經治后脅痛未再發作。
按語:患者因情緒不暢而發病,病程較短,無明顯表里寒熱之證,乃肝經氣機郁滯不通所致,故辨證屬氣滯。循經觸診時發現阿是穴拒按,考慮局部氣機郁滯不通,故以瀉法疏導氣機;章門屬足厥陰肝經,是脾經的募穴,又是八會穴之臟會,五臟氣血匯聚于此,章門喜按,故考慮肝經榮養不足,給予補法針刺章門,再繼以拔火罐改善局部血液循環。
6 中藥內服配合艾灸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巧克力囊腫之腰痛、痛經案
患者,女,42歲,2017年1月16日初診。主訴:腰痛2個月余,月經淋漓不凈半個月。刻下癥:腰酸痛如折,久站及勞累后加重,腹以下畏寒,乏力。末次月經2016年12月30日,淋漓未凈,色暗紅,量少,無口干口苦,納眠可,二便調。舌質淡暗,舌下絡脈曲張,苔薄白,脈沉細無力。平素月經第1~3日痛經,熱敷可稍減輕,痛甚則需服用止痛藥。既往有腰椎間盤突出癥、巧克力囊腫、痛經病史。西醫診斷:腰椎間盤突出癥、月經不調、巧克力囊腫。中醫診斷:腰痛、痛經、崩漏。給予溫經湯加味。處方:吳茱萸3 g,麥冬15 g,酒當歸10 g,赤芍10 g,川芎10 g,黨參片30 g,桂枝10 g,阿膠5 g(烊化兌服),牡丹皮10 g,甘草片10 g,法半夏15 g,續斷片30 g,杜仲30 g,5劑。每日1劑,水煎煮,早晚飯后30 min溫服,并配合艾灸腎俞、三陰交、地機等穴以補肝腎、調沖任、溫經散寒止痛。2017年1月20日二診:訴服藥后腰痛大減,月經已凈,無畏寒乏力。舌質淡暗,舌下絡脈曲張,苔薄,脈沉細。予原方調整川芎、牡丹皮均為5 g,繼續服用7劑,煎服法同前。2017年2月6日三診:訴末次月經2017年1月31日,至今未凈,色暗紅,量少,少許腰痛乏力,無口干苦,納眠可,二便調。舌質淡,苔薄,脈細。上方加熟地黃30 g,5劑。3 d后電話告知月經已凈,勞累后少許腰痛,囑其堅持艾灸1個月。
按語:姜勁挺等[7]認為腎氣虛損不固可導致腰椎間盤突出;趙瑞華等[8]認為腎虛是子宮內膜異位癥發生的根本原因,血瘀是其基本病機。經血不循常道排出體外,反而逆行積聚于他處,久之成瘀,形成巧克力囊腫,結合患者腰酸痛不耐久站、畏寒乏力及舌脈等癥可辨為腎虛夾瘀之體質,故辨證屬腎虛不固,腰府失養,寒瘀阻滯。治以溫經湯溫經散寒止痛、養血祛瘀調經,加杜仲、續斷以補肝腎、養腰府、強筋骨、調血脈。三診加大量熟地黃以填精補髓、生血通脈。艾灸具有疏通經絡、調和陰陽、扶正祛邪、逐寒濕、散腫結等作用,配合艾灸腎俞以培補腎元、溫運血行,灸地機、三陰交以健脾補肝、調經止痛,三穴配伍,扶正祛邪而收效。
7 小結
筆者發現,按照八綱辨證,表里、寒熱、陰陽、虛實均會出現疼痛的癥狀,無論外感六淫,還是內生寒、濕、熱、瘀血及氣機郁滯等實邪,又或者局部陰陽氣血津液不足,均會導致機體某個部位甚至多個部位出現疼痛。“通”和“榮”是眾多醫家對疼痛比較一致的治療大法。“通”即疏通,意即消除一切瘀堵之病理產物,使機體局部氣血得以流暢、循行不息;“榮”即榮養,意即補足機體缺失之陰陽氣血津液,使局部機體得到充分的濡養及溫煦。然而每于臨證之時,多以寒熱錯雜、虛實夾雜、本虛標實之證常見,故標本兼治實為治療疾病之大法。機體局部出現有形之邪可觀之觸之,臨床可采取針刺、刺絡放血、拔火罐、中藥穴位貼敷、艾灸等治療手段,直搗病灶以通之;機體出現無形之邪可辨之論之,臨床可采取中藥內服調整機體陰陽偏頗,調理氣血榮之,“通”“榮”兼顧,內調外治,方能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