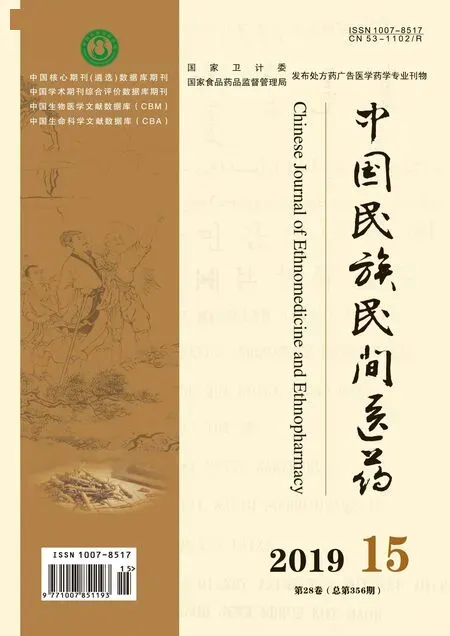清熱化痰散結法治療聚合性痤瘡臨床經驗
王 菁1 田 靜2
1.遼寧中醫藥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2;2.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遼寧 沈陽 110032
聚合性痤瘡是痤瘡中損害最嚴重的一種類型,多見于青年男性,常于面、胸、肩、背部發病。皮損形態多樣,表現為嚴重結節、囊腫、竇道及瘢痕。治療較為困難, 容易復發, 遷延難愈, 皮膚結構破壞程度較重,愈合后多留有色素沉著、凹陷性瘢痕, 給患者的心理帶來一定的影響[1]。聚合性痤瘡發病機制比較復雜,目前尚未完全明確,現代醫學認為本病多與雄激素及皮脂增加、痤瘡丙酸桿菌感染、毛囊皮脂腺開口處過度角化及繼發炎癥反應因素相關[2]。在中醫古籍中對本病有許多描述,《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肺風粉刺》記載:“此證由肺經血熱而成,每發于面鼻,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腫痛,破出白粉汁。”田靜教授擅長運用中醫藥防治顏面損容性疾病及變態反應性皮膚病,筆者有幸跟隨田靜教授在門診學習,現將其治療聚合性痤瘡經驗介紹如下,以饗同道。
1 探究病源 緊扣病機
中醫學認為,聚合性痤瘡的病機關鍵在于痰熱蘊結。聚合性痤瘡與生活狀態密切相關,患者脾胃素虛,或飲食不節傷而及脾胃,均可導致水液運化失常;偏嗜辛辣之品,助陽化熱,或多食魚腥油膩肥甘之品,或酗酒,使中焦運化不周,均可化生火熱。而脾失健運,濕邪內生,蘊濕化熱,成毒生痰,痰熱互搏,阻于經絡,損于臟腑,久之,氣血津液耗傷,無力抵抗邪氣,而使痰熱互結熏蒸頭面、胸背等處肌膚,毛竅閉塞,蘊釀成膿皰、囊腫、結節。田師在臨床工作中,根據患者的皮損及舌苔脈象,認為患者素體熱盛,加之飲食不節傷及脾胃,導致痰濕內生,熱毒痰濕凝結是其主要病機。
2 內外結合 審因辨治
根據臨床經驗,田靜教授認為,一般情況下,聚合性痤瘡的病程較長,局部皮損較嚴重,故治療上應內治與外治相結合,內治調攝五臟、清熱解毒、化痰散結,外治消腫排膿、通瘀化滯。在臨床上常中藥內服配合刺絡拔罐療法和水調散外敷治療本病,可以起到內外兼顧,標本同治之效。
2.1 中藥內服 田靜教授根據清熱化痰散結法,自擬消瘡飲治療聚合性痤瘡。處方:當歸、生地黃、夏枯草各15 g,連翹、陳皮、蒲公英、金銀花、野菊花、牡丹皮各20 g,皂角刺、炙甘草各10 g,白花蛇舌草25 g。但聚合性痤瘡臨床病情復雜多變,在具體譴方用藥上,對囊腫膿性多者,加穿山甲、天花粉、白芷消腫排膿;結節嚴重伴疼痛者,加浙貝母清熱解毒散結;瘢痕明顯者加用丹參以加強活血化瘀之功效,現代藥理表明,丹參含有的丹參酮具有較好的抗雄性激素及溫和的雌激素活性,能夠抑制痤瘡棒狀桿菌的生長,從而抑制痤瘡的炎癥反應[3];瘙癢明顯者,加白鮮皮、蟬蛻、白蒺藜祛風燥濕止癢;女子月經不規律者,加益母草活血調經;濕氣重者,加澤瀉、蒼術清利濕熱去濁。
2.2 刺絡拔罐療法 此法主要施以針對痤瘡的囊腫、結節皮疹,以達解毒散結功效。在臨床中,選取大椎穴和肺腧穴,施以毫針刺破小血管后,然后在針孔處迅速拔上火罐,刺絡和負壓產生的機械刺激通過反射途徑傳到中樞神經系統,加快毒素的清除與排泄,具有瀉熱解毒、通瘀化滯、調和氣血的功效。大椎穴屬督脈,與臟腑功能活動有關,刺絡拔罐此穴能既解陽經之毒,又可通調督脈而化濕解毒、導熱下行。肺俞穴可調補肺氣、祛痰除瘀、消癰生肌。現代醫學認為,刺絡拔罐療法具有改善血液循環,促使有毒物質排出,加快炎性反應吸收,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4]。
2.3 水調散外敷 水調散是中藥復方制劑,出自明代《普濟方》,因使用時需要加水調成糊狀而得名。主要由黃柏、煅石膏研末而成。具有清熱解毒、消腫止痛之功。使用時將水調散用純凈水調成糊狀,敷于囊腫、膿皰處,厚約0.3 cm,范圍大于皮損直徑0.5 cm。此法經皮膚吸收,直達病灶。其中黃柏性味苦寒,有清熱燥濕、解毒療瘡之功;煅石膏辛甘,性大寒,外用有生肌斂瘡的功效。二者合用,以寒治熱,使囊腫、膿皰消退,以防邪毒向周圍擴散。
3 病案舉例
王某,男,22歲。初診日期:2018年9月30日。以“面部、胸背部反復起丘疹、結節、囊腫半年,加重1月”為主訴。曾內服中藥湯劑,外用抗生素藥膏治療,用藥期間皮疹有所減輕,但仍反復發作,飲食可,便溏,睡眠可。來時癥見:面部、胸背部較密集丘疹、結節、囊腫,顏色鮮紅,其上有膿頭,舌質紅,苔黃膩,脈弦滑。診斷為聚合性痤瘡,證屬痰熱蘊結證,以自擬消瘡飲加減。處方:生地黃、浙貝母、金銀花、牡丹皮、桑白皮各15 g,炙甘草、清半夏、梔子、陳皮、夏枯草、皂角刺各10 g,連翹、蒲公英、野菊花、白花蛇舌草、炒白術各20 g。每日1劑,水煎服。配合每周一次刺絡拔罐法(大椎穴、肺腧穴)和隔日一次水調撒外敷治療。
2018年10月12日復診,丘疹、結節部分消退,顏色變淺,但皮疹處出現瘙癢感,上方中加白鮮皮15 g。
2018年11月23日三診,患者皮疹基本已消,無新生皮疹,囊腫干癟,無明顯瘙癢感。
按語:患者青年男性,正值生機旺盛之時,且病程日久,則熱毒之邪燔灼津液,煉液為痰,壅阻經絡,循經外發而致病發。痰熱阻絡,故粉刺、結節、囊腫并見。結合皮損及舌脈,均為痰熱蘊結之征,治療應清熱解毒與化痰散結并舉。方中清半夏、浙貝母、梔子、桑白皮除濕化痰;連翹、蒲公英、皂角刺清熱解毒散結之功尤著,現在醫學證明,連翹可以降低毛細血管的通透性,減少炎性滲出[5];配伍牡丹皮活血化瘀以助散結;夏枯草走氣分,清熱瀉火降濁,桃仁走血分,化血瘀,通經絡。一氣一血,既能順氣降逆、滌痰散瘀,又能疏通經絡瘀滯,對于本病所起效果與單用迥異;金銀花清熱解毒,歷代對金銀花的論述頗多,均認為本品入心、脾、肺、肝、腎五臟,無經不入,為消毒神品。大凡攻毒之藥,均有所散氣,而金銀花不但不散氣,還能補氣,更善補陰,尤妙于補先于攻,消毒而不耗氣血;生地黃清熱涼血;陳皮理氣助化痰之力;炒白術健脾燥濕;野菊花引藥上面部;炙甘草以護中,使諸藥雖涼而脾胃可受。二診時,患者皮疹處有瘙癢感,上方加白鮮皮以祛風止癢,《本草原始》云:“白鮮皮入肺經,故能祛風,入小腸經,故能去濕,夫風濕既除,則血氣自活而熱亦去。治一切疥癩,惡風,疥癬,楊梅、諸瘡熱毒。”配合刺絡拔罐療法及水調散外敷以增解毒祛瘀之功,加快改善局部皮損。內外合治,收效確切。
4 小結
聚合性痤瘡病程較長,并且愈后仍有可能留下明顯的瘢痕,影響面容。許多患者在初起時多應用抗生素、激素、維A 酸類的藥物來進行治療,部分患者用藥后癥狀明顯改善,但是停藥后癥狀反復,甚至加重,久治不愈,且使用抗生素易產生耐藥性,激素類藥物副作用相對較大[6]。田靜教授通過多年臨床實踐指出,熱毒痰濕凝結是聚合性痤瘡發病病機,清熱化痰散結乃治聚合性痤瘡之法。同時配合飲食調攝、護膚品選擇,往往收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