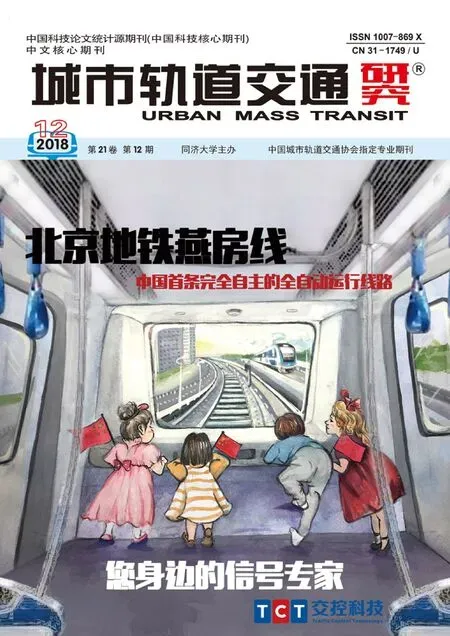滿載情況下地鐵車廂乘客熱舒適性評價
趙 楠
(海軍駐上海地區艦艇設計研究軍事代表室,200011,上海//工程師)
地鐵車廂普遍存在人流量眾多、人員復雜和車廂內空間相對擁擠的情況,尤其高峰時期上述情況更為嚴重,因此提高地鐵車廂乘客的舒適度這一問題亟待解決。
文獻[1]研究了空氣有規律地波動與人體熱舒適度之間的關系,總結發現了新的舒適度影響因素,即空氣的波動頻率和速度變化幅度。文獻[2]利用自制的動態出風裝置進行研究,發現裝置出風頻譜越接近自然風,受試者的熱舒適滿意度越高。文獻[3]顯示,當風扇的風速不超過2 m/s時,可以顯著改善室內的熱舒適度,但若風速太大,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同時相關的實驗結果表明,在28 ℃的環境下,實驗者也能感受到熱舒適,其條件就是將風速提高到一定程度。文獻[4]通過投票實驗研究,發現動態送風可以顯著改善局部熱環境。文獻[5]表明,在相對濕度為50%的情況下,人體依然能夠通過提高風速來提高舒適溫度上限。文獻[6]于1967年提出了聞名于世的熱舒適方程, 并綜合人體熱平衡方程及ASHRAE七點標度,提出了預測平均投票數PMV(Predicted Mean Vote)指標。該指標考慮了空氣溫度、平均輻射溫度、空氣流速、空氣濕度、人體新陳代謝率及服裝熱阻,是目前最完善的熱環境評價指標。因此,本文選用PMV指標作為熱舒適評價指標。
本文通過加載幅流風機和改變送風溫度,設計了3種不同工況,建立了1∶1的實車模型和人體模型,借助計算流體動力學(CFD)數值模擬方法研究送風速度和溫度對滿載地鐵車廂乘客舒適度的影響。研究結論有助于合理調整空調出風溫度和速度,進而達到既舒適又節能的效果。
1 物理模型
以B型地鐵列車車廂作為研究對象,列車頂部有兩臺空調機組,采用對送的送風方式,一臺機組位于一位端,另一臺機組位于二位端。機組的回風口位于各個機組下部,負責將車內的空氣送回空調機組。車廂左右兩側分別設置5排座椅,2個條縫型送風口分別位于車頂左右兩側,風口下方有導流板,負責將送風引入車廂兩側的座椅處。本車廂采用的回風方式為頂部集中回風,每個機組下方均布置1個回風口,回風進入機組下部風道后,再次參與送風循環。車廂內剩余空氣則通過廢排風道直接排向車外,廢排風口布置在列車兩端頂板,每端布置2個,如圖1所示。

圖1 地鐵B型車車廂通風設備布置示意圖
因車廂內部在車體長度方向上是對稱的,故取車體的一半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由于計算車型的排風和回風是分開的,因此,車廂內設置了送風口、回風口和排風口,即物理模型的入口和出口。在車頂特定位置布置有3個幅流風機安裝處,為減小列車震動對風機的影響,結構之間安裝有避震保護裝置。本文旨在研究滿載時風速和溫度對地鐵車廂內乘客舒適度的影響,因此車廂內共有232人,其中36人有座,196人站立。
幅流風機出風口處設置有送風格柵,幅流風機向下吹風,經過格柵進行風向的分列,用來增強吹風作用效果。扇葉長1.1 m,直徑為8 cm,蝸殼上部開設有進風口,下部平面處為出風口。蝸殼以扇葉圓柱中心線為軸做來回圓弧擺動,使得出風口的位置不斷變化,進而形成“掃風”的過程。
2 數值計算模型
本文采用RNGk-ε湍流模型和 SIMPLE數值計算算法,選用二階迎風(Second Order Upwind)差分格式的離散格式和標準的壓力插值格式來對計算模型進行數值模擬分析。目前,針對人體散熱計算模型的研究主要分為一節點模型、二節點模型、多節點模型和多元模型等。一節點模型把人體簡化為一個熱源,通過人體表面與環境的換熱來達到熱平衡,該模型較簡單,亦得到廣泛應用。本文主要研究地鐵列車內流場的分布,以及評價車廂內乘客的舒適度,因此,選擇一節點模型作為自定義人體模型的理論基礎,且計算模型采用輻射條件下的第二類邊界條件。
3 數值計算結果及分析
數值計算分為以下3個工況,分別為:
(1)工況一:無幅流風機且空調出風溫度為20 ℃的靜態工況,研究僅有進排風作用下的滿載地鐵車廂的風速分布情況;
(2)工況二:開啟幅流風機且空調出風溫度為20 ℃的動態工況,研究幅流風機對滿載地鐵車廂風速分布的影響;
(3)工況三:開啟幅流風機且空調出風溫度為22 ℃的動態工況,研究提高送風溫度對幅流風機作用的影響。
3.1 速度場計算結果分析
圖2為工況一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風速分布云圖。由圖2可知,當地鐵車廂滿載時,不同位置的風速大小區別較為明顯,即風速不均勻度增大。同樣,因車廂內乘客人數較多,從頂部吹出的風受到阻礙,難以到達下部即座位上的乘客位置。

圖2 工況一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風速分布云圖
圖3顯示了工況二時,幅流風機作用下的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風速分布云圖。由圖3可以清楚地看出,幅流風機在由7 s向左下方吹風轉換到23 s向右下方吹風的整個變化過程中時,最大風速出現在幅流風機出風口處,約為2.8 m/s,當靠近人體區域時,風速已經減弱到2 m/s以下,截面平均風速約為0.50 m/s,符合人體舒適性要求。
圖4顯示的是工況三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風速分布云圖,該云圖與圖3無太大區別,最大風速位置出現在幅流風機出風口,約為2.8 m/s,截面平均風速為0.51 m/s,符合人體舒適性要求。
對比工況一和工況二可以發現,幅流風機可以有效地擾動滿載地鐵車廂內的氣流,能將空調出風更加均勻地送至“氣流死區”。而對于工況二和工況三,即有幅流風機的兩個工況,在幅流風機的作用下車廂內的風速度分布幾乎無區別,最大風速均出現在幅流風機出風口處,風速約為2.8 m/s,截面平均風速約為0.5 m/s。
3.2 溫度場計算結果分析
無幅流風機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溫度云圖,如圖5所示。因無冷風直吹作用,且廢排風口在其附近,故車廂中部的熱量通過該處排出,造成這個位置的溫度較其他部位高。由于乘客密度增大,人體之間的輻射熱量增多,造成人體附近的溫度進一步升高,最高溫度大約為38 ℃。

a) 7 sb) 15 sc) 23 s

圖3 工況二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風速分布云圖
圖4 工況三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風速分布云圖

圖5 工況一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溫度分布云圖
圖6為工況二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溫度分布云圖。由圖6可知,在幅流風機作用的半個周期內,該截面的溫度變化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冷空氣在幅流風機的擾動下吹向車廂內各個區域。車廂截面最高溫度出現在人體附近,約為37 ℃。當出風溫度提高到22 ℃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溫度云圖如圖7所示。由圖7可知,與工況二相比,工況三的平均溫度稍高,為27.81 ℃,其溫差基本與出風溫差相符。由此可知,在上述客流密度下,當出風溫度為22 ℃時,乘客會感覺稍許悶熱。幅流風機的掃風會擾動原來的冷風流動,增加冷風的作用域,降低被作用部位的表面溫度。比較工況二和工況三的溫度分布圖可知,當,出風溫度為20 ℃時,滿載地鐵車廂內的平均溫度更符合人體舒適度標準。與工況一進行對比發現,平均溫度降低了0.3 ℃,說明幅流風機的擾動降溫效果較明顯。

a) 7 sb) 15 sc) 23 s

圖6 工況二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溫度分布云圖
圖7 工況三時滿載地鐵車廂截面半個周期的溫度分布云圖
3.3 PMV指標計算結果分析
圖8為各工況下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PMV指標分布云圖。由圖8a)可知,工況一除出風口處PMV值小于0(約為 1.5)外,其余部位PMV值幾乎都大于0,PMV值最大的部位靠近人體附近,其值達到3.0,尤其靠近廢排風口端,由于該部位無出風口的直接作用,同時高溫廢氣多經過該區域排向廢排風口,造成該部位PMV值超高,因此該部位的乘客體感尤其差。

a) 工況1

b) 工況2

c) 工況3
圖8 滿載地鐵車廂截面的PMV指標分布云圖
當出風溫度為20 ℃時,滿載地鐵車廂工況下的PMV值更趨近于零值,且整個截面PMV值的均勻度較高,由于該工況出風溫度較低,同時乘客數量多且散熱量大,使得熱量平衡之后乘客的舒適度為最佳。當出風溫度為22 ℃時,滿載地鐵車廂工況下,因乘客散熱量大且車廂內溫度較高而導致PMV值偏大,尤其是廢排風口一側車廂的PMV值約為2.5,該部位雖有幅流風機擾動,卻使得PMV值的整體均勻度遠遠高于無幅流風機作用的情況,但依舊難以克服因溫度較高而為乘客帶來的不舒適感。
4 結論
本文采用CFD數值模擬方法,通過有無加載幅流風機對滿載地鐵車廂乘客的舒適性進行了靜態和動態工況的數值模擬。結果表明,在幅流風機開啟、空調出風溫度為20 ℃的動態工況(即工況二)下,乘客的舒適度最佳;在幅流風機開啟、空調出風溫度為22 ℃的動態工況(即工況三)下,乘客的舒適度亦表現較佳。因此可知,幅流風機對地鐵車廂的舒適度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同時亦需綜合匹配多方因素才能使乘客舒適度達到最優。研究成果可對實際工程的應用提供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