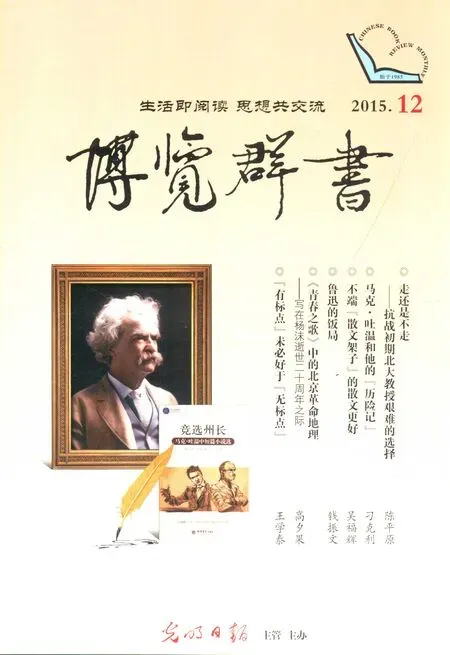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北方的河》里有中國的圖騰
林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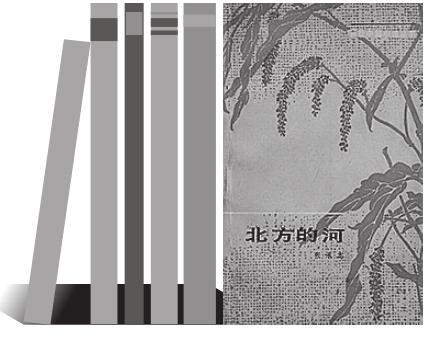
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張承志是一個(gè)以敘述知青歲月見長,同時(shí)兼具學(xué)者氣質(zhì)的作家。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往往雜糅了小說、散文、論文、報(bào)告文學(xué)等諸多文體的特征。發(fā)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說《北方的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北方的河》是一個(gè)關(guān)于追憶與尋找的故事。一個(gè)結(jié)束知青生活回到北京的男青年不愿意接受被安排的“計(jì)劃生育辦公室”的工作,一心想要報(bào)考自己喜歡的“人文地理科學(xué)”的研究生。在準(zhǔn)備考試的過程中他親身實(shí)踐,去到北方的幾條大河進(jìn)行實(shí)地考察,考察路上遇到了一個(gè)因公出差的女?dāng)z影師。小說圍繞著二人結(jié)伴而行的溯河之旅,以及主人公回京之后的生活困擾和愛情糾葛展開。可以說,《北方的河》既是一個(gè)有關(guān)“知青”的故事,也是一個(gè)有關(guān)“尋根”的故事。因考試而開始的大河之旅既是對個(gè)體理想的追尋,也是對理想的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并且是以“80年代”的知識與文化范式推進(jìn)的。
在整個(gè)80年代,關(guān)于“中國”的故事幾乎都是由知識分子來講述的。因而80年代的文學(xué)史中,想象“中國”的主體無疑是知識分子群體。這意味著重建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先要重建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文學(xué)史把《北方的河》劃入“知青文學(xué)”的序列,不僅因?yàn)樽髡邚埑兄驹?jīng)的知青身份,更重要的是小說寫出了知青們共同命運(yùn)的合流和分化,內(nèi)含著知青群體內(nèi)部的復(fù)雜性,而這種復(fù)雜性也是上世紀(jì)80年代的復(fù)雜性。
作為知青文學(xué),這部小說首先與七八十年之交返城后的知識青年普遍面臨的精神困境有關(guān)。隨著“文革”的結(jié)束,一代經(jīng)歷過“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的身份、生活、價(jià)值都需要重新定位。《北方的河》發(fā)表不久后,一些批評家就指出張承志的才華只擅長寫大江大河寫鄉(xiāng)野場景,刻畫城市生活的能力不夠。今天看來,這與其說是作者的文學(xué)才能有失,不如說是知青們對城市生活的焦慮使得小說的后半部分顯得相對貧乏與黯淡。因此如何重建理想中的共同體,如何重新確認(rèn)一代知識分子在共同體的歷史與未來中的位置就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小說開頭第一句話正是在這個(gè)語境中誕生:
我相信,會有一個(gè)公正而深刻的認(rèn)識來為我們總結(jié)的:那時(shí)這一代獨(dú)有的奮斗、思索、烙印和選擇才會顯露其意義。
如何克服一代人的精神危機(jī)呢?《北方的河》給出了兩種路徑:一種是小說主人公以空間置換時(shí)間,通過重新肯定歷史現(xiàn)場而走向未來的方式;一種是主人公曾經(jīng)的知青朋友徐華北在厭惡和否定中擺脫歷史奔向新生活的方式。重返歷史現(xiàn)場并不等于時(shí)髦的文化懷舊。小說中沒有具體姓名的主人公考察自己青春記憶中的河流,是在他經(jīng)歷過歷史洗禮與精神漫游后的重游。人不能兩次踏進(jìn)同一條河流。此時(shí)的主人公已經(jīng)是經(jīng)過反思與重建的主體。再次游歷北方的河某種程度上是他對自我重建的確認(rèn)。小說在敘事方法上不斷變換敘事視角,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他”)和第二人稱的敘述視角(“你”)不斷交錯(cuò)。這種自我分裂式的內(nèi)心獨(dú)白的產(chǎn)生,是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現(xiàn)代主體誕生的一個(gè)重要表癥。從這個(gè)角度看,小說的主人公已經(jīng)是一個(gè)邁入“新時(shí)期”的現(xiàn)代主體。而這個(gè)新的主體觀看山河卻不是為了憑吊歷史。歷史在他身上并未死去,不僅因?yàn)樗?jīng)生活和熟識的山川、河流、臺地、草原等將是他以后考試必須具備的知識,主人公在陽光下充滿豪情壯志赤身站在奔流的黃河邊上便是一個(gè)頂天立地的大寫的“人”的形象,是歷史的崇高客體。他在召喚青春時(shí)期那個(gè)勇敢無畏、積極健康、漫游遠(yuǎn)行的自己。通過再次尋找那個(gè)被特殊歷史時(shí)期所鍛造的自己來尋找未來前進(jìn)的方向。在這里,歷史被納入了未來,并成為未來的指示。歷史、現(xiàn)在與未來由此同時(shí)獲得意義。張承志試圖通過主人公的大河之行實(shí)現(xiàn)兩個(gè)時(shí)代的意識形態(tài)的對接。因此,主人公所代表的這一類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是毛澤東時(shí)代與“新時(shí)期”耦合而成的。
“遠(yuǎn)行”作為80年代文學(xué)的主題之一,在張承志筆下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這一點(diǎn)如果對照80年代中后期余華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便可讀出差別。差別不在于小說形式,不在于所謂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之別,而是“遠(yuǎn)行”對于青年人自我主體性塑造的成功與失敗。“遠(yuǎn)行”對于《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里的主人公而言,只是生活一次又一次荒誕的打擊。它不僅沒有幫助主人公確立自我,反而使“我”變成了一個(gè)孤零零的無意義的個(gè)體。而在《北方的河》中“遠(yuǎn)行”亦是“回歸”,是有動力的,有方向的,有目的的,是尋找自我和尋找意義的有效方法。這種有效性恰恰是被8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否定的那段歷史給予的。

很明顯,“北方的河”在小說中是作為“中國”的典型意象和圖騰符號出現(xiàn)。如何觀看和講述“北方的河”意味著如何想象“中國”,如何重建作為共同體的民族國家。小說的主人公想象“中國”的核心方法是:人文地理學(xué)。他把“人文地理學(xué)”認(rèn)定為“科學(xué)”,“北方的河”正是在“科學(xué)”話語中被賦予新的觀看視角與價(jià)值。在主人公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中,“人文地理學(xué)”由語言學(xué)、考古學(xué)和地理學(xué)匯聚而成。每一門知識對于這個(gè)小說重新想象“中國”都有它的作用。它們分別代表想象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統(tǒng)一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和明確的領(lǐng)土。《北方的河》主要贊頌了五條北方的河流:額爾齊斯河、黃河、湟水、永定河、黑龍江。小說用這五條大河在空間上延展文明的視野,在時(shí)間上勾連出連續(xù)流淌的歷史長河。它們共同創(chuàng)造出中華民族的文明血脈、民族性格與文化氣質(zhì)。其中,將額爾齊斯河也作為民族國家的地理象征并不常見。這是一條流淌在少數(shù)民族地域上的河流。將邊境河流與中原河流統(tǒng)一起來,一同納入民族國家的表述,不僅是對來自西方的現(xiàn)代單一民族國家想象的突破,也提供了現(xiàn)代文明由海洋向內(nèi)陸轉(zhuǎn)移的視點(diǎn),以及文明的邊緣與中心變化的可能性。
由于考古學(xué)的加入,“北方的河”不只是“中國”地理空間上的坐標(biāo),它還是建構(gòu)民族國家歷史統(tǒng)一性的媒介。以黃河為主的晉陜河谷因著主人公在毛澤東時(shí)代的知青經(jīng)歷成為兩個(gè)時(shí)代歷史的連接點(diǎn)。而當(dāng)作者試圖把這兩個(gè)連接起來的時(shí)代往更久遠(yuǎn)的歷史源頭追溯時(shí),“破碎的陶罐”作為重要的意象就在小說中出現(xiàn)了。主人公和女?dāng)z影師在湟水河灘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美而破碎的陶罐。有的研究者將這一意象視為美學(xué)觀上“殘缺的美”的象征。“陶罐”作為考古對象,在小說中與其說是審美的對象,不如說是歷史的對象。
與主人公重走青春之路相對應(yīng)的是他的朋友徐華北。同樣是返城知青,徐華北絲毫不想回顧自己的知青生活,他拋下曾經(jīng)的戀人,拋下一起插隊(duì)的朋友,義無反顧地回城,同時(shí)將自己指認(rèn)為歷史的受害者。他也不滿意自己在城里的工作,卻通過轉(zhuǎn)型為文學(xué)青年而實(shí)現(xiàn)自我救贖。有意思的是,“文學(xué)”在小說中對知青群體主體性重建的作用。主人公和徐華北都是熱愛文學(xué)的青年。徐華北憑借“文學(xué)”找到戀愛對象,以及離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文學(xué)”是徐華北所代表的另一類知識分子可以順利進(jìn)入“新時(shí)期”的秘密武器。不難想象,徐華北很快將匯流到80年代占據(jù)主流位置的右派作家群。而我們的主人公熱愛文學(xué),卻不得其門而入,他心心念念要把自己對北方河流的愛寫成詩,卻始終沒有寫完。在“文學(xué)”這個(gè)面向上,他沒能得到8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認(rèn)同。主人公完成自我重塑,憑借的是另一套話語:“科學(xué)”話語。
事實(shí)上,“科學(xué)”與“文學(xué)”這兩種看上去相對立的話語在80年代的意識形態(tài)中與其說是南轅北轍,不如說是相輔相成。“代表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科學(xué)”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其實(shí)也是不同的文化修辭的產(chǎn)物。科學(xué)主義與人文主義是80年代的兩大主潮。“科學(xué)”與“文學(xué)”在“現(xiàn)代性”知識與觀念的層面上成為80年代現(xiàn)代化理論的兩種不同范式。“北方的河”在小說中被“文學(xué)話語”和“科學(xué)話語”雙重?cái)⑹觥V魅斯c徐華北看似選擇了兩種不同的話語,但在80年代他們命運(yùn)的相似性仍然遠(yuǎn)大于差異性,因?yàn)樗麄児餐袚?dān)了歷史的負(fù)重,共同面臨著現(xiàn)實(shí)的壁壘(小說中強(qiáng)大而壓抑的“體制”)。同理,《北方的河》可以視為80年代初文學(xué)界彌合兩個(gè)時(shí)代的裂縫,撫慰歷史轉(zhuǎn)型的陣痛而作的一種嘗試,文學(xué)、科學(xué)與政治在民族國家想象上完成了一次合謀。這樣的嘗試之所以是可能的,因?yàn)?0年代有著時(shí)代的共識,有著共同的他者。而那些微小的縫隙將留給90年代,并成為90年代知識界的分歧與分化的伏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當(dāng)代文學(xué)專業(yè)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