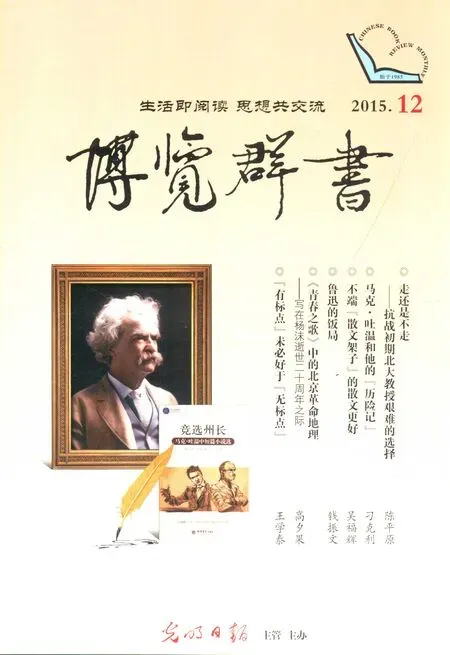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人生》之所以叫“人生”
葉端
路遙的《人生》是反映80年代社會生活和個人命運的重要作品,不僅在當時引起轟動,至今仍吸引著無數讀者。小說最成功的是塑造了高加林這樣一個人物。
高加林出身農村,接受了教育,成為一個有文化有理想的新青年,卻只能回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他想要施展自己的才華,卻屢屢遭受挫敗,只有接受自己身為農民的命運。在他一度雄心勃勃的時期,作者借黃亞萍之眼形容高加林:
她現在看見加林變得更瀟灑了:頎長健美的身材,瘦削堅毅的臉龐,眼睛清澈而明亮,有點像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保爾·柯察金的插圖肖像;或者更像電影《紅與黑》中的于連·索黑爾。
這兩個人物正好反映了高加林人格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保爾·柯察金式的鋼鐵般的意志、吃苦耐勞的精神、為集體事業獻身的奉獻性,和青梅竹馬的富家女冬妮婭因志向的不同而分離;另一個則是于連,為了向上爬不擇手段,不惜以上流社會的女人為跳板。他們的共同點是充滿奮斗的激情和實現人生價值的強烈渴望;在一個大的舞臺上,他們會成為英雄或野心家。
然而,高加林所處的環境,卻使他困囿于一個狹小的現成生活。小說沒有寫高加林最初回到農村做民辦教師時的感受,但以文化人在農村受到的尊重和免于農活的好處,至少也算學有所用了。而在小說開始時,高加林失去了民辦教師的職位,高家村又處在從集體生產到包產到戶的過渡時期,再加上大隊書記高明樓的私心,集體的凝聚性對高加林失去吸引力,機械繁重的體力活更加劇了內心壓抑的感受。他的情緒喜怒無常,很多時候具有表演性人格,呈現出夸張的情感和動作,過分自傲又時常自卑。如小說第六章不得不重新做農民時,他故意穿破爛的衣服,把手弄爛出血。處于逆境時,他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抗爭性,和不公平感。尤其當他的自尊受到威脅時,他格外容易被激怒。第12章他到縣城挑糞時,先與城關先鋒隊的人打架,又與張克南媽起爭執。第22章張克南知道母親毀了高加林的工作后,提出可以經濟上幫助他,高加林先是“一下子憤怒地站起來,大聲咆哮:‘別侮辱我了!你滾出去!滾出去!”,然后又“猛然走上前來,用一條胳膊摟住了他的肩膀,用一種親切低沉的音調說:‘克南,對不起。你怎能說這種話呢?如果我不了解你是出于一種真誠,我就馬上會把你打倒在這里……原諒我,你走吧!”這樣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比起小說,更像是戲劇。
如果在別的作家手里,如簡·奧斯汀筆下,他很有可能會是柯林斯先生一類作為調味的丑角形象,以夸大他情緒化的不得體。而路遙寧愿把這些有不平之氣的普通人用舊的筆調樸實地寫,這顯示了他的寬厚之處。或者說,他的諷刺是內在性的。因為想要刻薄地評價人是容易的,而他更愿意在同情的情境之中如實展現人的缺點和長處。同樣,想要尖銳地批判社會是容易的,但要表現真實的存在處境是困難的。
自以為有才能的年輕人,想離開陳舊的環境是合乎情理的,而他們到大城市遭遇迷失或失敗,也是必然的。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有這樣的問題,年輕人外出闖蕩,懷著天真的愿望,試圖跨越階級的壁壘,考取功名,贏獲意外的財富,也是傳奇故事中調和夢想與現實的方式。但是,在高加林這里,挫折不是他在城市的遭遇帶來的,而純粹是一個戶口身份問題,一個外在性的悲劇。小說展現了一種命運的回環,一種古希臘悲劇式的結構。《人生》之所以叫“人生”,最終質詢的是人的命運問題——即人是否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人的自由意志能否與注定的命運對抗。
同時,為了凸顯這個悲劇的外在性,路遙對高加林在縣城的經歷寫得太過完美了,他輕而易舉就獲得了人們對他工作能力和個人魅力的贊許。如果是在城市,這或許有些夸張,但是在縣城這個城鄉結合的“交叉地帶”,提供了一種個人極度舒展的空間,又使他處于可進可退的曖昧位置。在小說中,他的能力始終是富余的,可以說,他是在一個理應向上走的情況下往下沉淪的。
和他對比,其他人的工作又變動得如此輕易。高明樓的兒子三星先是頂替了高加林的民辦教師的職位,又調到縣農機局的機械化施工隊,劉立本的女兒巧玲便很自然地補了民辦教師的缺。馬占勝被查辦,他們看起來并未受牽連。黃亞萍父親的老戰友“聽了她的播音,當時就讓到江蘇人民廣播電臺當播音員”,似乎也不算走后門。所有的困難只針對高加林一個人。假使高加林真有作者所寫的那樣的才能,情況就變得更吊詭。和西方此類現實主義的小說不同,這是個到不了巴黎的于連的故事。高加林對世界的探險止于這個“一個萬人左右的山區縣城”,即便如此,這個“藍色霧靄中的縣城”,也只停留在夢中,就像菲茨杰拉德筆下的綠光,是無法逾越的階層鴻溝,就像人們渴望卻注定失敗的許多事物。
人們對高加林的同情,正是出于這樣一種顯而易見的不公正。如果小說寫的是知識青年被迫下地勞動,最后農民教育他們要熱愛土地,又是另一番情形,讀者在接受道德洗禮之余未免替這些城市的棄兒感到憂慮。而高加林由于出身農村,便被自然而然地籠罩上濃重的鄉土感情。他如果不愛種地,就得懺悔,這幾乎是他的原罪了。我們相信高加林的悔過是真誠的——他內心有著對土地的熱愛。但是,用強化他對一個鄉下姑娘的感情,來表達他的追悔,以彌合他在城鄉之間游離的痛苦,未免是對農村男人在城市的失敗,通過農村女人的“優越性”予以補償(盡管巧珍身上“溫順”這種美德,實際出于農村男女間性別權力的不公)。
《人生》不是愛情小說,路遙也不想把它變成一個倫理困境。高加林去縣城之前,沒和巧珍結婚,這避免了發生婚外情的道德問題。而在他被驅逐回農村之前,巧珍先結婚了,介于巧珍對高加林的癡情,她和馬拴的婚姻雖從一開始就有伏筆,仍顯得過于倉促。基于加林最后要幡然悔悟,加林絕不能真正愛上黃亞萍,黃亞萍也并非高加林的初戀——盡管他們曾經有很多機會親近——而是一位曖昧的“女同學”。高加林在兩段感情上都是被動的,似乎他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兩個女人就不能自拔地愛上了他。事實上,這兩個女人只是農村與城市的化身。和哪個女人結合,就意味著他將過著怎樣的生活。
對缺少社會資源和上升途徑的高加林來說,利用婚姻,幾乎是條必然途徑。我們可以看到,路遙對黃亞萍的人物設定中,特別強調她是個南方姑娘。如果僅僅是討論農村與縣城二元,南方的情節不是必要的,但在這里,它代表著一個更大的世界,代表著北方人對南方美好風光與富庶的渴望。在19世紀法國及英國的許多著作中,隨著社會的急劇變動和商業的繁榮,“年輕的野心家”直接把婚姻或做貴婦人的情夫當作一種發財或躋身上流社會的渠道,以此生發出無數故事,這幾乎是一種固定的橋段了。亨利·詹姆斯的《華盛頓廣場》講的就是父親寧愿女兒終生不幸也不愿意讓她和這樣的財產獵人結婚。
另一方面,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允許這樣一種不正之風得到傳揚。青年人企圖通過戀情謀求上升,也會因為情感的糾紛失去一切。司湯達《紅與黑》中于連和瑞那夫人的悲劇、巴爾扎克《交際花盛衰記》中呂西安與艾絲苔的悲劇正是如此。在《人生》里,高加林因為和黃亞萍的關系得罪了黃亞萍原本男友張克南的媽媽,導致他工作走后門被舉報,很快又失去好不容易得來的前程。但是,路遙不會讓人物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而是讓他回到他原本的地位。高加林兩次失去工作,既沒有報復高明樓,也沒有報復張克南。除非舉報是巧珍做的,他才會有于連那樣感情上的沖動,但善良的巧珍顯然不會那么做,村民們也都寬容地接納了他。路遙也沒有讓高加林像于連一樣在法庭上痛斥社會的不公,而是諄諄教誨:“一個人應該有理想,甚至應該有幻想,但他千萬不能拋開現實生活,去盲目追求實際上還不能得到的東西。”路遙不愿意讓自己的人物用雞蛋擊打高墻,一方面是他的同情心和責任感,他是在力圖描寫一種真實的人生而非可以當做實驗的假設,高加林的人生也會為他的讀者的人生帶來真實的影響;一方面則出于道德關懷,在他看來,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正義”只是暫時的勝利。這回應了關于命運的另一個問題——人在迫切地改變自己命運時能否不擇手段?
在變動的年代,個人意識開始覺醒。路遙發現了到了人們躁動的內心,以及在更大天地自由施展才能的渴望,并提出溫情的告誡。一方面,小說非常看重對知識的把握;另一方面,這代表智性和理性的力量卻把他引向悲劇的結局。在命運悲劇的框架下,土地既代表著傳統觀念的人不能忘本,也變成一種宗教情感,路遙試圖將高加林從于連拉回保爾·柯察金的軌道,并以虔誠之心接受對自己的懲罰。
在《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的個人命運和當地社會生活的改變結合得更緊密。剝去了高加林身上浮躁和浪漫主義的一面,孫少平和孫少安更踏踏實實地耕耘于平凡的生活,肯定了普通勞動的價值。因此,《人生》更大的意義在于一種對欲望的警醒,以堅實之心承受苦難,和對自身道德性的復歸。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