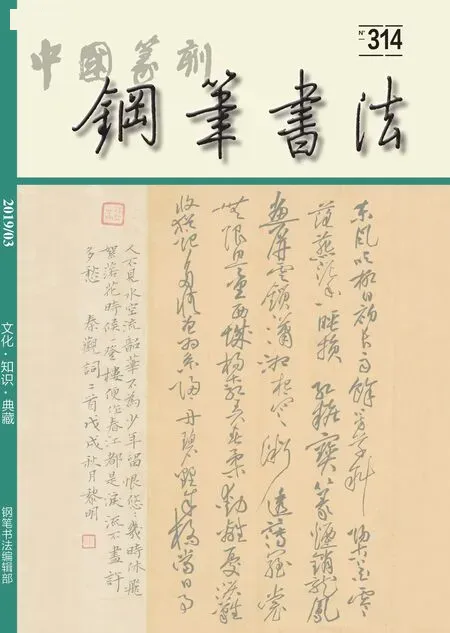試論當代書法審美鑒賞的理性回歸
文︱傅德鋒
平心而論,中國書法是存在審美標準的,而且這種審美標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長期的書法實踐和理論梳理逐步形成的。盡管中國書法的審美標準不是絕對的、唯一的,但它卻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之上存在有它的基本標準。
反過來講,如果說中國書法沒有基本的審美標準,那么是否就可以說,一切使用毛筆書寫漢字的書跡留存都可以算得上是書法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真正懂書法的人都普遍認為,只有那些既具備傳統功底又具有一定創(chuàng)新意識的作品才能稱得上是書法作品。從三代吉金鐘鼎竹帛文字到秦漢魏晉,再到唐宋元明清民國乃至當代,大量被人們所認可的書法作品都具有這一特征。
非但如此,即便是那些歷史上公認的書法作品,也同樣被人們分為若干不同的檔次和品級。清包世臣作《國朝書品》,將書法分為五品,分別是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為九等,分別是:神品、妙品上、妙品下、能品上、能品下、逸品上、逸品下、佳品上、佳品下。這就充分說明,不同的書法作品,可以根據不同的審美鑒賞標準來加以劃分等級。從師承、筆法、結體、行氣、章法、氣韻、格調、意境等不同角度,可以針對一件書法作品進行鑒賞辨別。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因素,那就是書家本身的身份地位、學識修養(yǎng)和在其他領域的建樹等。
中國自古就有“字因人貴”“字以人傳”的說法。一部中國書法史,從某種角度來講,就是一部官員書法史。一個沒有身份地位的人,則很難在書法史上留名。歷史上很多經生胥吏所書寫的書法作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藝術水準,但他們卻很少能將自己的真實名姓流傳下來。由此可見在中國書法史上,一定有很多優(yōu)秀人才和作品因為種種原因被歷史的塵埃所湮沒。
這就無怪乎僧人書法家懷素為了見知于世人,只得不遠千里,“擔笈杖錫,西游上國,謁見當代名公”。懷素從遙遠的南方(長沙)一路走到當時的都城長安,投奔其表兄錢起,然后在錢起的引薦下,拜見顏真卿等當朝大員,并當眾作“書法現場表演”。一方面是希望藉此能夠得到高人指點,另一方面是希望得到當朝高官和名人的認可和推重。
就這一點而言,今天與古代并無太大區(qū)別。當代的書家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同樣必須經歷一個不斷進行人際公關的過程。一個普通書法愛好者,不但要在書齋之內靜心苦修,還要登門拜訪各級名人,參加各類書法培訓班、研修班,并從參加縣市基層書法展覽開始,直到參加全省全國展覽,其目的無非也是希望藉此能過獲得相應范圍內書法家的認可和推重。而且其參加的比賽和培訓級別越高,接觸社會的面越廣,所能學到的東西就越多,其社會影響也就越大。
就當代書法的創(chuàng)作水準而言,似乎是以“文革”作為分水嶺的。“文革”以前,建國十七年,由于國家此前經歷了兵火戰(zhàn)亂,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需要休養(yǎng)生息,恢復國力。所謂盛世修文,像書法這樣的藝術門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可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只能依附于美術而存在。而從民國過渡到新中國之后的一些書法家,也由于連年的政治運動,不可能將更多的精力花費在書法研究方面,同時也很難具備相應的物質條件。
“文革”結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文化領域獲得了空前解放,經濟文化水平逐漸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書法開始逐漸復蘇。
然而,當時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書法整體水平還處在一個非常初級的層面上。那時出現的一些書法展覽,其作品大多是一些對漢隸、唐楷和前人作品的簡單化臨摹,不要說是個人藝術風格的形成,僅就技術層面而言,很多基本問題也都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隨著上海《書法》雜志的創(chuàng)刊和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成立,中國書法在新時期的發(fā)展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中國書法》《中國書畫報》《書法報》《美術報》《書法研究》《青少年書法報》《書法導報》等專業(yè)報刊相繼創(chuàng)刊,再加上很多經典碑帖的大量出版,客觀條件和藝術氛圍越來越好,中國書法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在長達近20年的生活時段里,中國書法經歷了一個自由長足發(fā)展的特殊時期。在西方文藝思潮的沖擊之下,文藝思想空前活躍。反映到書法上,則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嘗試性探索。“現代書法”和“流行書風”風靡一時,成為一個時代書法界的焦點話題。但客觀地講,這個時期的書法審美鑒賞標準是相對比較混亂的。因為今天我們再回頭看當年那些“現代書法”和“流行書風”,包括當時由中國書協主辦的全國書法展的獲獎作品,很多都已經沒法看了,顯得非常膚淺稚嫩。在當初那個時候,可能很多作者都接受不了這樣的評價,但時隔近20年之后,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經歷了“文革”的思想禁錮,迎來了“改革開放”。人們壓抑已久的沉悶思想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得到宣泄和釋放。于是,片面強調“個性解放”和“藝術創(chuàng)新”成為了當時人們的狂熱追求。事實上今天我們冷靜下來做一番分析思考,就會發(fā)現,其實當時的書法家們缺乏了一個錘煉功底、積淀修養(yǎng)的必要過程。當時的展覽作品固然在形式上、視覺印象上有一定的突破,但在技術含量和內在意蘊上非常匱乏。作品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張揚、浮躁,揭示的還是作者們內心的焦慮和彷徨。片面追求形式設計和視覺沖擊,流露出的還是對傳統經典的淺層次理解。但這并不是說,那個時期的探索毫無意義,而是說這種探索還遠不能以成功來加以詮釋。
藝術審美鑒賞能力的獲取,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提升的過程。作為書法藝術的基本審美標準是自古以來就早已存在的,只不過人們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的過程。中國書法到底應該走向何方,應該如何推陳出新,應該在多大范圍內、什么程度上求新求變,這都需要人們不斷思考并付諸實踐。但無論如何,都必須經歷一個足夠長的基礎錘煉和修養(yǎng)積淀過程。只有在精湛的技術和豐贍的學養(yǎng)之上,才可能有真正有價值的藝術探索。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然而就在這樣的困惑時期,因著市場經濟觀念的不斷沖擊和影響之下,“官本位思想”在書法界一度呈泛濫之勢。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批的只有普通票友水平的“官員書家”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借助書法沽名斂財的捷徑,紛紛通過綜合運作手段,躋身書協,擔任了書法協會的各種要職。一時之間,這些人的“信筆涂鴉”之作在“主席、副主席、理事”的耀眼光環(huán)映照下,水漲船高,大行其道。人們紛紛趨之若鶩,爭先購買,甚至以“奇貨自居”,以期“待價而沽”。其實除了一部分人是出于討好官員,迎合“權力尋租”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在盲目“收藏頭銜”而已。
書法界丑拙低俗書風盛行,不能不說與只具備普通票友水平的“官員書家”紛紛擔任書協要職關系甚大。一時之間,書法界演變成了一些官員延伸腐敗的灰色地帶。
近年以來,中央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伴隨著一批腐敗官員的相繼落馬,一些書法官員被書法協會陸續(xù)清退,這些人的作品價格一落千丈。一些收藏人士在吸取了沉痛教訓之后,才開始重新審視書法的真正價值。
就近十年以來的全國書展而言,其審美導向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一方面是開始抵制那些過度的表面化的“形式設計”,另一方面剛在大力提倡向傳統回歸。除此之外,還倡議書家多讀書,加大提升自身綜合修養(yǎng)的力度。這些無疑都是好的方面。
事實上,好的書法作品必須具備以下幾個先決條件:一是扎實的傳統功底;二是鮮明的藝術風格;三是作者本身具備的獨特的人格魅力。這三者實際上是與古代書家一脈相承的。
一個人的身份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要以書法的名義在社會上立足的話,那么你就必須具備最基本的書法功底和綜合藝術修養(yǎng),同時還要有良好的口碑。好的書法作品,不僅要有鮮明的藝術個性,更要具備世所公認的藝術共性。傳統功夫就是藝術共性,經典碑帖就是最好的參照。失去了這個基礎,任何個性都談不上藝術個性。
我們欣喜地看到,近年來,書法家們越來越趨于理性,他們越來越注重傳統功夫的深入錘煉,越來越注重提升自身的綜合修養(yǎng)。社會收藏人士也逐漸不再以書家的社會頭銜作為衡量一件作品藝術價值高低的主要標準,開始就作品本身來加以考量。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有人說,“回歸傳統”相比于當初的“流行書風”是矯枉過正,認為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但我認為,回歸傳統本身并沒有什么錯。關鍵在于如何真正實現對傳統的回歸。因為傳統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流動發(fā)展的存在,它不是僵化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的積淀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只要我們深刻認識到了傳統的主旨所在,則這種回歸就會使我們越來越走向理性,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