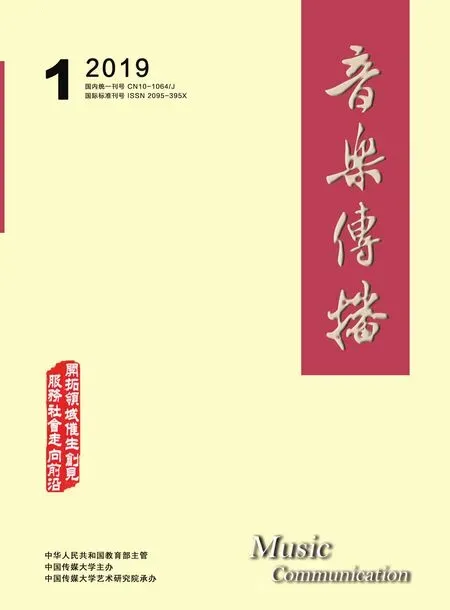廣州市兩類粵曲職業表演者生存現狀考察與比較
■潘妍娜
(廣州大學,廣州,510006)
“表演者”是傳統音樂文化的創造者和承載者,同時也是音樂歷史的書寫者。作為文化中的個體,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總是直接作用于表演者的身上,并反映于其音樂觀念與實踐之中,正如民族音樂學家斯蒂芬·布魯姆在其研究中提出的,在音樂與社會歷史背景之間關系的分析中,職業音樂表演藝人扮演著所謂“中間人”的角色。①參見斯蒂芬·布魯姆《伊朗馬什哈德與博季努爾德的藝人角色變遷》,載布魯諾·內特爾主編《八個城市的音樂與文化:傳統與變遷》,秦展聞、洛秦譯,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因此,關注職業表演者的生存狀態,是我們認識音樂文化變遷的關鍵。本文研究對象——廣州粵曲職業表演群體是指在廣州市區內主要從事粵曲演唱表演的人群。他們當中的部分人是通過系統、規范的專業學習,在畢業后從事粵曲演出的,也有的人本不是從事粵曲演出,因愛好唱粵曲,而轉變成為職業的粵曲表演者。總的來看,根據其專業背景與表演水平的差距,當下廣州粵曲職業表演者呈現出“專業團體中的表演者”與“茶座中的表演者”兩個群體的不同。本研究從2013年4月份開始,對廣州市現有粵曲表演場所與表演團體進行了走訪,對兩類粵曲從業者的專業背景、表演環境、經濟條件等問題進行了相應的考察與比較,以此進一步理解粵曲在當下傳播與生存狀態的差異性。
一、粵曲職業表演者發展的歷史簡述
目前粵曲界比較統一的認識是粵曲表演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經歷了“八音班”、“師娘”、“女伶”三個發展時期。早期的“八音班”②八音班一般為八名成員八種樂器(故此名“八音班”),后來也有十至十二人的,稱為“大八音”。所演唱的“粵劇”清唱,原本為珠江三角洲農村中演出的吹打樂伴奏,表演者一般為鄉村樂師或走街串巷賣藝的“盲藝人”③參見曾寧《粵劇與粵曲、嶺南八音班的關系》,載《南國紅豆》1996年第12期。,八音班演出形式為不上妝的清唱,邊奏樂器邊唱,唱曲者同時也是樂師,一人一角。這種演出多服務于農村中的祭祀、集會等活動。清朝末年開始,廣州的城市化發展促進了城市娛樂需求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在廣州城市茶樓“歌壇”中出現了以唱“粵曲”為業的失明女性藝人“師娘”(也名“瞽姬”)①參見黎田、謝偉國著《粵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8-33頁。。20世紀20年代左右,為適應茶客需求,明眼“女伶”逐漸代替了盲眼的“瞽姬”,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大量女性表演者進入這一職業領域,女伶人數增加到300多人②伍蘇、黃玉瓊、羅志偉、黃曉華口述,黃德琛執筆《廣州“女伶”補遺》,載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六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頁。。歌壇隨之應運而生一批教彈琴唱曲的職業教師,女伶們表演、唱腔、唱法受到嚴格的培訓,這使得行業的職業性日漸加強;另一方面,歌壇的商業競爭促使女伶們不斷打磨、研究新的唱腔與唱法,促生了一批技藝高超、才華卓絕的女伶(如小明星、徐柳仙等人),粵曲創腔的個人風格流派與代表曲目也隨之成熟。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廣州粵曲歌壇出現了爭艷斗技的局面,成就了廣州歌壇的鼎盛時期。③參見《粵曲》,第34-62頁。30年代末日軍南侵,1938年廣州淪陷后,歌壇紛紛停業,女伶紛紛四處逃散,隨之粵曲也進入了停滯期。
20世紀40年代,廣州的“歌壇”有所恢復,但相對30年代的輝煌已不能相比,在表演者群體上也不再局限于“女伶”,男性表演者也開始加入。④關楚梅、梁百川《回憶四十年代的音樂茶座》,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1952年,廣州市文聯組織一批著名藝人,組成了粵曲史上首個有政府經費補貼的民營公助性質的團體——廣州市曲藝大隊,由粵劇名角白駒榮任隊長,成員包括當時著名的粵曲藝人熊飛影、關楚梅、薛覺明等人;1954年,廣州市曲藝學會成立,并于1956 年在此基礎上更名為廣州市曲藝聯誼會;1958年,廣州市文化局將廣東民間音樂團與曲藝聯誼會合并組成廣東音樂曲藝團,主要配合建國初期國家的各項中心工作。⑤參見《粵曲》,第71頁。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粵曲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官方與民間共同發展的雙重模式,其職業表演者的社會身份也由此分化為了兩種類型:一種是延續著自20 世紀初以來茶樓歌壇的歷史傳統而主要在粵曲茶座表演的“民間表演群體”,另一種是專業學校⑥代表性學校是廣東粵劇學校(現更名為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培養下的以廣東音樂曲藝團為代表的主要在專業舞臺上表演的“專業表演群體”。
二、專業表演群體:廣東音樂曲藝團中的粵曲表演者現狀
本文所提出的“專業表演群體”是一個相對于傳統茶樓歌壇中的表演者的不同的群體。這個群體由于多畢業于廣東粵劇學校,且畢業后多直接進入廣東音樂曲藝團工作,因此他們在學藝經歷、生存狀態乃至音樂觀念與實踐等方面都與茶樓中的表演者多有不同。筆者于2017年1月間走訪了廣東音樂曲藝團演員駐唱的彩虹曲苑與愛群大廈鴻圖居,對這一群體的生存現狀進行了考察。
曲藝團演員概況廣東音樂曲藝團是當下廣東地區唯一專門從事廣東音樂和廣東曲藝表演的專業文藝團體,2008年改制后成立廣東音樂曲藝團有限公司,獲得國家補貼與資助,有專屬粵曲與廣東音樂的劇場彩虹曲苑。廣東音樂曲藝團擁有雄厚的創作力量,整理、創作、撰寫、編配了一大批優秀的廣東音樂和廣東曲藝作品,在社會上有較高影響力。筆者從廣東音樂曲藝團官方了解到:如今團中一共有20 名粵曲表演藝人⑦2017年1月資料,廣東音樂曲藝團喉管演奏家陳芳毅提供。——其中女性18 人,男性2 人;年齡最小的20 歲,最大的58 歲;從唱喉⑧“唱喉”是粵曲界對不同角色發聲方式的稱謂,分為子喉(女性角色與發聲)、平喉(年輕男性角色與發聲)、大喉(性格粗獷的男性角色與發聲)。來看,演唱子喉的11人,平喉7人,能夠同時演唱平喉與子喉的1人,同時演唱子、平、大喉的有1人;國家一級演員5 人,二級演員7 人,三級演員5 人,四級演員3人。整體來看,該群體通常受過較為專業的訓練,因而專業水平較高,多畢業于廣東粵劇學校(現為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具有扎實的曲藝與聲樂功底,不僅會唱粵曲,還會演奏民族樂器——何萍、梁玉嶸等著名粵曲“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均屬于該團。
曲藝團粵曲演出形式曲藝團的粵曲演出主要體現為“政府任務”性質的演出。廣東音樂曲藝團作為國家扶持的專業文藝團體,從其建團之初開始便主要服務于國家的文藝工作,因此,接受、承擔各級政府部門的外事、慶典、宣傳演出任務是其主要的日常演出工作——這與民間茶座中的娛樂性、商業性、市民性的演出有根本上的不同,更顯話語性與主導性。綜合來看,其演出類型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受邀請出席的重要的政府宣傳活動。如廣州市政府在日本東京舉行的“2017廣州《財富》全球論壇宣傳推介會”上,廣東音樂曲藝團國家一級演員,著名平喉演唱家梁玉嶸獻唱《彩云追月》,及與著名子喉演唱家廖綺對唱《帝女花·香夭》;2016 年由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廣東音樂曲藝團承辦的大型民族交響音樂會“偉大的征程——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民族交響音樂會”上,粵曲演唱名家陳玲玉、梁玉嶸分別登臺獻唱具有濃郁嶺南風格的新創作粵曲《星海·黃河》、《憶秦娥·婁山關》。第二類是由政府主導創作、排演的新曲目(劇目),例如2016年廣州市與佛山市人民政府主辦排演的描寫粵曲名伶小明星人生的粵曲舞臺劇《永恒的星光》。第三類是彩虹曲苑的惠民演出。彩虹曲苑是曲藝團的專屬劇場,設207個座位。作為團里的基本任務與工作,曲藝團每周六、日晚固定時間(19:30 至21:30)都會在彩虹曲苑二樓劇場,由曲藝團的20 位演員輪流出演——由單位里負責安排班表的人員指定,不能隨意更改,未被安排演出的演員可休息。彩虹曲苑的演出多為惠及喜歡觀看粵曲的老年人,演出票價便宜,多為30—50元。
除了完成上述日常工作任務之外,改企后的曲藝團也接受商業演出,其中既有曲藝團統一接洽的商業演出,也有曲藝團演員自己私下接的商業演出。
曲藝團演員收入情況雖然相對于民間藝人來說,廣東音樂曲藝團有國家撥款能夠保障基本工資,但仍有部分收入需要自負盈虧,這種體制給曲藝團的演員帶來一定的生存壓力。一般來說,廣東音樂曲藝團正式編制的粵曲表演者的每月收入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收入是國家下發的工資與補貼——據筆者在曲藝團所了解到的,不同演員根據職稱的不同,基本工資也不同,曲藝團喉管演員陳芳毅告訴筆者,國家四級演員基本工資為2 000—3 000元,國家三級演員基本工資為3 000—5 000元,國家二級演員基本工資為4 000—7 000元,國家一級演員基本工資為8 000元以上。另一部分收入是日常工作任務之外曲藝團或個人接演出所得的提成。演出地方覆蓋珠三角地區、香港、澳門、廣西等地,演員以此獲得額外收入。商業演出的提成不一,如果商演是由曲藝團安排的演出,則演員需要與曲藝團分成①關于詳細的分成情況,由于受訪者不愿透露,出于對受訪者意愿的尊重,在此不列明。,如果商演是演員個人尋找的,商演收入為個人所得。
三、民間表演群體:粵曲茶座中的表演者現狀
在茶樓中開設的專門演唱粵曲的“茶座”是粵曲表演的傳統舞臺,其前身可追溯到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歌壇”,在粵曲的發展歷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粵曲茶座與大眾日常的飲茶需求相符合,因此長期存在于市民生活之中。但是,經歷歲月變遷,粵曲茶座日漸式微的現狀讓人感嘆——筆者從2013 年7 月考察至今的過程中亦有所體會。在廣州,位于沿江西路的愛群大廈與大同酒家②大同酒家于2016年12月1月由于經營不善而關門停業;愛群大廈粵曲茶座由于酒店升級改造,于2018年4月26日關門,原茶座中大部分粵曲表演者轉到廣州泮溪酒家茶座駐唱。是較為穩定的兩個粵曲茶座,也是除了廣東音樂曲藝團彩虹曲苑之外的兩個重要的粵曲表演舞臺。這兩個舞臺為民間粵曲藝人群體提供了商業演出的舞臺,因此筆者主要對這兩個茶座中的藝人群體進行了調查。
粵曲茶座演員概況愛群大廈鴻圖居酒家長期以來一直是廣東音樂曲藝團商演的主要地點。1993 年開始,廣東音樂曲藝團的喉管演員陳芳毅與一批演員最早到愛群大廈13 樓開啟粵曲茶座,后來轉到15 樓的鴻圖居里——15樓場地大約能開15張12人的大桌。相對于其他粵曲茶座,愛群的粵曲茶座設備齊全。演出者雖然掛名廣東音樂曲藝團,但是筆者考察時發現真正團內的演員到場演唱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掛靠于其名下的非廣東音樂曲藝團名冊中的表演者。據現負責人陳芳毅介紹,該茶座樂隊有10 至13 人,表演者約有30 人,男性較少,每場只有1至2位男性演唱。
大同酒家距離愛群大廈不遠,入駐場地的是廣州最大的民營曲藝團——珠江曲藝團。珠江曲藝團是1985年成立的,與廣東電視臺有合作。該曲藝團最初叫作“廣州珠江廣播曲藝團”,90 年代初脫離了廣東電視臺自己經營;在1992 年的時候開始進入大同酒家演出。大同酒家粵曲茶座的表演場地十分寬敞,據實地考察得知,整個大廳能夠同時招待超過300名顧客,設施也是一應俱全,樂隊有統一的唐裝。據團長陳樹榮介紹,表演群體分為入冊人員和自由人員——入冊人員大約有30 人,其中男性有4人。由于大同和愛群距離較近,兩邊的表演群體會有所“重合”的情況——有的演員一日走兩邊的場,俗稱“跑場”。
總的來看,茶座中演員普遍呈現“老齡化”,大部分演員年齡集中在40歲—60歲,筆者在調查過程中遇到的40歲以下的演員僅5人。演員的來源較為復雜,其粵曲專業背景也不盡相同。筆者對在兩個茶座中演出的40名演員發放了問卷,同時進行了個案訪談后發現,按照專業背景的不同,茶座中的演員主要有三種類型。一類是前文提過的在正式工作之余在茶座駐唱的專業曲藝團演員——這類演員相對來說專業水平較高,但是人數較少且僅在愛群的粵曲茶座中有,筆者在考察期間僅遇到兩位。一類是民間劇團的演員,其中有不少是粵西民間劇團的演員。由于粵西地區的演出市場有很強的節令性,一般春節前后是酬神戲的高峰期,到了演出淡季,這些民間劇團的演員便會到廣州的粵曲茶座演唱一段時間。這些演員受過一定的科班訓練,有舞臺演出經驗,但相對于廣東音樂曲藝團的演員來說,其專業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除以上兩類外,茶座中的演員中還有一部分是通過自學或自己拜師學藝后進入粵曲茶座的。他們有的一直都以此為業,有的之前從事其他工作,由于愛好粵曲而在退休后進入到茶座中演出——由于大多未受過科班訓練,這類演員的專業水平顯得參差不齊。
粵曲茶座演出形式不同于曲藝團有國家扶持并以任務性演出為主,粵曲茶座的演出機制是完全市場化的,演出形式非常靈活自由。粵曲茶座演出時間一般為每天下午14:00—16:00,不售門票,只設最低消費,一般為16元/人——這個價格大約是“一盅兩件”(即茶位費與兩件點心的價格)的水平。在其中喝茶的客人都可以觀看粵曲表演,在觀看演出過程中,客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給表演者打賞紅包。每天茶座的演唱曲目不是提前安排,而是由演員與觀眾每天臨時交談后確定。演員的演唱順序每天也都不同,演員會提前告知茶座自己有空的時間,之后,由茶座負責人安排當天的演唱順序——由于最后的演唱者較為“吃虧”(觀眾走了較多),因此茶座負責人會輪流安排表演。
由于扎根于茶樓之中,與大眾日常飲茶需求相結合,與專業劇場“大舞臺”清晰的“觀演邊界”和規范的“觀演儀式感”不同,粵曲茶座中的“觀演邊界”總是處于流動中。這首先體現于,在茶座中,演員不僅僅是“表演者”的角色,也并不像曲藝團演員一樣很少與觀眾交流,相反,他們的表演不僅是在舞臺上為觀眾演唱,還包括在舞臺下為觀眾斟茶遞水、閑聊家常,以此換取更多的“感情利是”①“利是”是廣東方言,意為大吉大利、好運等。“感情利是”是茶座對紅包的稱呼。(紅包)。觀眾在觀看演出時也不需要正襟危坐,而是可以隨意走動、交談,上臺遞紅包,表演當中還有服務員穿插其中點餐、倒水等等——這一系列在正式劇場中被認為是打擾演出的行為在茶座中都是被合理化的,因此茶座中演員與觀眾的關系也更為親密。與專業劇場相比,粵曲茶座更像是一個日常社交空間,其中的粵曲表演更顯商業性,其形式更為自由。
粵曲茶座中的演員收入正如上文所述,茶座中演員的主要經濟來源是觀眾的“打賞”——和觀眾“感情”越好,收入(利是)便會越多。觀眾“利是”的賞錢數目一般根據其對演員的喜愛程度以及演唱水平而定,演員每日所得利是并不歸其一人,而是會根據每人每日所得金額大小,按照一定的比例與曲藝團(或茶座組織者、樂隊)進行分成。筆者通過對珠江曲藝團的陳樹榮團長采訪得知,演員收入按照當日“利是”所得的不同分成比例為:109 元以下,留團(伴奏+曲藝團)一半;110 至509元,留團四成;510 至909 元,留團三成;910 至19 999元,留團兩成;20 000元以上,留團一成。
關于紅包所得,由于涉及個人問題,受訪者多數避之不談。筆者根據兩次實地調查觀察到的紅包數量和金額對當日演員收入數據進行推測。2014年8月4日,筆者在大同酒家進行考察時發現茶座中演員收入差距較大,收入最高的演員高平(化名)約收400 元,大部分演員收入為100 元左右。演員的工資是日結,而伴奏工資則是月結。當日有七位伴奏樂師,據團長介紹每人工資約為200元,不比站在舞臺中央的演員收入低。當天曲藝團收入也有352元。這只是平日的數據,若遇上每月一次的小宴會,半年一次的大宴會,各方收入都會增加很多。例如,2014年9月5日,珠江曲藝團舉行中秋大宴會,當日的分成標準提高了不少,每位演員的收入也翻了幾番。有位演員艷華(化名)當日收到9 930 元,與曲藝團八二分賬后,獨得7 944 元。當然這只是個例。經筆者觀察,當日上臺獻唱的有30 位演員,平均每位演員拿到約1 000 元。在與8 月4 日的收入進行對比時,筆者發現8 月4 日收入最高的高平,在9 月5 日收入偏低,這說明演員的收入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但無論如何,大宴會上的收入都比平日多,演員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收獲頗豐,這是莫大的鼓勵和激勵。
從上述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下廣州粵曲從業者中存在著專業曲藝團演員與民間茶座演員兩個群體——這兩個群體盡管在日常演出中也會有所交集(例如愛群大廈中廣東音樂曲藝團的部分團員與民間自由職業者同臺演出的情況),但是在根本上,兩者在專業水平、經濟條件以及表演環境等方面有較大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兩個群體具體的傳承活動中的音樂觀念與實踐也不盡相同:茶座中的表演者由于生存多依賴于“利是”,運營完全依靠的是觀眾打賞紅包——這決定了其演出是以觀眾喜好為導向,過于注重與觀眾交際應酬卻往往忽視唱功的鉆研的,其專業水平參差不齊,為了迎合觀眾的喜好,多演唱粵曲的經典曲目,較少有個人的創新,風格也較為固化;而專業曲藝團中的表演者由于多受過專業訓練,對傳統唱腔、流派風格的傳承方面較為系統,另外,由于其長期表演的舞臺是城市現代專業舞臺,因此其表演多追求專業化的現代審美,在風格上也較多個人的創新。關于兩者音樂風格與傳承活動的差異,筆者將進一步撰文闡述,就本文的調查來看,兩類表演群體所代表的,正是傳統粵曲進入現代之后隨著城市經濟文化發展而分化出來的關于“專業”與“民間”的兩種敘事。認識到傳承者的主體差異性,不僅是我們理解粵曲當代變遷復雜性的切入點,也是未來粵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