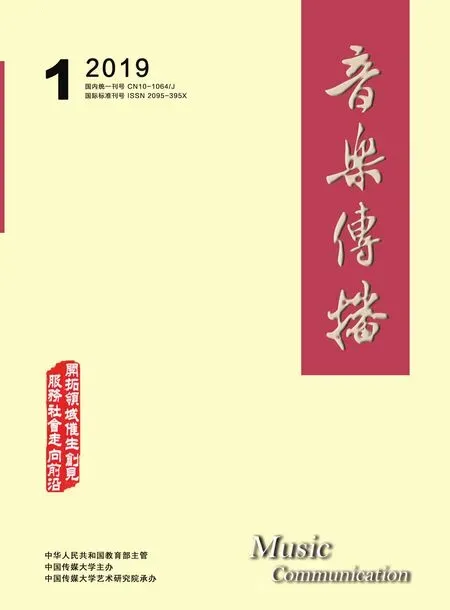昆曲在浙江地區的傳承與發展
■石 蕾
(浙江傳媒學院,杭州,310018)
昆曲是一種現存的、十分古老的中國傳統戲曲,其文辭典雅、唱腔細膩、表演精深,具有極高的、不可取代的藝術價值。它雖發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地區,①參見吳新雷《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但在明清之際便已發展為全國性的劇種。六百多年來,它經歷過“四方歌者皆吳門”的興盛期,也曾度過全國僅剩一個三十余人的正宗南昆戲班的頹敗凋敝、瀕臨滅絕的艱難歲月。可喜的是,如今它已成為人們探索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時的一件瑰寶,在當代展現出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功能。
與昆曲產生地江蘇昆山在地緣上相近的浙江,參與和見證了昆曲產生、發展、興盛、衰微、短暫復興、保護與傳承、創新與傳播的各個階段。在昆曲形成期,浙江古老的戲曲文化曾滋養了它,也得益于它;在昆曲興盛之時,浙江是其重要的傳播地之一;在昆曲衰微之時,它在浙江得以延續命脈,并曾有過短暫的復興。下面,本文將針對昆曲幾百年來在產生、發展、傳播與傳承過程中與浙江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做一初步梳理,闡述浙江對昆曲藝術的重要性,以期對今后昆曲在浙江的發展和傳承有所啟迪。
一、宋元永嘉南戲與海鹽腔對昆曲的滋養
關于“昆山腔”、“昆曲”、“昆劇”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在很多戲曲理論家的著作中都有所闡述。本文采用吳新雷在《昆劇的文化內涵和藝術特征》一文中的觀點,即“自清代中葉以來,昆腔、昆曲、昆劇三個名詞意義相同,互相通用”。①吳新雷《昆劇的文化內涵和藝術特征》,載朱恒夫主編《邁向精神殿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魏良輔在《南詞引正》中指出,昆山腔發源于元末的昆山地區。昆曲在經魏良輔改革之后,其唱腔細膩綿長、清麗婉轉,樂隊場面完備,從而逐漸受到文人雅士的關注,激發后者專門為其創作劇本。目前認為,梁辰魚的《浣紗記》是文人專為昆曲創作的第一部劇本,該作品也被眾多學者視為明清傳奇的開端。從此,昆曲走上了典雅脫俗的高格調之路,并在清乾隆年間被奉為“雅樂正聲”。而若論及昆曲的產生與形成,則其在唱腔音樂和劇本創作這兩個方面,均受到浙江古老的戲曲文化的影響。
昆曲作為南戲的延續昆曲在歷經幾百年的演出實踐與理論探索之后,在文學、藝術上都已經頗為深厚,并滋養了后世眾多的地方戲曲,從而被尊稱為中國傳統戲曲的“百戲之母”。當然,昆曲的劇本,即明清傳奇的創作,在文體上傳承自更早期的戲曲形式——南戲。南戲產生于北宋末年的溫州,也被稱為“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②參見徐渭《南詞敘錄》,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3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俞為民在《南戲流變考述——兼談南戲與傳奇的界限》中指出:“正因為南戲與傳奇在文體與樂體上沒有根本的區別,故在明清時期,戲曲家們視南戲與傳奇為同一種戲曲形式。他們在論及南戲或傳奇時,并沒有將兩者加以區分。在論及南戲時,也稱其為傳奇,反之,在論及傳奇時,也稱其為南戲,兩者常常互稱。”③俞為民《南戲流變考述——兼談南戲與傳奇的界限》,載《藝術百家》2002年第1期。吳新雷在《論宋元南戲與明清傳奇的界說》中講道:“在時代概念上,南戲是傳奇的前身,傳奇是南戲的延續,在宋元稱為南戲,在明清稱為傳奇。”④吳新雷《論宋元南戲與明清傳奇的界說》,載《藝術百家》1992年第3期。昆曲有一些經典劇目直接采用了南戲戲文,例如,被魏良輔評為“曲祖”的《琵琶記》即為南戲作者高明(元朝末年永嘉瑞安人)所作。《琵琶記》在明清時期已成為廣為流傳的昆曲劇目,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也被改編上演過多次,從而也成為當代昆曲藝術的一大經典。昆曲興盛之后,明清傳奇雖在思想性、文學藝術性等方面都超越了古老的南戲戲文,但其與南戲之間的繼承關系無可置疑。
昆曲對海鹽腔的吸納昆曲的聲腔是在南戲傳播到江南各地后產生的。徐渭的《南詞敘錄》列出了南戲的四種聲腔:余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和昆山腔。昆山腔創始于元朝末年,興盛于明清時期,至今一直延續著命脈,并成為中國傳統音樂的寶貴財富。海鹽腔大約出現于南宋,在昆山腔興盛之前,一直被視為“南曲正聲”。⑤參見葉長海《湯顯祖與海鹽腔——兼與高宇、詹慕陶二同志商榷》,載《戲劇藝術》1981年第2期。有學者考證,在當今的永嘉昆劇中可以找到海鹽腔的余響。⑥參見葉長海《永嘉昆劇與海鹽腔》,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一直以來,學術界對昆山腔和海鹽腔之間的關系是有爭論的。部分學者認為,這兩者是并列發展的,例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戴和冰認為“昆山腔與海鹽腔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影響,二者之間只是一種并行關系,而不是傳承關系”。⑦戴和冰《對魏良輔〈南詞引正〉所涉劇唱問題的再探討》,載《文化藝術研究》2011年第4期。另有學者認為,昆山腔源自海鹽腔,例如:南戲研究專家錢南揚先生認為“戲文在昆腔之前,早已用海鹽在演唱,到昆腔起來之后,海鹽腔日漸衰落,經過一段相當時間,新腔遂代替了舊腔”。⑧同上文。上海戲劇學院教授葉長海在《湯顯祖與海鹽腔——兼與高宇、詹慕陶二同志商榷》一文中肯定了詹慕陶的《商榷》對昆山腔與海鹽腔之間的關系的論述:“昆山腔與海鹽腔有著一脈相承、相吸收、相融化的血緣關系,它們是二又是一的,也就是說昆山腔是繼承和包括了原來的南曲正聲海鹽腔在內的,并漫延、接替和發展到了原來海鹽腔的家鄉(杭、嘉、湖)”;“昆腔無非比海鹽腔更為清柔而婉折,它們實是一體的”。⑨《湯顯祖與海鹽腔——兼與高宇、詹慕陶二同志商榷》。葉長海認為,“昆山腔是在海鹽腔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故而海鹽腔、昆山腔這一系統的腔調均以‘體局靜好’為特色”。⑩《永嘉昆劇與海鹽腔》。當然,無論是并列,還是繼承,昆山腔是晚于海鹽腔,并對海鹽腔有所借鑒的,兩者有著相似的唱腔氣質,只是昆山腔在經魏良輔改良和數百年的舞臺實踐之后,呈現出更加細膩綿長、清麗婉轉、雅致脫俗的面貌。
綜上所述,昆曲雖發源于昆山地區,但其戲劇文本的創作、唱腔的形成都深受浙江更早期的戲曲文化的影響,與之有著相似的基因,這也成為其后來能在浙江獲得廣泛傳播的原因之一。
二、明清時期昆曲在浙江地區獲得的廣泛傳播與研究
浙江省與蘇州、昆山兩地相鄰,有著相近的語言、民風,為昆曲的傳播奠定了廣泛的受眾基礎。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經濟上的繁榮和文化上的交流也為昆曲演出提供了物質保障、市場需求和創作源泉。另外,因為上文已經提到昆山腔的形成受海鹽腔的影響,與海鹽腔有著相似的唱腔氣質,所以同一劇本從海鹽腔演唱改為昆山腔演唱并不困難,這也促進了昆曲在浙江的發展。徐宏圖在《蘇昆入浙考》中指出:“昆劇于昆山誕生后不久即傳入浙江,并受當地觀眾熱烈歡迎而獲得迅猛發展,成為昆劇興起時最先傳播的地區之一。”他還進一步論證了昆劇入浙的時間約在萬歷元年(1573)之前的嘉靖、隆慶年間。①參見徐宏圖《蘇昆入浙考》,載《藝術百家》2010年第1期。昆曲在傳入浙江后,為適應各地民眾的欣賞習慣,在浙江多地形成了不同的支派,這些支派在此后為昆曲的傳承做出了貢獻;同時,浙江的文人雅士也創作出大量的昆曲作品,極為有力地推動了昆曲藝術的發展。
明清時期浙江各地昆曲支派和遂昌昆曲十番關于昆曲在浙江的支派的界定,學術界是有爭議的。例如,吳新雷在《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一文中將杭州、嘉興、湖州及紹興一帶流行的昆曲定為正宗的蘇州昆曲,即“正昆”,而把寧波、金華、溫州等地形成的“甬昆”、“金昆”、“永昆”等支派稱為“草昆”。他還指出,“草昆”是因當地演員多搭草臺唱戲,并且唱腔較粗率而得名,并列舉了浙江藝術研究所的洛地在《戲曲與浙江》一書第五章第六節中的相同觀點。②參見《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徐宏圖則在《浙江諸昆補考》一文中否定了“草昆”這一說法。他認為有關“草昆”的界定欠妥,并論證了所謂“草昆”戲班對蘇州昆曲的嚴格的繼承過程。他說:“昆曲既有‘蘭花’之雅,其種類再多也不會質變為‘草’,充其量只是‘聲各小變,腔調略同’而已。強然稱其為‘草’,顯然是一種偏見。”③徐宏圖《浙江諸昆補考》,載《戲曲藝術》2011年第3期。另外,他還將浙江的昆曲支派梳理為“興工”、“溫昆”、“金昆”、“寧昆”、“紹興昆劇”、“高腔、亂彈班中的昆劇”六種。無論如何,昆曲在浙江的興盛,首先表現為其支派較多,這些支派日后為昆曲的傳承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另外,昆曲在浙江的興盛還孕育出一種獨特的器樂演奏形式——遂昌“昆曲十番”。浙江檔案館的喬野撰寫的《遂昌·昆曲十番》一文指出,遂昌“昆曲十番”的演奏劇目以湯顯祖的劇作為主,采用傳統的工尺譜。④參見喬野《遂昌·昆曲十番》,載《浙江檔案》2009年第12期。洛地認為,遂昌“昆曲十番”的曲譜傳承自蘇州正昆。⑤參見殷颙《浙江遂昌“昆曲十番”音樂形態探析》,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遂昌“昆曲十番”與湯顯祖和昆曲都有密切的關系,對昆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它已被列入浙江省級和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明清時期浙江的昆劇創作與理論研究昆曲傳入浙江后,得到了浙江籍的眾多文人才子,以及曾游學或任職于浙江的不少文人才子的推崇。他們紛紛為之創作劇目,例如徐宏圖在《蘇昆入浙考》中提到的一大批明朝的創作者:徐渭(1521—1593,紹興人)的《罵曹》是如今昆劇舞臺的保留劇目,湯顯祖(1550—1616,曾在遂昌為官)的《臨川四夢》對昆曲影響之深更無須多言,高濂(1527—約1603,杭州人)的《玉簪記》自問世以來一直盛演不衰,另有沈鯨(約1573 前后在世,平湖人)的《鮫綃記》等大量名作。⑥參見《蘇昆入浙考》。此外,明末清初的李漁(1611—1680,蘭溪人)的《笠翁十種曲》中收有《風箏誤》,這也是當今浙江昆劇團的經典傳承劇目,而清初洪升(1645—1704,杭州人)的《長生殿》更是造就了“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昆曲盛況的兩部劇作之一。
除了劇目創作,明清時期這一帶的文人還有大量關于昆曲表演、創作、品評的理論成果,例如:徐渭的《南詞敘錄》是專門研究南戲的戲曲理論專著,其中不乏對昆曲的論述;李漁的《閑情偶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戲劇理論著作,與王驥德(1540—1623,紹興人)的《曲律》一起對昆曲演出實踐起了較強的指導作用;呂天成(1580—1618,余姚人)的《曲品》和祁彪佳(1602—1645,紹興人)的《遠山堂曲品劇品》中則都記載有多部昆曲作品,并有所品評。
明清時期昆曲在浙江的興盛還表現為“家班”眾多,這一點在徐宏圖的《蘇昆入浙考》中有詳細的論述。浙江人接納和喜愛昆曲,致使昆曲在浙江的支派較多,理論著述也較豐富,而這又為清末昆曲走向衰微之后,人們對昆曲的研究與傳承提供了極好的幫助。
三、“傳”字輩的活動重地和新編《十五貫》的誕生地
清末民初,以京劇為首的花部戲曲形式逐漸興盛,加之外來文化的沖擊、大眾文化的興起、新的娛樂形式的出現,以及社會的動蕩不安、社會階層結構的巨大變化,讓昆曲藝術喪失了大量的創作者與欣賞者,從而逐漸衰落、瀕臨消亡。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昆曲在浙江的支派一直維持著演出,除了寧波的昆班在1934 年后消亡之外,金華和溫州的昆班都在艱難中維系著昆曲的命脈。另外,上海紡織工業實業家穆藕初⑦穆藕初(1876—1943),愛國實業家、業余昆曲家,上海人。因十分喜愛昆劇和當時享有“江南曲圣”之稱的俞粟廬①俞粟廬(1847—1930),昆曲唱家,昆曲名家俞振飛之父,江蘇婁縣人。,于1920年選定杭州西湖邊的靈隱北高峰,在其山腰的韜光寺的一側建成一座以俞粟廬別號“韜庵”命名的別墅;1921年,他又邀請百代唱片公司為俞粟廬錄制唱片。羅亮生的《戲曲唱片史話》介紹了這張唱片,這也是俞粟廬被存留至今的唯一唱片。韜庵別墅曾留下余氏父子、徐凌云②徐凌云(1886—1966),字文杰,號摹煙,昆曲曲家,浙江海寧人。、沈月泉③沈月泉(1865—1936),昆劇演員,浙江吳興人。及“傳”字輩學員等眾多昆曲名人和昆曲傳承人的身影,為當時昆曲在杭州的演出、交流活動提供了場所。
從民國中后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昆曲也曾在衰微中有過短暫的、不太穩定的復興跡象。1921 年,蘇州的文人名士建立昆劇傳習所,但半年后就由于經濟陷入困境,由穆藕初慷慨解囊接辦。該所日后培養了21 位“傳”字輩演員。1927 年至1937 年間,“傳”字輩學員出師后,先后組成“新樂府”、“仙霓社”昆班,在上海等地演出。全面抗戰爆發后,昆班雖被迫解散、各奔東西,但“傳”字輩藝人的傳承活動并未停止。其中,周傳瑛、王傳淞加入浙江朱國梁等人創辦的“國風蘇劇團”,時有演出昆曲,劇團也在兩年后改名為“浙江國風昆蘇劇團”。后來到了1956 年,這個劇團演出的新編本《十五貫》在全國范圍內大獲好評。據統計,在1956年4月至5月這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北京共有7 萬多觀眾觀看了演出。④參見洛地《周傳瑛在〈十五貫〉轟動京城后的昆劇思索》,載《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人民日報也為之發表社論“從‘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談起”。此后,全國多地的昆劇團陸續成立,并效仿《十五貫》進行昆曲傳統戲的整理改編,昆劇演出和交流活動隨之開始活躍,昆曲的文化、藝術價值也重新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昆曲的思想教育功能也尤被文化部門所看重。另外,這個時期還出現過一系列有關昆曲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傳承與發展的理論研討。可以說,是“浙江國風昆蘇劇團”的新編本《十五貫》的成功引發了昆曲的短暫復興,全國由此掀起了昆曲傳統戲整理與改編的一次熱潮。
《十五貫》的演出成功有多方面原因:除了周傳瑛、王傳淞等“傳”字輩昆曲藝人的精湛表演外,這很大程度上還歸功于浙江省文化部門領導能獨具慧眼發現人才,并能大力扶持和協助劇團參與劇本的改編與創作,并為《十五貫》的演出進行精心的策劃與推廣。1956 年演出成功后不久,“浙江國風昆蘇劇團”便經浙江省文化局批準由民營轉為國營,并更名為“浙江昆蘇劇團”。在此后的三年中,“浙江昆蘇劇團”在全國十多個省的省會城市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演出,所到之地均遇盛情接待,可謂譽滿全國。⑤參見同上文。其間,劇團還上演了整理改編的傳統戲《西園記》、《鳴鳳記》和《救風塵》,在20 世紀60年代還上演過多部現代戲。在周傳瑛、王傳淞、周傳錚等藝人的努力下,劇團還接連培養了“世”字輩和“盛”字輩的昆曲傳承人。如今,“世”字輩的汪世瑜、“盛”字輩的王奉梅等都已成為國家一級演員和著名昆曲表演藝術家,為昆曲的傳承而不懈奮斗。
另外,蘇州市戲曲研究室于1962 年在寧波、慈溪等地的調查尋訪中發現了一批昆曲老藝人,并邀請了其中多位老藝人去蘇州傳藝。⑥參見《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當時,寧波昆曲老藝人向蘇州的昆曲藝人傳授了60 多出折子戲,⑦參見柯凡《昆曲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為昆曲傳承人的培養做出了重大貢獻。寧波昆曲老藝人的口述回憶也被整理匯編,為昆曲的研究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其間,浙江金華、溫州等地的昆班也有演出和昆曲學員培訓活動,比如:1958 年,永嘉昆劇團在上海演出《金釵記》、《琵琶記》、《當巾》、《追舟》等劇目,獲得戲曲界好評,該團還曾獲得昆曲大師俞振飛“南昆北昆,不如永昆”的稱贊;1962 年在蘇州舉辦的“蘇、浙、滬兩省一市昆劇觀摩演出”中,武義縣宣平昆劇團的《打狼屠》、《刺梁》和《見娘》也獲得好評。⑧參見《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可以說,這些從明清時期就開始形成的昆曲支派一直在浙江延續著其活動。
簡言之,民國中后期及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昆曲在浙江失去了曾經的光華,但“傳”字輩藝人和浙江寧波、金華、溫州等地的昆曲藝人們仍在艱難中維持著演出,使昆曲藝術得以活態延續。這一時期,“傳”字輩藝人在新中國的浙江省政府扶持下排演的新編劇《十五貫》曾掀起短暫的昆曲熱潮,這股熱潮也波及全國,引發了有關昆曲劇目、表演藝術等方面在新時期如何傳承與發展的研究。這之后,“傳”字輩又在浙江培養了大量的昆曲傳承人,這也為昆曲藝術在21 世紀的發展儲備了力量。
四、改革開放以來昆曲在浙江的傳承與發展
“文革”期間,昆曲表演活動中斷,人們對昆曲的理論研究也停滯了。而到了20 世紀70 年代末,中央一系列重要會議的召開和重要政策的落實使得中國傳統戲曲包括昆曲的發展重獲生機。80 年代,黨和政府大力扶持昆曲事業。1982 年,文化部對昆曲工作提出“搶救、繼承、革新、發展”的八字方針(此方針中的“搶救”在1995 年順應傳承態勢而修改為“保護”)。此后的幾年里,又有關昆曲的保護和享受特殊政策的重要文件陸續出臺;昆曲指導機構也成立了,負責昆曲人才培養和對昆曲傳統劇目進行音視頻記錄、文字記錄等搶救工作。①參見《昆曲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由此,昆曲再度出現短暫的復興。
1977 年,浙江省政府和文化部門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浙江昆蘇劇團”在全國第一個恢復建制,并更名為“浙江昆劇團”,隨后將包括《十五貫》在內的多個劇目陸續重新上演,并積極排演新編歷史劇如《楊貴妃》等,以及現代戲如《人情錢》等。1978 年,該團向全國招收了60 名昆曲學員,培養了林為林、張志紅等屬于“秀”字輩的優秀傳承人。而“永嘉昆劇團”也在1979 年恢復建制,并招收了30 多名新學員,還積極起用青年演員參加戲曲會演。該團雖在90 年代初消失,但十年之后又恢復了建制。蘭溪的“金家昆劇團”是在1978 年恢復的,隨后開始在金華地區的農村演出。
這一時期的浙江籍學者們也對昆曲進行了專門、深入的研究。比如陸萼庭(1924—2003,鎮海人)的《昆劇演出史稿》是我國當代第一部專論昆曲的著作,胡忌(1931—2005,奉化人)與劉志中合著的《昆劇發展史》也為昆曲研究開辟了新的研究視野;另有許多學者的大量學術論文,茲不贅舉。這些資料豐富、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成果,有力地促成了昆曲從這一時期開始被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的局面;而今昆曲有成為學科的趨勢,他們功不可沒。
20 世紀90 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際文化的交流,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習慣開始發生重大改變,而流行音樂的興起更是讓昆曲的細膩精深和悠長緩慢顯得跟不上“大眾趣味”。值得慶幸的是,2001 年5 月18日,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在這之后,有關部門更深地意識到了到昆曲在當今的生存挑戰和發展困境,由此再次出臺一系列全方位的、關于昆曲“保護、繼承、革新、發展”的政策,并及時、大力開展工作。如今的昆曲也有了多元化的發展,許多人也樂于通過昆曲陶冶情操,了解古人的生活樣式、精神狀貌及審美情趣,從而欣賞中華經典傳統文化和藝術。
目前,我國境內一共有七個在冊的昆劇團,其中兩個位于浙江。浙江昆劇團繼“傳”字輩在浙江立下“傳”、“世”、“盛”、“秀”四代傳人之后,又設立了按“萬”、“代”、“昌”、“民”排輩的昆曲傳承人培養計劃。“代”字輩已在2013 年開始招收,并于2017 年與“世”、“盛”、“秀”、“萬”字輩共同實現了“五代同臺”的演出。進入21 世紀,浙江昆劇團排演了大量的新編歷史劇和傳統改編劇,并多次獲獎。其中,新編歷史劇《公孫子都》在2012 年與《十五貫》一同入選“全國昆曲十大優秀劇目”。該團多年來還一直堅持在國內外積極開展昆曲藝術的傳播、推廣與交流活動。而浙江永嘉昆劇團(即1999 年成立的永嘉昆曲傳習所)在21 世紀初改編排演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三部南戲之一《張協狀元》,也在海內外受到廣泛好評。同時,浙江多地的昆曲支派都在政府扶持下被搶救與逐漸恢復。
進入21 世紀以來,昆曲理論研究也越來越精細。浙江籍學者如洛地(1930—2015,諸暨人)、葉長海(1944—,永嘉人)、俞為民(1951—,余杭人)等分別在昆曲的曲律、文學、傳承與創新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浙江雖不是昆曲的發源地,但卻在昆曲的產生與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藝術形式上,昆曲的劇本創作傳承于溫州南戲,昆曲的唱腔受海鹽腔的影響,與之有相似的氣質,都被文人喜愛;在傳播過程中,浙江是昆曲興起后最先傳播的地區,產生了多個支派,并有大量浙江籍文人致力于昆曲的理論研究,對昆曲的劇本創作和表演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昆曲在衰微之時,又在浙江得以延續活動,更是在新的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實現過復興,由此還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進入新世紀,昆曲已經成為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和唐詩、書法一樣,代表著中國最優秀的傳統文化藝術。浙江曾是“傳”字輩的活動重地,近百年來,遵照“傳”字輩的培養計劃,浙江已經培養出第六代昆曲傳承人。這些傳承人以及大量的學者,也定會為昆曲文化的發揚光大而繼續開拓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