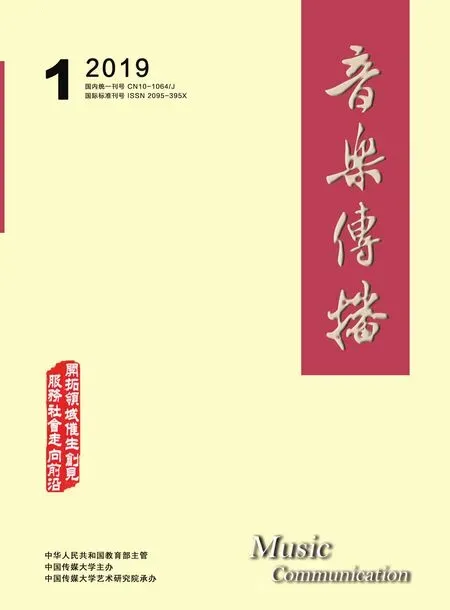單簧管協奏曲《帕米爾之音》的融創特色與藝術價值
■程梓峻 吳 霜
(廣西藝術學院,南寧,530022)
單簧管誕生于17 世紀末至18 世紀初,其音色變化多樣,音域寬廣,表現力豐富,是木管樂器組的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音樂家一直在努力探尋單簧管這一西洋樂器與中國音樂文化的融合發展,探求民族音樂在此可能的新形式。但是,在這樣的創作思路逐步確立后,成果方面卻不顯著,沒有出現公認的高質量作品,以至于有人對這一思路發出了一些懷疑的聲音。胡壁精①胡壁精,四川成都人,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音樂家。早年就讀中央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與作曲專業,隨后憑借扎實的演奏功底與過硬的音樂素養順利入職空軍政治部文工團。他起初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提琴的樂團演奏,后來在新成立的空政藍天幼兒藝術團兼任藝術總監。工作性質的變化給了他更多進行音樂創作的機會。在此階段,他創作了大量不同風格、題材的音樂:歌曲代表作有《搖起船兒走長江》、《吹吧,四化的春風》、《不朽的英雄楊建章》等;器樂曲有《打獅歌》、單簧管獨奏《塔吉克的婚禮》、雙簧管獨奏《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等;舞蹈音樂主要有《冰山戰歌》、《晨》、《一衣帶水情》等;大型歌舞音樂有《青春在藍天閃光》等。單簧管協奏曲《帕米爾之音》是1982年完成的。的《帕米爾之音》是單簧管進入中國后,由中國人為其創作的第一部協奏曲結構的大型器樂作品,它所獲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上述的懷疑。它既吸收西方創作技法的優點,又弘揚本土音樂的特色,以實踐證明了這條路的可行性。
管樂工作者應該對演奏的作品有全方位的認識:不應僅停留在技術層面,要站在更高的視角來審視作品的內涵。技術的呈現,誠然是研究的基礎,但對背景音樂文化認識的不足,則會導致藝術性上的缺陷。尤其是對于《帕米爾之音》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中西合璧”式大型作品來說,如果不對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及其開創性的創作思路進行分析、感悟,僅運用一般性的固有音樂風格認知習慣對其進行解讀的話,就很容易出現偏差,導致詮釋片面、風格不統一。本文將挖掘此曲獨到的創作思路,探究其蘊含的歷史文化背景,分析其在國內乃至國際社會產生的積極影響,總結其如何在管樂藝術發展、民族音樂傳播等領域成功應用,展示其獨特的民族化藝術特色,以促進這部優秀作品的傳承與推廣。
一、《帕米爾之音》的創作背景
單簧管協奏曲《帕米爾之音》是新中國管樂創作史上一次重要的嘗試,它突破了西方管樂藝術形式與中國少數民族曲調之間的屏障,標志著中國單簧管音樂的創作水平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胡壁精豐富的創作實踐經歷、文藝發展的時代需求、社會思想的不斷開放,以及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氛圍,都對這部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 世紀80 年代初,我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國民經濟尚未真正強壯,一切都處在某種新舊交替的關鍵節點,也讓一部分人對改革開放的洪流感到迷茫。這充滿矛盾與困惑的時期,催生出新中國的又一次思想解放①參見狄景山《“文革”與“文革”后的思想解放運動》,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第4期。,而文化藝術事業的蓬勃發展也是當時思想解放的一種集中體現。
單簧管進入中國較晚,由于當時的國人很少熟識這件外來樂器,所以遲遲沒有音樂家為單簧管創作中國作品。直到20 世紀30 年代,才有冼星海創作了《風》,這部為聲樂、單簧管與鋼琴而寫的樂曲讓單簧管首次擁有了“中國solo”。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簧管仍只是樂隊當中的一個聲部。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 年,時任中央音樂學院單簧管教授的張梧創作過一首單簧管獨奏曲《蘇北調變奏曲》,這是他在安徽北部的鄉村走訪采風時利用當地民間曲調的主題改編創作的,以西式樂曲結構搭配中國的民間曲調,發揮了單簧管的大部分特點,使之成了受到公認的中國第一首單簧管獨奏曲,可謂一次重要的探索。隨后,辛瀘光的《回旋曲》、《牧羊曲》等單簧管獨奏曲也相繼問世,但數量不多。直到80 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對外學術交流的機會與渠道日益豐富,對單簧管技術理論的研究也廣泛展開,其間大量的單簧管理論資料傳入國內,介紹了很多被西方視為主流的演奏技術,對當時中國單簧管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費奧多托夫的《單簧管演奏者表現音樂形象所使用的手段》、浮德爾的《演奏先鋒派音樂及單簧管新技巧的實際方法》等。此時,胡壁精成功創作《帕米爾之音》,既是對傳統民族音樂財富的又一次挖掘,也是對單簧管音樂中國化的又一份貢獻。相比此前篇幅普遍偏小、曲式較為簡單、缺乏更為深遠的藝術影響力的中國原創民族化單簧管作品,《帕米爾之音》無疑成了當時推動中國單簧管音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一個標志。
二、融創性實踐特色
《帕米爾之音》的成功是單簧管民族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此曲獨特的創作手法帶來了極具民族化特點的藝術面貌:作者親赴帕米爾高原采風,相當精準地挖掘和提煉了塔吉克族的音樂素材,并在遵循西方傳統創作形式的前提下,很好地呈現了民族特征和風格,深入詮釋了中國民族音樂文化的豐富內涵。這里的重點,或許在于其“融創性”思路。這個思路的成功實踐,在為今后類似的創作手法樹立標桿的同時,也極大地發揚了我國民族音樂的傳統精神。下面分三個方面詳細闡述筆者的以上認識。
(一)創作歷程
20 世紀70 年代末,胡壁精曾兩次踏上帕米爾高原,實地體驗塔吉克民族的生活與文化。②具體創作歷程參見李媛媛《胡壁精〈帕米爾之音〉單簧管協奏曲的創作之旅》,載《大眾文藝》2013年第2期。這片位于新疆西南的神秘土地以它壯麗的風景、淳樸的民風,深深吸引了來自遠方的客人。胡壁精通過參與牧民的日常生活,記錄、收集了當地大量的民族音樂和與之相關的習俗資料,其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一場盛大的婚禮。塔吉克族婚禮極具特色,熱鬧非凡、紅飛翠舞,牧民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慶賀,為新人送上自己的祝福。他們會將兩段分別象征牛奶和酥油的紅白綢緞妝戴在新人身上,祝愿他們的日子像牛奶和酥油那樣甜蜜和諧、吉祥如意。婚禮現場通常還會舉行叼羊比賽,過程緊張刺激,場面宏大。在婚禮的整個過程中,都會有年輕人在圍觀隊伍中跟著鼓手的節奏唱歌跳舞,或吹奏鷹笛,音樂極富感染力。胡壁精曾表示:“如果說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展現的塔吉克婚禮令你印象深刻,那親臨現場的感受只會更加震撼……淳樸的祝福,時刻都拉近著彼此的心靈,多年后仍回味無窮,難以忘懷。”
從帕米爾歸來的胡壁精滿腔熱忱,開始運用搜集到的音樂素材進行創作。1978 年,他隨部隊再次前往帕米爾高原,赴紅旗拉甫的空軍導航站進行慰問演出,這次他帶去了一部完全用塔吉克民族音樂元素創作而成的舞蹈音樂《冰山雪蓮》。這部作品的音樂主題同時也是日后《帕米爾之音》創作時的重要素材。
胡壁精在創作《帕米爾之音》時十分重視單簧管技法在民族音樂中的細節合理性問題。創作過程中,他與中央音樂學院擔任單簧管課程的黃遠涪教授進行了大量的單簧管演奏技術探討,在充分保證了協奏曲創作的嚴謹性的同時,充分融合了塔吉克的民間音樂元素。
(二)新疆塔吉克族音樂文化
“塔吉克”一詞意為“王冠”。塔吉克族歷史悠久,也是我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屬歐羅巴人種,其民族語言則屬于印歐語系伊朗語族帕米爾語支。塔吉克族人口的主體在中亞地區,分為“平原塔吉克”和“高原塔吉克”,居住在我國境內的是后者,他們通常在帕米爾高原東部過著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大部分聚居在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生產仍以畜牧業為主。當地群山環繞,南北兩側的山脈海拔均超過七千米,聳入雪線之上的山體常年積雪,冰川滿布,風光極其壯美。
塔吉克族同胞能歌善舞,每逢婚慶或節日,場面通常都十分熱鬧。這種場合,客觀上給分散在不同區域的牧民提供了一個交流音樂文化的場所,而且活動現場演奏的樂手還可以把這些音樂手藝傳承給年輕人。塔吉克族的原生民歌通常比較簡單,樂手和詩人更多是現場觸景生情,即興創作。這種即興編創的特性,維持著塔吉克族民間音樂旺盛的生命力,使其題材、旋律得到不斷的發展。
塔吉克民族音樂屬于波斯—阿拉伯樂系,其內容豐富,調式音階與節奏節拍方面也十分多樣。在音階方面,塔吉克音樂有著與新疆維吾爾族民間音樂十分接近的音列,有四音音列、五聲音階、六聲音階和七聲音階等。胡壁精在創作《帕米爾之音》時,深知單簧管是一件誕生在西方七聲大小調體系下的樂器,其設計符合的是西方七聲大小調音樂的演奏方式。為了避免演奏上的諸多不便,也為了更好地融合西方大小調體系,他在塔吉克民族音樂中提煉出了塔吉克升Ⅲ級七聲調式,而除此以外,五聲音階、六聲音階、四音音列均為不完整調式音階。除了豐富的調式音階,最能體現塔吉克族音樂特征的就是節奏與節拍了,7/8 拍與5/8 拍是塔吉克民族音樂常用的拍子,其中又以7/8 拍的運用最為廣泛。這種拍子的巧妙之處在于它往往有兩個重音——通常是由一個3/8 拍和一個4/8 拍組合而成。這種不對稱的節拍在我國其他各少數民族的音樂里極為少見,由此也極具辨識度。在《帕米爾之音》中,民族調式的精確提煉、特色節拍的巧妙運用,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可以說胡壁精的“融創性”思路的實踐不僅是對單簧管藝術發展的推動,更是對民族音樂文化自身內涵的升華。
(三)獨具匠心的“音畫”創作構思
《帕米爾之音》的創作,是一次東、西方音樂藝術融合的嘗試,而作曲家創作之初就確立的“音畫”構思更是其一大亮點。作曲家在音樂的呈現過程中,力圖做到每一段旋律都有畫面感,并賦予音響以想象力,在準確把握塔吉克民族音樂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彰顯了符合東方音樂審美的獨特神韻,讓作品真正做到了“形神兼備”。對此,我們按樂章順序來做分析。
第一樂章——沙漠駝鈴這個樂章講述的是在廣袤無垠的沙漠上,一支駝隊艱難地前行。全章幾乎使用了西方奏鳴曲式的標準寫作手法,但應為快板的第一樂章卻是中速的行板,并且以一段散板為引子來展開。舒展的樂句營造出了廣闊的意象,仿佛使人置身壯麗的帕米爾高原。作曲家使用升sol,并使之向下構成一個增二度,這一變化立刻體現了塔吉克民族的音樂特性。然后,“漂浮”在高音區的音符很好地描繪了沙漠的宏闊悠遠,而緊接著的連續下行的六連音將音樂交給了手鼓。音樂進入呈示部,畫面開始從模糊的輪廓聚焦到沙丘上前行的駱駝隊,節奏恒定,給人以任重道遠、前路漫漫的畫面。在手鼓的拍打中,單簧管被引出。此處的單簧管用中音區演奏,音色渾厚扎實,畫面的聯想也隨著聲音從環境轉入人物。其間,音樂多次出現“四-十六前附點”節奏型來強化塔吉克民族音樂的特征。
呈示部的副部主題的節奏、韻律與主部主題有很大的不同。雖然駱駝隊員的步伐依舊艱難,但音樂中多了一份樂觀與豪放,凸顯了塔吉克人民勇敢堅強、頑強不屈的精神世界。
展開部則表現了一場呼嘯的沙漠風暴,隨著急劇加速的下行半音七連音,聽眾也迅速墜入這場風暴。兩個主題不斷交叉變幻,連續三組下行增四度模進不斷將風暴推向高潮。華彩樂段的出現標志著風暴已經結束,雨過天晴,單簧管此時音色柔和,兩小節后重新回到主部主題上來,駱駝隊繼續他們的征程。
第二樂章——高原之夜第二樂章是一個帶有再現的復三部曲式,嚴格遵循西方協奏曲的結構要求。樂章伊始,弦樂輕柔地奏出引子,帕米爾高原寧靜祥和地沉睡在夜空下,湖邊年輕的塔吉克族戀人正在彼此耳語。良辰美景下,單簧管緩緩奏出第一段主題,它靜謐、深情,像一段情歌娓娓動聽。然后,轉入中速樂段,出現相對自由的單三部樂段,旋律變得熱情而富于張力,緊接著是一段華彩性質的單簧管獨奏,密集快速的琶音經過句配上樂隊的呼應點綴,從聲效上增添了幾分湖面波動的美感與夜色中未知的神秘感。最后的再現段,主奏單簧管完成連續下行琶音后重新回到柔美的夜色中,湖面漸漸恢復最初的平靜,高原夜色重新籠罩大地。單簧管用一連串密集、輕柔的上行音符將詩情畫意的氣氛拋向帕米爾的夜空,結束該樂章。
第三樂章——高原婚禮該樂章熱情奔放,為快速的回旋曲,展示著塔吉克族婚禮熱鬧非凡的場景。它是《帕米爾之音》中最先被創作出來的樂章,當時也是專門為單簧管創作的,此事前文已有提及。樂章開門見山,樂隊以極強力度的演奏迅速將聽眾帶入盛大的慶典當中。隨后,樂隊迅速奏出連續的后半拍節奏型,似乎騎手已躍躍欲試。單簧管緊跟著用裝飾音帶出兩句長音,像號角一樣宣布婚禮上的叼羊比賽拉開帷幕。緊湊的主題旋律表現著騎手們比賽時的英姿,贊美著塔吉克族小伙子無畏的氣概。第二部分,樂曲韻律發生變化,出現了塔吉克族傳統音樂最具特征的7/8 拍子,仿佛親朋賓客們翩翩起舞。第三部分,樂曲回歸到賽馬叼羊的節奏上來,掀起樂章的高潮兼全曲的高潮。大段的長線條音階,配合著樂隊合奏,在對慶典盛況進行刻畫的同時充分展示出塔吉克青年的熱情和活力。樂曲最后用連續的快速三連音推進情緒,結束在無盡的歡騰之中。
三、《帕米爾之音》的藝術價值
單簧管傳入我國已經一個世紀,其間經歷了與我國民族文化發展融合的漫長過程。而單簧管藝術真正在中國得到發展,顯然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帕米爾之音》正是在這樣一個單簧管民族化的關鍵時期問世的,其中西結合的獨特思路對當時的中國單簧管教育、中國管樂的推廣,以及中國民族音樂發展等方面都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可謂一部藝術價值很高的作品。
(一)對中國單簧管教育事業的影響
長期以來,我國使用的單簧管教學體系均來自西方,基本以歐洲傳統教學法為基礎,除了樂曲是外國作品,音階、練習曲等教材也都源自西方體系。這些作品與教材對專業教育來說或許的確是練習演奏的佳選,但對普及教育來說就有一定的難度和深度了,其風格韻律與國人的音樂審美習慣的距離、音樂語匯的不同,使得初學者練習起來較為困難。
當今我國的單簧管教育發展態勢興盛,專業類院校的單簧管教師大多具備較高的音樂素質,熟悉西方音樂體系的教學模式,對西方音樂作品的理解也較為系統,而普及教育層次的教師隊伍水平參差不齊,對西方作品風格的把握很多時候并不十分規范,也較缺乏系統性,不利于我國單簧管藝術的全面發展。《帕米爾之音》的出現,為我們提示了一種新的思路:多運用大家所熟知的各民族風格音樂為教材,讓學生在易于接受的樂曲里練習發音、氣息等基礎技能,不僅可以避免形成一些不良演奏習慣,還可以提高學習效率,增長學習興趣。誠然,前面提到的《蘇北調變奏曲》、《回旋曲》等民族化單簧管作品在技術上較為簡單,更適合初學者上手,但如果沒有《帕米爾之音》這樣的作品,我國單簧管教育中的樂曲需求也無法得到更全面的滿足。協奏曲的體裁融入塔吉克民族風格的素材,不僅有利于學生積累多種作品風格的經驗,更有助于在技術水平方面進行拔高訓練。同時,《帕米爾之音》出于其宏大的規模和豐富的技術內涵,一問世便被許多藝術院校列為教學大綱中的必練曲目,也為專業層面上的單簧管藝術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資源。
(二)對中國單簧管音樂推廣的貢獻
前文已述,20 世紀80 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讓全國經濟復蘇,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帶動文化的建設,中國與外界的交流也日益頻繁。乘著這股東風,中國單簧管藝術得到快速發展,《帕米爾之音》正是此時一次成功的民族化嘗試。1986 年,我國著名單簧管演奏家、中央音樂學院陶純孝教授給予此曲充分的肯定,并且在受邀參加世界單簧管協會該年的年會時親自演奏了此曲,在場的各國大師對此曲頗不吝溢美之詞。單簧管演奏家約翰·丹曼后來也曾公開演奏該曲,并給予高度評價。此后,《帕米爾之音》經常代表中國單簧管音樂在世界各地上演,在許多國際單簧管學術交流活動中,它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事實證明,吸收西方交響樂精華,提煉本民族優秀音樂文化,使二者有機結合,是推廣中國單簧管音樂的一條可行之路,我們還需要更多這樣的優秀作品,助力中國原創音樂的海外流行,讓中華優秀藝術文化發揚光大。
(三)對民族音樂傳播能力的拓展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間藝術種類繁多,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儲備豐富。這些音樂文化是在勞動人民長期的社會行為中醞釀形成的,飽含了我們民族的文化精髓,是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音樂文化的對外傳播,可以使國際社會進一步了解中國,并促進人類文明的交流溝通。
長期以來,塔吉克民族的音樂都是口傳心授,其主要功能大都與族群的生活禮俗密切相關,許多曲調都是在生產勞動和婚喪嫁娶的人生時序中產生和發展的。當今,隨著技術的高速發展,不少塔吉克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變化,處于原始生活狀態的人數正在減少,越來越多的人在向城鎮轉移,因此與民俗伴生的傳統音樂也在逐漸失去其生存土壤,這同時也降低了塔吉克族音樂內部傳承和向外傳播的能力。胡壁精以交響化思維對民族音樂進行創作,將中國民族音樂元素融入在西方更為通行的交響樂形式中,無疑較好地提升了民族音樂的海外傳播潛力。
1986 年陶純孝在世界單簧管協會年會上展示《帕米爾之音》后,不斷有外國的單簧管演奏家找到他,想要獲得樂譜,以便將其列入自己的音樂會曲目。可見,《帕米爾之音》作為有強烈的中國民族音樂風格的交響化單簧管作品,在國際樂壇上已形成一定的影響,讓我國的少數民族音樂元素獲得了更為廣闊的藝術空間。《帕米爾之音》的成功,展示了中國民族音樂曲調在現代音樂理論體系下勃發出的新力量,豐富了多元化的當代音樂形式,在發揚民族音樂文化的基礎上,促進了中國原創音樂的海外傳播,堪稱可資借鑒的優秀案例。
結 語
綜上所述,《帕米爾之音》至今仍在開發本土音樂資源方面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這部單簧管協奏曲的總體形式雖然談不上十分新穎,甚至還略顯保守,但因為作曲家深度挖掘了民族音樂的精髓,在創作上又大膽啟用了一些新手段,充分利用了單簧管的技術優勢,所以還是在“音畫”性質這一具有標題音樂特點的創作框架下,很好地呈現了塔吉克民族音樂的某些核心審美,同時也給我國傳統民族音樂的傳播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當下指出了一條可行之路。
筆者認為,通過對這部作品和今后可能出現的同類作品進行文化背景、創作特色、社會效用等的細致分析,不僅可以深化對民族化交響樂的理論認識,也利于把握民族音樂語匯的實踐風格,進而推動其國際化。因此,筆者衷心希望更多的單簧管演奏者、創作者和傳播者能在這方面有進一步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