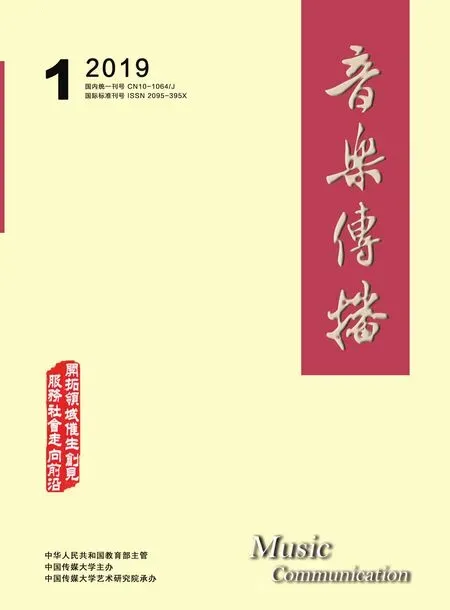嶺南音樂文化在馬來西亞的傳播及其影響
■劉藝超 劉德波
(韶關學院,韶關,512000)
嶺南音樂文化是一種內涵復雜的音樂文化(嚴格說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筆者提到的嶺南音樂是指廣義的嶺南音樂,后詳),它主要通過移民和文藝表演傳播到馬來西亞,對馬來西亞尤其是其華人社區的音樂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文擬從音樂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簡要探討嶺南音樂傳播的歷史、條件、內容及其作用。
一、嶺南音樂及其文化上的界定
我國地理學稱五嶺之南為嶺南。在當今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嶺南音樂是一種旋律節奏明快婉轉、以廣東音樂為主流的,具有濃郁民間風味且和中國其他地區具有明顯區別的音樂。它形成于19 世紀中晚期,常使用裝飾音和“加花”的音調,具有最近一百多年來嶺南文化“中西結合,古今結合”的特點,其開放性以及包容性十分顯著。進入20 世紀后,隨著廣東的經濟、文化實力的提升,嶺南音樂在全國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應該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廣東音樂成了嶺南音樂的核心,它發展了嶺南音樂,因此嶺南音樂也就成了世人印象中的“廣東音樂”。①劉德波、劉藝超《廣東傳統樂舞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載《音樂傳播》2017年第2期,第74頁。其實,嶺南音樂也包括我國湖南、廣西、江西、海南、香港、澳門、臺灣等地的音樂形式和內容。過去有不少人忽略其中這些地區的音樂成分,可能是歷史性文化傳播、音樂文化考古、資料搜集整理等方面的條件限制使然。從發展和豐富嶺南音樂的使命出發,從提升音樂文化的品位出發,現代的我們應該解放思想,打開眼界,努力健全“嶺南音樂”的時代定義,這對繼承和發展嶺南音樂將是有益的。①黃太聞《重新定義嶺南音樂》,“演出網”博客,2008年6月14日。http://user.show160.com/1284976/blog/a36971
這也就是說,嶺南音樂在論述時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嶺南音樂是指廣東音樂,而從廣義來說,則要包括上述諸多地區的此類民間音樂。顯然,下面所談到的嶺南音樂是廣義的。
另外,“音樂文化”一詞雖在學界頻繁被使用,但其概念也容易導致誤解與混淆。比如,不少人有這樣的誤解:音樂文化的內涵和“音樂藝術”是一樣的概念。嚴格來說,“音樂藝術”的藝術形式是存在某種標準的,它實際上是由規律性的音樂所形成的聽覺審美對象,而音樂文化包含的內容更為豐富,音樂藝術只是在其范疇之中,卻不是其全部。音樂文化的內涵包括各種性質、各種形式以及發揮各種作用的音樂現象,它們和音樂藝術的關系都很密切,但也存在各自的差異,這些差異體現于它們自身的特征、性質以及作用等方面。所以,本文要探討的也是“音樂文化”概念下的各種文化現象,并非某種藝術形式的品位和審美屬性。于是,筆者闡述的嶺南音樂文化不僅以廣東音樂為主,也包括嶺南地區的各種音樂藝術,還包括這些藝術的相關歷史和文化。
下面,筆者主要從中外音樂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探討嶺南音樂文化在馬來西亞傳播的歷史及其影響。
二、嶺南音樂在古代馬來西亞的傳播
古時候,華人移民是馬來西亞的嶺南音樂文化的主要傳入者。華人向東南亞一帶移居已經擁有較久的歷史,其中福建、廣東一帶的華僑占據人數優勢,他們自然把家鄉的音樂文化帶到了新的居住地。鄭和下西洋時,有一批隨行人員負責記錄、檔案整理等工作,其中費信、馬歡、鞏珍等人都是當時知名的學者,他們隨船隊回國后分別著書立說,留下了著作《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這些書在記載旅途見聞的基礎上,也介紹了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音樂狀況。另外,鄭和隨帶的樂師以福建泉州樂師為主,下西洋后還有一些隨行士卒留居當地,這些都有利于閩粵地區的音樂在東南亞的傳播。至清末民初,閩粵沿海一帶的樂種和劇種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已經有了較為顯著的影響,至今猶存。②馮文慈著《中外音樂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98 頁。
自明至清,從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向馬來西亞移居的人很多,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其中,來自福建泉州、漳州兩府的占大多數,來自廣東的也不少,主要是廣州人、潮州人以及客家人。19 世紀末之前,移民以男性居多。前往南洋后,馬來西亞是他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們一開始多與巴塔克和巴厘女奴聯姻,后來其經濟狀況逐漸向好,能與馬來西亞女人結婚的隨之增多,土生華人社會文化群也慢慢形成。清代的馬來西亞土生華人社會以馬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為中心(當時新加坡因各種條件的限制,還未獨立建國)。③林延青、李夢芝等著《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頁。1801 年,他們在檳榔嶼成立了最早的地域團體——廣東暨汀州會館,以及仁和公司。1805 年,惠州會館在馬六甲成立。隨著當地華人社會不斷發展,各類地域團體的數量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比如檳榔嶼,到1850 年已經有中山(1805,指成立年份,后同)、番禹(1819)、五福堂廣州(1819)、汀州(1819)、惠州(1822)、南海(1828)、安陽(1833)、順德(1838)、增龍(1849)等十多家會館;而在馬六甲,也增添了茶陽(1821)、應和(1821)、潮州(1822)、寧陽(1828)、福建(1843)等著名會館。④賀圣達著《東南亞文化發展史》,云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471頁。這些會館的設立,為嶺南音樂文化在當地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19 世紀上半葉,中國戲劇已在馬來西亞受到廣泛的歡迎。中國戲的演出遍布當地社會多個角落,包括村邊、街頭、廟宇以及戲院等,觀眾數量不可小視。同時,華人的節慶活動上,文藝演出也是必不可少的內容。此時馬來西亞的中國戲表演已經具有一定的水平,不僅文戲、武戲兼備,而且有豐富的角色譜系和相當高超的技藝。當然,學者研究表明,當時他們的服裝、化妝、表演方式、伴奏音樂、舞臺布景以及戲院格局都與中國大陸幾乎一樣,戲目也以傳統的中國戲為主,⑤王靜怡著《中國傳統音樂在馬來西亞的傳播與變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頁。可見古代嶺南音樂文化的傳播主要是由中國移民擔當的。
三、嶺南音樂在近代馬來西亞的傳播
近代,馬來西亞華人社區進一步取得較大的發展。19 世紀下半葉,舊有的會館得到鞏固,新的會館又在馬來西亞各地紛紛建立。至19 世紀末,福建、廣州、潮州、客家、海南已經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的5 個大幫。⑥《東南亞文化發展史》,第471頁。各幫下屬的會館數量都在一百家以上,可窺見當地華人社會之興盛。以會館為主的地域華人組織,帶來了包括音樂文化在內的各類中華文化,使地域文化得到了維持與繼承,同時又以經濟為紐帶,“宗幫而經商”,為音樂文化的傳播積累著物質條件。
比如,馬來西亞的民歌受中國民歌特別是《詩經》與其他傳統民歌的影響較多。土生華人在馬來民歌的創作過程中,融入了很多關于中國的文化與風俗。英國學者溫斯泰德在他的著作《馬來文學史》中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馬六甲的中國居民對馬來民歌產生影響;馬六甲的中國僑生則在創作馬來民歌的過程中,注入了悅耳的押韻,塑造了形象和意境。①周南京《回顧中國與馬來西亞、文萊文化交流的歷史》,載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頁。這里提到的中國僑生,就包括來自廣東的華人后裔。
在1920 年之前,有大批中國戲班和傳統音樂藝人赴南洋地區演出,自然有不少到過馬來西亞。以廣東粵劇戲班為例,有史料顯示,小埠戲班的規模為30 至60 人,大埠的戲班更是可達100 人。其中永壽年班名氣較大,班中名角甚多,例如扎腳勝、丁香耀、出海蝦、聲架悅、大眼順、新細倫等,其《斬二王》、《海鹽名流》以及《三氣周瑜》等劇目最具代表性。單獨前往馬來西亞演出的演員也不在少數,這些演員往往參加到當地戲班中,比如著名粵劇演員靚元亨、新華等人,都是當時馬來西亞戲班中的名角。另外名聲較響的還有振天聲劇團。1908年,由于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國喪”期間完全禁止文藝演出,該劇團就在黃詠臺的率領下到馬來西亞巡演,并且在暗中進行革命宣傳。他們的代表劇目有《熊飛起義》、《博浪擊殺秦》、《剃頭痛》等,孫中山曾觀賞演出并表示十分贊賞。該團在馬來西亞演出的地點包括吉隆坡、霹靂州以及太平等地,各埠也均表現出熱烈歡迎。②《中國傳統音樂在馬來西亞的傳播與變遷》,第29-30頁。
至于瓊劇,其傳播地帶也包括南洋地區。當時,也有瓊劇班前往新、馬地區,比如1893 年,瓊劇名旦鄭鴻鳴逃至南洋后就在那里演出。這個時候,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而產生反清思想的瓊劇藝人普遍活躍,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瑞蘭。他逃亡到南洋成立了“星州劇社”,并為支持星州碼頭工人罷工而舉行義演。同時期,瓊劇藝人吳長生也多次在新、馬演出。這些戲班及藝人演出的劇目主要有《賣胭脂》、《張文秀》、《林攀桂》、《師姑偷詩》、《父子同科》等。③王裕群《瓊劇在南洋的發展史話》,載《華僑史論文集》,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1983年編印,第293頁。
西秦戲,是廣東東部沿海地區的古老戲種。順泰源戲班以演出西秦戲而著名。在1903 年以前,這個戲班已經到過新、馬等地演出,受到當地華人社會的歡迎。另外,廣東木偶戲也在馬來西亞得到流傳。比如1911 年,廣東木偶藝人鄭萬楷就和他的木偶戲班在新、馬演出獲得成功。
傳統的粵劇戲班在馬來西亞上演了不少新戲,對革命進行大力宣傳,表現出對封建專制的反抗。比如由名角京仔恩演出的《徐錫麟刺恩銘》以及《蔡鍔云南起義師》等,均有反清思想的體現。另外瓊劇《蔡鍔出京》也是宣傳革命的劇目,由王器民、吳發鳳等人編寫。值得一提的是,還有許多富有愛國意識、民族意識的傳統劇目在這一時期上演,如粵劇《大反雞林園》、《岳飛報國》、《王佐斷臂》等,這些傳統劇目以古喻今,激發了海外華僑的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
文明戲也在馬來西亞廣為流傳,粵劇大師馬師曾就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演出過《癲》、《嘲》、《廢》、《憨》等戲,還和演員陳非儂合演《古怪公婆》等戲,受到當地華人好評。
四、嶺南音樂文化在現當代馬來西亞的傳播
進入現代,嶺南音樂文化更加頻繁地傳入馬來西亞。20 世紀20 至30 年代,包括廣東的潮劇、粵劇、瓊劇、漢劇、粵曲等在內的15 個劇種和曲種的演出團體曾到馬來西亞演出。如1921 年,廣東新戲的“新天彩”戲班,“科班超群童子班”曾前往馬來西亞演出;1932 年,粵劇演員少昆侖所組劇團以及白玉堂等人的劇團陸續前往馬來西亞演出;1936 年至1938 年,勝壽粵劇團、覺先旅行粵劇團以及瓊劇五組戲班先后到馬來西亞演出。在抗日戰爭初期,當地粵劇、瓊劇、潮劇等活動也仍在堅持進行。
20 世紀下半葉,馬來西亞的華人創立了一些帶有研究性質的文藝社團。如1963 年5 月25 日成立的吉隆坡劇藝研究會、1969 年9 月30 日成立的南馬文藝研究會等。④石滄金著《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研究》,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419頁。這些社團的建立和活動,也有助于嶺南音樂文化在當地的深入普及。
后來,港澳臺地區有許多華人歌手前往馬來西亞。比如Beyond樂隊的主唱黃家駒曾于1993年在馬來西亞舉行演唱會。在當代,廣東的流行音樂在馬來西亞廣為傳播,且有了更大、更重要的平臺,比如“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它也是中國其他地方的流行音樂對外傳播的重要平臺)。該流行音樂排行榜由中國的上海東方廣播電臺、廣東人民廣播電臺“音樂之聲”、北京音樂臺、香港電臺、臺灣HitFM聯播網,以及馬來西亞的“FM988”、新加坡的“醉心頻道933”等七家電臺共同舉辦。2013 年5 月21 日,該排行榜還在吉隆坡召開媒體發布會,宣布“第十三屆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頒獎禮”于該年10月5日在馬來西亞舉行。①潘忠黨《傳播媒介與文化: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的三個模式(下)》,載《現代傳播》1996年第5期,第21頁。該屆“頒獎禮”以“玩強音樂”為主題,旨在提倡向一些優秀音樂人看齊,學習樂觀態度“玩音樂”、在音樂道路上堅持“打不死”的精神,以及他們在音樂創作和演出中頑強的生命力。馬來西亞“FM988”為主辦臺。發布會還邀請了演出歌手胡彥斌、張煒、梁佳杰和伍家輝等,馬來西亞多位歌手也在現場參與了這一音樂界盛事。
五、小結
嶺南音樂文化在馬來西亞傳播的影響是顯著的、多方面的。第一是加強了馬來西亞華僑社會的凝聚力。馬來西亞華僑通過組織相關藝術社團,通過嶺南音樂藝術這個紐帶緊緊地團結起來,有利于自身的發展。第二是豐富了馬來西亞華僑社會的精神生活,通過“鄉音”沖淡了“鄉愁”,讓人們在祖國音樂的感染下陶冶情操,推動個人精神品質的升華。第三是有助于中馬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當前,中馬關系越發密切,文化交流也更頻繁,嶺南音樂自然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在外交舞臺上發揮著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是為馬來西亞培養了音樂藝術人才,如馬來西亞著名歌手梁靜茹。
可以說,以廣東音樂藝術為代表的嶺南音樂文化在馬來西亞的傳播,既得益于華僑、華人的努力,也得益于嶺南音樂藝術工作者的辛勤勞動。馬來西亞華僑立足當地,致力于嶺南音樂藝術的傳播;而嶺南藝人赴馬來西亞演出,不僅在特定歷史時期傳播了革命思想,也今昔皆然地弘揚了嶺南音樂文化。同時,文化交流并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2013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時,在歡迎午宴上的致辭中還特別提到梁靜茹。梁靜茹在中國擁有很多的歌迷,以至于許多人以為她也是中國人。應該說,梁靜茹是馬來西亞音樂長期接受嶺南音樂文化的浸潤后,在當代“回饋”中國的一個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