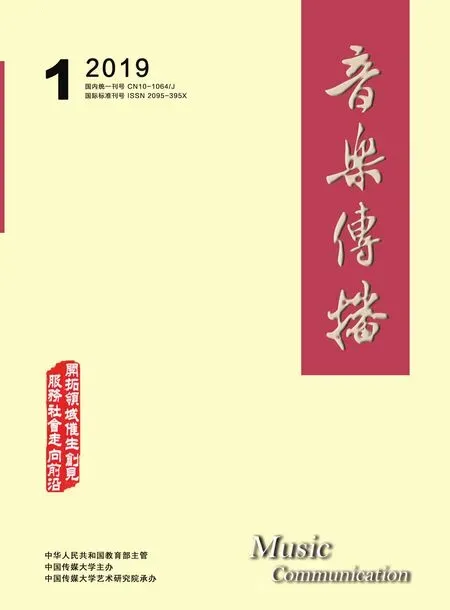數字技術對音樂錄音再現性與表現性的影響
■門子玉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100024)
音樂錄音的再現性和表現性一直是音樂錄音研究者熱議的話題,當然二者也沒有對錯之分。而近年來,錄音藝術在技術層面上不斷有飛躍性發展,各式各樣的模擬周邊設備已被豐富多彩的音頻工作站應用插件所代替。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過程,不但體現出錄音技術已響應了音樂錄音對更真實的再現性和更豐富的表現性的需求,更體現了音樂錄音作為一門藝術對技術層面產生的推動作用。據此,本文將從筆者的音樂錄音實踐出發,在簡要回顧錄音技術史中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對音樂錄音的再現性和表現性特征進行比較,以便探究數字錄音技術對音樂錄音之再現性與表現性的影響。
一、音樂錄音技術相關發展概說
鑒于音樂錄音所用技術的發展變化史相當宏偉和復雜,筆者在此僅從聲道數量、母版品質、模擬與數字錄音的基本對比等角度做出略述,為后文關于數字技術大發展背景下錄音藝術再現性、表現性的研究權作一思維鋪墊。
(一)前期錄音中的聲道數量變化
音樂錄音經歷了單聲道、雙聲道、多聲道的發展歷史。到20世紀50至60年代,音樂產品即以水星(Mercury)公司的3 聲道錄音而引人注目(當時其使用的是35mm 磁性電影膠卷,拾音以3 只Shoeps 話筒進行)。當然,三聲道錄音的著名代表還有RCA 和VICTOR 等公司。到70 年代,五音(Pentatone)公司出版的4 聲道作品享有盛譽,其錄制時使用的是四軌模擬開盤磁帶,出版載體則為33 又3 分之1 轉的密紋唱片。這種錄音對音樂的解析力又有所提升,擴展了頻響范圍和動態范圍。
如今的多聲道已經遠不局限于這些模式,不僅有5.1聲道環繞聲,還有更讓人眼花繚亂的7.1聲道、7.2.4聲道等。如果結合采樣深度(位寬)來看,則又有8 位單聲道、8位立體聲、16位立體聲、多通道16位立體聲、多通道24 位立體聲等之分。可以說,多聲道錄音技術目前趨近成熟,為音樂錄音的更多藝術需求,當然也為其對再現性與表現性的追求架起了技術的橋梁。
(二)后期制作中的母版品質提升
若要追求更近乎完美的音質,更好地還原再現性的與表現性的音樂,則獲取音質更高的母版是一種堪稱從源頭著手的思路。在音樂錄音的制作領域,隨著相應技術的發展,原始錄音的分辨率在不斷提升。PCM 已從44.1kHz 采樣率、16 位量化發展到176.4kHz 采樣率、24位量化,此外更有攜帶著更高采樣率的DXD(352.8kHz采樣率、24位量化)。分辨率的提升,為更高音質的原始錄音提供了技術上的基礎。
母版重制(re-mastering)的規則也在改變。過去的音樂錄音母版是從模擬磁帶或者DASH 數字磁帶、DAT數字磁帶和MO出發進行重制的,遵循的是“紅皮書”的CDDA 規則;目前,新型的錄音母版制作已利用高分辨率的PCM文件或者DXD、DSD等文件格式,摒棄CDDA的規格,采用全新的載體和格式完成。各種信號處理手段的進步,也為母版保留更好的音質創造了條件。1995年,美國RR 公司推出一種高清兼容數字的HDCD 信號處理方法,通過使用自定義抖動、音頻濾波器和一些可逆的幅度與增益編碼,對16位的音頻信號進行等同于20位的編碼。該技術已經提供了超過CDDA 的動態范圍,音質大有提升。同年,日本JVC 公司又發明了一種特殊CD 母版制作工藝XRCD,可實現CD 分辨率的擴展。1998 年,該公司又推出XRCD2,改用磁光盤(MO DISC)來存儲K2 數字轉換器輸出的20 位音頻信號作為制作CD的母版,進步更為明顯。該公司并未止步,2003年推出了擁有24 位量化精度的XRCD24,至2007 年又發布了K2HD,其頻帶居然寬達100kHz。
(三)錄音技術從模擬到數字
模擬錄音通過傳聲器把聲音信號轉變為電信號,并通過放大器傳送到錄音磁頭。交變的電信號流過磁頭的線圈,讓磁頭前產生磁場,從而使磁帶上的磁粉發生感應變化,以磁能的方式把聲音信息儲存起來。但是,磁頭的磁場強度與磁帶的感應程度之間并不是線性關系:只有振幅適宜的信號才能很好地被記錄在磁帶上,較高的電平信號就容易使錄音失真。誠然,模擬錄音技術有很多優點,但它在再現性所要求的一些細節上無法實現技術突破,除高電平失真外,信噪比也欠佳。這即便對于表現性的音樂在錄音藝術上的追求來說,也是一種明顯的限制。
反觀數字錄音技術,其采樣頻率越高、量化精度越高,記錄下來的振動曲線就與原始信號越接近。在前文所述的高采樣頻率和高量化精度下,音樂錄音的再現性已經極大增強,賦予許多人以身臨其境般的音樂真實感和聲響細節。當然,數字錄音技術對聲音高保真的支持,亦可以對表現性的音樂錄制產生良好的推動作用。
二、兩類音樂錄音活動的實踐案例和特點分析
由于筆者的錄音實踐通常是為各種規模的樂隊進行的,本文也僅以樂隊錄音案例為切入點,分別對當前的再現性音樂錄音和表現性音樂錄音的特點做一簡要分析。
(一)再現性音樂錄音案例和特點
筆者從事過2017 年6 月在北京音樂廳舉辦的“龍聲華韻——陳培勛作品專場”的錄音工作,這是再現性古典音樂錄音的典型案例。
在話筒總體設置方面,該場錄音采用AB 制式加側展的方式——中國交響樂團人數較多、樂團座席區較寬大,所以利用側展話筒拾取左右部分的聲音可以實現更強的聲像整體感和聲音包容感。在舞臺上,除主話筒(2只,全指向)和側展話筒外,還有15 只心型指向的“點話筒”負責拾取多個樂器聲部的細節(亦包括鋼琴和豎琴,但一些本身音量很大的打擊樂未單設),另又在觀眾席的中間區域設置2只拾取觀眾效果的話筒。
在前期錄制時,LL、RR 的聲像分別設置到了左、右兩個極限,各種樂器則根據舞臺上的擺位簡單地做了聲像分布和平衡。彩排時,筆者還根據監聽的情況及時調整了部分話筒的擺位和高度。這些做法為后期加工節省了時間,也有利于聲音還原的真實度和自然感。
根據理論知識和實踐案例,筆者對再現性音樂錄音的特點有這樣幾項概括:聲音效果調整和音色變化幾乎沒有痕跡;樂隊整體平衡;樂器趨向于傳統品種;有良好的聲學環境中的自然混響;樂隊座席和主話筒在縱深上平衡。
再現性音樂錄音多用于古典音樂,聲學條件一般為音樂廳和歌劇院等專門演出場所。由于后期沒有很多“奇怪”的音色,即使需要進行均衡(EQ)調整,也不會因為要突出某個頻段而犧牲樂器本身的聲音特性。但是,再現性音樂錄音活動也不是純粹“順其自然”即可,它仍然需要人工雕琢。畢竟,觀眾在現場欣賞音樂會時除了聽覺感受,還受到視覺、觸覺甚至具體觀賞位置的多重影響,但就音樂錄音作品而言,聽覺感受之重要性幾乎等于全部。這就要求這種音樂錄音現場須盡量避免細節紕漏和瑕疵——縱然任何再現性音樂錄音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實還原。同時,錄音師可以依據自己的審美判斷,利用強大的后期技術手段,模仿甚至稍微美化出所謂的臨場感和自然感,從而爭取到欣賞者的共鳴。
(二)表現性音樂錄音案例和特點
與再現性音樂錄音相比,表現性音樂錄音更具革新性和創意性。筆者在此僅以自己2018 年6 月錄制的歌曲《Gold and Rum》為例,其樂隊編制是一套完整的架子鼓、主音吉他、電貝斯,以及主唱。錄音棚位于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臺三層,其混響時間較短,音色感也較為“干燥”。錄制時,架子鼓、主要人聲、貝斯的錄制是在錄音棚的錄音間內先后完成的,而伴奏人聲、主音吉他、伴奏吉他則在控制室內先后完成,吉他聲音一律走線。為確保質量,筆者還對架子鼓的多個組件進行了分別拾音,比如2 只動圈話筒分別用于底鼓的外側和內側,多只電容話筒拾取軍鼓和通鼓等。
另外,由于該樂隊特重獨立的創造性,曲目都是完全的原創作品,所以在錄音和混音任務中有些很獨特的元素,比如樂器多被改裝,連接了失真模塊和效果器,曲式也十分具有表現性等。
作為一首具有強表現性的流行音樂,《Gold and Rum》不僅在前期分軌錄音的時候要注意信號的還原和真實度(以便顧及音源本身的失真音色、大量的模擬效果器的表現性),還有必要在后期打破古典音樂錄音實踐中那種“美”和“再現真實感”的定義。表現性音樂和再現性音樂最大的表面差別,可以說是在原樂器音色的還原度上。如果說再現性音樂更加注重自然感和空間感,那么表現型音樂所追求的就是對傳統音色觀的突破和對音樂可能性的不斷開創和挖掘。筆者在這首作品的后期混音之中,對鼓組的單件樂器、電貝斯、主音吉他、節奏吉他乃至人聲,都進行了均衡、壓縮和特殊效果處理。
對于人聲,為了做出樂手所要求的表現性,筆者在500Hz 左右提升了大約5dB,并做了低切。對于這首歌里大量的合唱樂段,出于樂手時間安排考慮,多軌錄音時每次只錄一位樂手。為了合成合唱的效果,筆者加入了Doubler 4 的模擬合唱效果器,把聲音展寬為兩個信號,再平衡到主唱樂手身后,營造出三個人同時錄音的假象,順應了該音樂的表現動機。
對于節奏吉他,鑒于前期多軌拾取到的失真音色和其他樂器融合得不是很好,筆者后期為其串入了人工的失真效果器。除真實音色的變化外,筆者還加入了double,營造出“乒乓效應”,使節奏吉他在結尾時拉長延音,增添了其表現性。此外,這里還做了大量的壓縮和效果器的調整串聯。可以說,這些不斷變化的音色、密密麻麻的節奏型等,都是對音樂的表現性的強調,以圖對音樂有新的詮釋,與再現性音樂的錄音方式迥然不同。一般來說,表現性音樂錄音都會做更多的音效調整,不僅涉及樂器,還涉及人聲,其樂器種類一般也比再現風格的音樂更多。
通過實驗可以看出,雖然再現性錄音方式的作品更為“經典”,為很多聽者所欣賞,但錄音師在合適的條件下發揮主觀能動性,將自己的意識和作者的創作理念融入錄音制品,實現表現性錄音,更有生動新穎之趣。再現性音樂錄音作為音樂錄音的基礎,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表現性音樂基于再現性錄音的基礎,以全新的形式和面貌詮釋了音樂錄音的新意義。在表現性音樂錄音中,錄音師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音樂藝術的創作,利用一些音樂中的“藝術虛構”,平衡虛與實的關系,豐富聽者的體驗和音樂的審美情趣。
三、數字錄音技術對兩類音樂錄音活動的影響
在信號的錄入處理方面,數字錄音技術有著比模擬錄音技術更高的清晰度和保真度,為音樂錄音的品質保證奠定了技術基礎。愛迪生在圓筒留聲機上的錄音,聲響是極度微弱的;進入20 世紀20 年代電聲錄音時代后,技術上雖有所進步,但是RCA 發行的主流唱片也只能記錄不到5 分鐘的聲音信號,超過5 分鐘的音樂就要被分割或者刪減,大大影響了音樂的連續性。而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錄音的信號可以直接進入音頻工作站后,音樂錄音的時間上限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磁帶錄音時代,錄音機一般最多8 軌一組,但如今的工作站記錄256 軌也并非極限。分軌錄音對再現性音樂錄音是一項重要的技術支持,它可以讓前期錄音把每一件樂器的局部細節通過多補的一個“點話筒”作為一軌記錄下來,而這些細節的錄制讓再現性音樂有了更寬廣的調整空間,由此又增強了再現性音樂的真實度。
同時,數字錄音技術對表現性音樂的后期混音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它讓音樂作品在美學上的特殊追求更加容易實現。表現性音樂可以在數字音頻工作站上進行豐富的音色變換、動態處理,更加方便錄音者傳達對作品的理解;工作站在此為發揮錄音者的主觀創造性提供了充足的技術支持。應該說,數字錄音技術對表現性音樂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流行音樂的表現通常來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因此它所表現的除了聲學環境和樂譜的客觀性以外,更多的是主觀性創造和想象力,而這些后期的人為聲音效果離不開相應的技術的支持。當然,表現性音樂也不會全然脫離實際,其表現性是和再現性對立統一的。音樂錄音過程中,錄音師對音樂的表現即使有自己的創意,也必須依據錄制完成的聲音信號的客觀情況進行加工處理,但是,錄音手法上的突破創新歸結到底也離不開數字錄音技術的助力。
再現性錄音和表現性錄音作為音樂錄音藝術概念的兩大分支,都為音樂產品的不斷問世發揮著巨大的能量。而數字錄音技術的日新月異,為追求更高的音質和更新奇的審美體驗都奠定了技術基礎。音樂錄音作為聽覺藝術上的一環,對提高人的審美素養乃至綜合素養都起著積極作用;技術的發展,則使得這種積極作用在具體實現方式上的突破和創新不斷獲得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