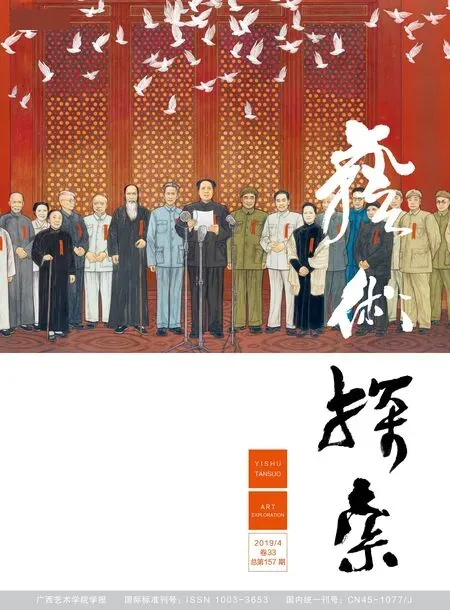城市化進程中民間音樂的保護策略研究
樂之樂
(吉首大學 音樂舞蹈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進入21世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鎮,城市化成為繼工業化、現代化、信息化之后的又一全球性潮流。而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我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文化的根基、各族人民創造的珍貴遺產——民間音樂,其依附的文化生境也發生變化,它又將何去何從?
一、城市化給民間音樂帶來的影響
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業發展成為其初始動力,工業化成為其根本動力,市場化成為其直接動力。機械逐漸取代手工,工業生產打破以往農村自然經濟桎梏,大批農民工涌入城市,勞動力不斷向城市遷移,土地資源市場化,產品市場化。這使民間音樂依附的文化生境發生改變,并不可避免地遭遇城市化的種種侵蝕,面臨尷尬境遇。
(一)生存環境變化,導致民間音樂消失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原本以手工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逐漸被一臺臺機器取代,民間音樂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都發生了變化。農民不再面朝黃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婦人不再每日每夜地描龍繡鳳;漁夫不用日夜兼程地劃船、撒網、捕魚;工人不用靠雙手打石蓋房、上梁架橋。我們再也聽不見田間勞作時的插秧歌、薅草鑼鼓,聽不見漁民撐船、放排、捕魚時所唱的船工號子、搖櫓號子、放排號子、打漁歌,也聽不見工人修房蓋屋時所唱的打夯號子、上梁號子、立扇號子,等等,它們已消失在隆隆的機器聲中……
(二)方言淡化,導致民間音樂失語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1]31,是人類文明的象征。中國有56個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為了增進交流,維護祖國統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四條規定:“公民有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權利。國家為公民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提供條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推廣普通話和推行規范漢字”[2]30。普通話推廣力度的不斷加強,也加速了方言的消亡。那夾雜著方言的一首首歌謠、一段段戲曲,也隨之遠去而失聲……
(三)人口流失,導致民間音樂失傳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及多元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間音樂的消亡。電視機、手機、電腦、洗衣機、電冰箱等進入千家萬戶,鄉村的夜晚不再是唱曲、對歌、講古,而到處播放著港臺歌手的搖滾音樂會、肥皂泡沫劇、綜藝節目。民間音樂失去了觀眾,更失去了傳人,傳承岌岌可危。正如樊祖蔭所說:“任何文化的傳承,都由‘傳’和‘承’(即傳承人與被傳承人)雙方互動構成。如果只有傳遞而無人承接,那么,再好的文化也是無法傳承下去的。”[3]8筆者在湖南省張家界桑植縣馬合口、五道水、官地坪等地調查桑植民歌時發現,60歲的老人大部分還會唱一些桑植民歌,45歲以上的僅個別人會唱,而年輕人和小孩(沒有上學的)幾乎很少有人會唱。
(四)民俗改變,導致民間音樂匿跡
民俗文化是滋養傳統音樂的土壤,任何民間音樂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和民風民俗。民間音樂伴生于各種民俗文化事項,如湘西的哭嫁歌、婚禮歌、祭祀歌、打溜子等都與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婚喪習俗同在。在城市生活和新事物的沖擊下,外來文化與原生文化不斷發生碰撞,一些伴生于民俗的音樂品種不斷創新發展,得以繼續存活,如被譽為“中國式的詠嘆調”的土家族哭嫁歌,隨著年輕人婚俗觀念的轉變,逐漸變成各大旅游景點實景演出中的展演項目,但多數民間音樂品種則隨著民俗活動的消失而瀕臨匿跡,如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完好保留土家族語言的只有龍山縣坡腳鎮,這里還保留著純正的土家族母語民歌,而在其他土家族聚居地這些民歌則已不復存在了。
二、當前保護措施及反思
民間音樂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積淀,以及多樣的種類和豐富的內涵,與各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在城市化推進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其也在迅速變化,因此全國上下紛紛實施保護和搶救。這些措施是否有效阻止了民間音樂的消亡,民間音樂在城市化進程中是否得到了創新和發展呢?
我國當前的保護措施,歸納起來有三個層面。
(一)政府層面
我國政府一直重視民間音樂的傳承與保護,設立各種機構對其進行有序保護。1998年,文化部經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準設立“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旨在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挖掘和搶救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促進民族民間文化的交流與發展。隨著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引起廣泛關注。2006年,經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準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掛牌成立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承擔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各項工作,有效促進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另外,在政府的倡導下,我國還設立了大量的研究和保護機構,如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民族音樂文化產業研究委員會等,各省市也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等機構,對我國民族民間文化開展搜集、整理、挖掘、保護、研究、傳播、推廣、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并取得豐碩成果。
同時,國家還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出臺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以便更好地維護機制管理,實施各種保護策略。如2003年11月,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組織起草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該草案主要涉及繼承人保護、文化遺產保護及相關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三個方面的內容。2011年,文化部、財政部下發《關于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通知》,進一步加強民族民間文化保護,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
這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為我國民間音樂的傳承和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使其生存環境得到了改善,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為例,由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和政府各部門的不斷宣傳,各單位開始大量申報“非遺”項目,但很多項目存在重合或交叉。如“土家族撒葉兒嗬”于2006年5月被錄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這一藝術形式在湖南省張家界市桑植縣和湖北省都頗為流行,之后兩地便都有了這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牌匾。“土家族打溜子”也一樣,2006年由湖南省申報后被錄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由于它的流傳范圍不限于湖南,在名錄條目介紹中“湖北省土家族打溜子”被列為“土家族打溜子”的擴展項目。鑒于民間音樂分布區域廣、門類品種多、特性鮮明等特征,加之各地對其保護力度不一,效果和影響也各不相同。
(二)學者層面
在學術界,相關的專家、學者紛紛奔走呼吁,各學術組織紛紛召開專門的學術會議,組織考察活動,對民間音樂的傳承和保護建言獻策。如1986年5月,全國政協文化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在人民大會堂共同召開保護民間文化座談會,就如何搶救、保存和保護民間文化進行討論,提出尊重、保護各民族民間文化的締造者和傳承者,包括民間歌手、民間藝人等,提升他們的地位,給予他們相應的榮譽。
另外,還有2003年召開的“中國少數民族藝術遺產保護及當代藝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召開的“‘文化多樣性與當代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召開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召開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與實踐論壇”“中國藝術人類學論壇暨國際學術會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藝術人類學研究”,等等,對民間音樂及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提出了有利的保護對策和措施。在中國知網,以“民間音樂”為關鍵詞,檢索到期刊、學位論文5 000余篇。學者們從不同學科出發對其進行學理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民間音樂的傳承與保護、藝術特征、開發應用、創新發展等方面。雖成績卓越,但民間音樂品種各異,藝術特征不盡相同,因此他們提出的傳承和保護措施并不具有普適性,在實施中也面臨一定的問題,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民間音樂的傳承和保護。
(三)民間層面
民間層面,在以民間音樂為元素的賽事、民歌節、節目、展演活動等爭相怒放的同時,各地民間藝人對自己的技藝也有了充分的認識,并積極地參與傳承和保護工作。自2002年起,在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先后籌備舉辦了2002年浙江仙居、2004年山西左權、2005年北京宋莊的“全國南北民歌擂臺賽”,將原生態民歌搬上舞臺展演和競賽。隨后,在北京也舉辦過多次以“原生態”命名的演唱會。2006年,第十二屆中央電視臺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首次增設了“原生態”唱法。2007年12月,由文化部主辦的“中國原生民歌大賽”在陜西西安舉行。此外,廣西、湖南桑植等地舉辦一年一度的“民歌節”,中央電視臺以及各地方電視臺推出《中國民歌大會》《遠方的家》《民歌中國》《中國民歌知多少》《放歌中國》《中華情》《民歌戲曲聯唱》《天天向上》《歌從黃河來》等節目。越來越多的民間音樂被搬上舞臺到城市展演,如桂林的《印象·劉三姐》,云南的《云南映象》,張家界的《魅力湘西》《天門狐仙》,鳳凰的《天下鳳凰》,等等,它們都融入了大量的民間音樂元素,將各地的風土人情、信仰習俗,通過音樂、舞蹈、戲曲等形式進行呈現,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這無疑促進了民間音樂的傳承和保護,弘揚了我國傳統音樂文化。
但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人口不斷向城市遷徙和集結,旅游業發展持續高漲,這些措施和策略依然存在弊端。經過媒體的報導、宣傳和推廣,民間音樂展演形成經濟效應,大大促進了民間音樂的傳承,但同時也歪曲了它的傳承。一些商家為了經濟利益,將一些民間音樂植入與之無關的展演中,導致人們對民間音樂產生錯誤的認識;一些藝人為了經濟利益進入演藝行列,導致原本樸實、原生的民間音樂為了某種效應而進行展示,失去了其原本的價值和意義,成為一種打趣逗樂的藝術形式。因此,筆者認為應該正確地引導民間音樂的傳承和創新發展。
三、建議實施的保護策略
對于民間音樂的傳承與保護,我們必須實現靜態與活態相結合的策略。在靜態保護方面,應及時申報項目名錄,完善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體系及保護機制;制定相關保護法規和保護細則;劃定設置文化生態保護區,將民族民間傳統音樂文化遺產原狀保存在其所屬的區域及環境中,使之成為“活文化”。在活態保護方面,主要是有效利用傳統音樂,實現保護的最大價值和文化自覺保護等,以適應不同環境的文化生態,形成一個相互聯結的體系網絡,以達到保護的最佳效果。
(一)有效利用傳統音樂,實現保護最大價值
在社會轉型期,商品經濟和大眾傳媒熱浪的沖擊給民間音樂帶來了生存的危機,也為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新的發展契機。民間音樂在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城市化進程中,不斷探索、尋求新的發展路徑,才能躋身城市音樂中,實現價值的最大化,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市場化是城市化發展的直接動力,而市場化主要體現于商品的價值。使民間音樂脫離鄉土社會而融入城市化進程,必須找到民間音樂與市場的契合點,探索其強大的經濟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等。因此,大量的民間音樂與文化創意產業聯姻,不僅實現自身價值,還得以廣泛推介和傳播,并給予創意產業源源不斷的素材和資源,為其提供新的發展商機,促使其開拓更廣大的文化市場。
1.與動畫產業結合。民間音樂與動畫產業的結合,為少兒提供音樂文化啟蒙教育,培養兒童樸素的人生觀念和傳統文化的自信力,為其日后的傳統音樂文化教育打下堅實基礎。如1956年,由后來擔任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廠長的特偉執導的國產動畫片《驕傲的將軍》,大膽在將軍造型中運用京劇臉譜元素,片中人物動作的設計也采用京劇程式化的表演動作,人物的舉手投足無不展現出我國民間音樂文化的氣息。著名音樂人陳歌辛還巧妙地將經典琵琶曲《十面埋伏》融入片中,生動展現出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將軍深陷敵軍重圍無力反抗、倉皇而逃的悔恨與彷徨。我國第一部水墨動畫片《小蝌蚪找媽媽》、吳應炬制作的《牧童》、萬籟鳴導演制作的《大鬧天宮》、我國第一部彩色動畫片《哪吒鬧海》,以及《寶蓮燈》《梁山伯與祝英臺》等,都大量使用了古琴、琵琶、揚琴、笛子、古箏等民間器樂配樂,并融入古代繪畫、皮影、民間年畫,以及京劇【流水】【快三板】等節奏板式,大量運用民間音樂如《春江花月夜》《梁祝》等作為配樂,使民間音樂得以不斷創新發展。
2.與影視產業結合。借助影視作品的動態演述,民間音樂可有效提高全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音樂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和文化價值的認識,增強人們的民族文化認同感,推動人人尊重民間音樂,人人愛護、維護民族音樂文化遺產的局面,促進文化生態保護工作,達到整體性保護的最終目的。同時,影視吸收傳統音樂精華,也使民間音樂在影視作品中得到深化。電影《百鳥朝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講述了陜西無雙村焦家班嗩吶傳承的故事,也反映了我國傳統的禮俗制度。經典嗩吶曲《百鳥朝鳳》在劇中不斷回旋,使人們觀影時對民間音樂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3.與旅游產業結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伴生于民俗的民間音樂成了旅游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有效地利用到旅游文化的打造中去。打造文化精品,一度成為充實和豐富旅游資源內涵及構建特色性旅游文化的示范。這不僅給文化持有人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也為民間音樂的活態保護提供了借鑒。如湘西旅游圣地德夯國際苗鼓節、張藝謀創意的桂林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張家界的《天門狐仙》等,就是民間音樂與旅游產業成功結合的典范,有效傳承、發展了民間音樂。
4.與社區群眾文化結合。城市化的推進使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定居城市,成為社區中的一員,社區成為城市中又一個人口集散地,而社區群眾文化成為成員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社會習俗等文化事項的總和。20世紀末,我國社區群眾文化建設成為國家、政府職能部門及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全國性社區群眾文化建設不斷升溫。作為社區成員的農村人口依托社區文化搭建傳承鄉土文化和民間音樂的平臺,有利于我國民間音樂在城市中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也有利于社區群眾文化建設,及加速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如湖南省吉首市的廣場舞活動,其場所不再限于廣場,而逐漸延伸到各個小區,只要有足夠的空間,就是眾人起舞的地方,其音樂也不再是流行的《最炫民族風》《小蘋果》等,而是融入了具有土家族、苗族、白族、漢族等民族特色的民間音樂,如《請到我們湘西來》《矮寨飛龍》《我在湘西等你》《織女謠》等,同時融入仗鼓舞、打苗鼓、耍花棍等藝術形式。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間音樂成為社區成員進行文化交流和展演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農村人口融入城市文化的又一個渠道。
(二)劃定文化生態區域,建立傳統文化村落
“文化生態學”是1955年斯圖爾德提出來的,他認為:“文化與其生態環境不可分離,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互為因果”。[4]8劃定文化生態保護區域,建立活態保護村落,既可以保護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又可促進城市化進程,為城市化增添新的元素。根據區域文化特點,選定在生產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群聚居空間給予完整保護和特別關注,使這一特定區域的傳統音樂文化得到有效發展和健康傳承。如1999年12月9日,中國與挪威合作建立的貴州黎平縣肇興鄉堂安寨的侗族村落,就是中國唯一一座侗族生態“博物館”。這座村寨保持著原汁原味、古樸濃郁的侗族風情,這里的鼓樓、戲臺、吊腳樓、侗族大歌、侗族樂器及侗族服飾等有著原生態的風味,成為侗鄉的“活文化”,有力地保護了侗族民眾的音樂文化。簡言之,劃定文化生態保護區,構建活態保護村落,將民間音樂活態地保存在其所屬的區域及環境中,使之成為“活文化”,是活態保護傳統音樂行之有效的舉措和有效辦法。
(三)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完善傳承保護機制
對于以口頭方式進行傳承的具有口傳性、即興性、流變性的民間音樂,一方面國家和地方政府的保護舉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其本身卻隨著文化生境的改變而瀕臨滅絕。因此在城市化推進的過程中,我們應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完善傳承保護機制,生產性、活態性、整體性、綜合性地實施保護策略。
韓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尤其重視對傳承人的認定和培養。其《文化財保護法》明確規定,重要無形文化財持有者或持有團體除可獲得必要的生活補貼外,如將自己的技藝或藝能傳授給他人,還可獲得“重要無形文化財持有者”榮譽稱號。文化財廳長有權為他們配備助教,他們還可獲得每月每人30萬韓元的政府補貼。為了確保重要無形文化財的傳承,韓國政府還特設獎學金,以鼓勵和資助那些致力于學習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年輕人,并對學生的選拔條件、年齡要求、學習期限等都做了相應規定,有一整套嚴格的獎懲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的先進制度和措施頗有成效,我們不妨依照我國國情制訂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如:建立完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機制,解決傳承中的實際問題,使傳承人有的放矢、毫無顧忌地做好傳承工作;建立活態保護場所,有效實施活態整體保護;建立完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對傳承人、非遺項目等建檔立戶;建立一套適應城市化進程的民間音樂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措施;等等。
(四)發揮民眾主體作用,形成文化自覺行為
“文化自覺”是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在反思自身學術生涯時提出的,意為生活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明曉其文化的來龍去脈,應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的目的在于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因此,認知、理解和詮釋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聯系現實,尊重并吸納他文化的經驗和長處,與他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語境,達到文化與文化之間、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文化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契合運行,從而構建人與文化、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文化空間,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自覺”。在國家的大力宣傳和政府各職能部門的倡導下,我國民間音樂的傳承與保護工作成效顯著,如《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的編撰,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實施,等等。我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不斷提升,文化自覺不斷凸顯,民間音樂不斷受到重視。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民間音樂得到每一位中華民族成員自覺的傳承和保護。例如,桑植縣委、縣政府堅持政企合作,依托“紅色文化、綠色家園”特點,從市場著眼,從娃娃抓起,搭建教育傳承平臺,組織宣傳部和非遺辦等相關部門的專業人士,將桑植民歌中的經典曲目選編進學校的校本教材,推行“人人會唱桑植民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等活動。
在一體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時代,“文化自覺”勢在必行。完全依靠外力是不可能持續保護好民間音樂文化的,人民是傳統音樂保護的主人,只有積極發揮人的主體地位、人的能動作用、人的創造力,才能更好地實現民間音樂文化的生態保護。政府正確主導,社會共同參與,各方協力配合,才能建立起科學而有效的傳承和保護機制,從而達到自然與文化的相互適應和依存,形成文化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契合運行,實現全民族、全社會的文化自覺保護。
在城市化推進中,民間音樂既隨著文化生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甚至消亡,又遇到新的發展機遇,在經歷探索、創新、蛻變、發展等過程后,正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行。我們相信,在城市化進程中,民間音樂必將遭遇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對此我們應正確看待,并結合實際,找到最佳解決方案,使其得到有效、合理的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