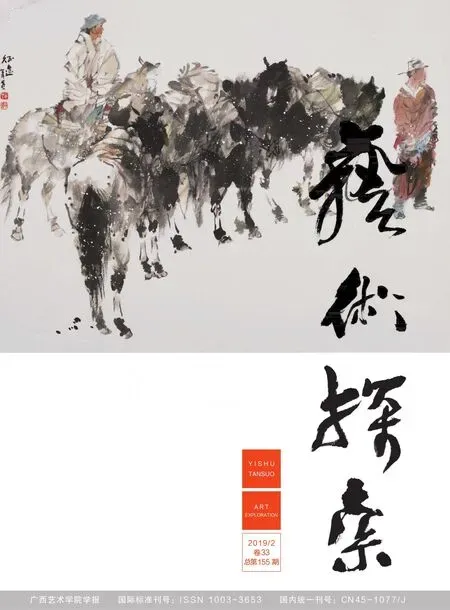二十四史“藝術列傳”的概念及其內涵變遷
李倍雷
(東南大學 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在二十四史中,從《史記》的《龜策列傳》到《晉書》的《藝術列傳》的演變,這期間經歷了從概念到內涵的重要變遷。其中《漢書》的《方技列傳》到《后漢書》“藝術”概念的出現,再到《魏書》的《術藝列傳》的出現都是很重要的變遷過程,由此才有《晉書》《周書》《隋書》《北史》的“藝術列傳”。這整個過程展示著“藝術”概念的演變及其內涵的變遷,演繹了中國古代藝術自身確立、演進與發展的路徑,昭示著中國古代為“藝術”立“傳”的安身立命的文化性格。我們今天對二十四史“藝術列傳”等一系列現象與內涵的爬梳,目的在于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史境”中為當今藝術尋求源頭和立心之本,同時與西方的“Art”的對話、交流提供一個話語空間,并為二者的相互比較提供一種可操作性的語境。畢竟中國的“藝術”與西方的“Art”所有不同,當今我們在使用“藝術”的概念時應該清楚不完全是“Art”的同義語,二者從詞性、語義到內涵都各有自己的“能指”與“所指”。因而,我們爬梳二十四史“藝術列傳”以及傳統文化史境的“藝術”概念,在于為我們今天建構中國的藝術理論立心,為建構中國的藝術理論話語體系立命。
一 、《史記·龜策列傳》到《后漢書·方技列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正是為“龜策”立傳。唐人司馬貞(679~732年) 索隱云:“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陋略,無可取。”[1]2441唐人張守節(生卒年不詳)正義云:“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候、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1]2441這里說明一個問題,“龜策”用來占卜兇吉在《史記》前就有了記錄,但并沒有被編入正史的“傳史”中,此時人們對“龜策”一類活動持否定態度。唐人劉知幾(661~721年)《史通》對這個問題有所分析:“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2]34因此,可以看出將“龜策”編入《史記》,以此為“列傳”也并非司馬遷的本意。“龜策”古時用于占卜兇吉,是人類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活動,《禮記·曲禮上》:“龜為卜,筴為筮”[3]31。筴同策。即古代卜用龜甲,筮用蓍草。“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1]2441《史記·太史公自序》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兇,略窺其要,故作龜策列傳。”[1]2506我們探討二十四史“藝術列傳”的變遷卻“扯”到“龜策”這個問題上來,是因為“藝術列傳”與“龜策”有很大的關聯。《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1]2487將“六藝”作為儒者立本之法,“龜策”乃古代玄之又玄的技術,而“六藝”與方技中的“龜策”有關。
《漢書·藝文志》始有“六藝”。其云:“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4]1351顏師古注:“六藝,六經也。”六經者即儒家經典《易》《詩》《禮》《樂》《春秋》《書》。值得注意的是,《藝文志》中把《術數略》和《方技略》合并在一起為志。“術數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有梓慎,鄭有裨灶,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粗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4]1935所謂“術數六種”也就是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漢書·藝文志》把《史記》中的《龜策列傳》的內容納入《術數略》中為“蓍龜”一類——《龜書》《夏龜》《南龜書》《巨龜》《雜龜》《蓍書》等,“蓍龜者,圣人之所用也”[4]1392。同時《漢書·藝文志》還涉及到“醫經”。“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4]1395有意思的是,“方技”實則也有講醫術的內容。“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4]1398所謂“四種”指的就是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可以看到“術數”與“方技”有交叉。另外,還有類似于“鬼策”的“雜占”,“雜占者,記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征。”[4]1393另還有《兵書略》涉及到各種強弩“射法”,實為“禮、樂、射、御、書、數”中的“射”。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于明靈之府,封縢于瑤壇之上者,靡得而窺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乃望云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圣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1825
也就是說《后漢書·方術列傳》將那些用于“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者”的天文地理知識及其技術,以專門人才來掌握。不僅如此,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的是《方術列傳》實際是在“日者”“龜策”的基礎上演變而來并增加了“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挺專、須臾、孤虛”等術數的內容,這為后來《魏書》的《術藝列傳》奠定了基礎,也由此為二十四史“藝術”立傳提供了條件。當然,完成“藝術列傳”之前首先有一個關于“藝術”概念的演變過程,即從“方術”到“術藝”最終到“藝術”定型,并由此為“藝術”立“傳”。
二、從“方術”“術藝”到“藝術”概念的形成
《莊子·天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6]864唐人成玄英(608~669年)疏:“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其情,順其所為之性。”[6]864“方術”概念最早應該出現在《莊子》的著述里。有意思的是,成玄英疏用了“藝術”這個概念來闡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中的“方術”。《晉書》《周書》《隋書》《北史》都是在唐代重修的過程中,專門使用“藝術”這個概念立傳編入史書,足見唐代使用“藝術”這個概念非常普遍。成玄英用“藝術”這個概念與“藝術列傳”的內涵基本上是一致的,指的是技術、才能等。“治道藝術”就是治道的技術。當然,“藝術”這個概念最早是《后漢書》提出的。《后漢書》為南朝宋史學家范曄(398~445年)所著,故“藝術”這一概念出現在南朝宋時期,廣泛興盛并定型于唐代。
《后漢書》首次將“藝”與“術”二字合并使用為“藝術”,這是中國古籍文獻中第一次出現“藝術”這個概念。“藝術”概念的出現,為以后的“藝術列傳”在概念上確立了基礎。《后漢書》有兩處用到“藝術”這個概念。
首先,《后漢書·安帝紀》:“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5]145章懷太子李賢注云:“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前書曰:‘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李賢沒有明確地提到對“藝術”的解釋,當然我們應該看到《后漢書·安帝紀》這里將“藝術”與五經、諸子、傳記等并列,這個并列意義非同一般,它意味著“藝術”獨立于其他類別。
其次是《后漢書·伏湛傳》再次提到“藝術”的概念,其云:“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如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李賢注:“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5]600這里李賢除了同前注“百家”外,還特別對“藝”“術”二字分別作了注釋,這種注釋的方式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信息,“藝術”二字是并列關系,非偏正詞組,二者各有其所屬的內容,這為《魏書》的“術藝列傳”的“術藝”概念前后并置提供了合理的邏輯基礎。與此同時,我們尤其要注意李賢對《伏湛傳》中“藝術”的注釋,這一闡釋實際上是對后面“藝術列傳”內容及其涵義作了最明確的注解與圈定,也為二十四史中的“藝術列傳”提供了條件和理論基礎。
李賢所注“藝術”內涵的文化邏輯基礎是承接了儒家傳統主體文化路徑,或者說他是將“藝術”這個概念置于漢代“獨尊儒術”的史境中進行注釋的。且說《后漢書》是南朝宋時范曄所著,他是以《東觀漢記》(東漢班固、陳宗等)為底本并參照其他各家所著《后漢記》(晉薛瑩)、《續漢書》(晉司馬彪)、《后漢書》(三國吳謝承)、《后漢書》(晉華嶠)、《后漢南記》(晉張瑩)等完成的《后漢書》,在文化態度和體例上與班固《漢書》保持漢代“獨尊儒術”一致。李賢所注“藝術”概念與《后漢書》“藝術”概念的內涵存在有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一致性。因此,“藝謂書、數、射、御”與《周禮》的“六藝”保持高度統一。《周禮·保氏》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7]499唐人顏師古注《漢書》將《藝文志》《儒林傳》《韋賢傳》等篇中的“六藝”解釋為“六藝,六經也。”盡管二者也有不同的地方,但“六藝”與“六經”之間肯定有非常緊密的關聯,因而“書、數、射、御”是納入“藝”的范疇。再看李賢注“術”所指的是“醫、方、卜、筮”,這仍是前面說的“方技”的范疇。李賢對“藝術”的注釋,為我們從“方技”的概念變遷為“藝術”的概念找到一個很好答案,同時也為“術藝”變遷為“藝術”找到一條最佳線索。
李賢對“藝”“術”進行的分別注釋,說明了這兩個字是并列關系,分指不同的內容或領域。《魏書》用“術藝”這個概念編入列傳,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了。“藝”與“術”二字前后置換不影響它們各自的內涵。許慎《說文解字》對“藝”“術”分別有詞義上的解釋。《說文·丮部》云:“埶,種也。從丮坴。丮持種之。”段玉裁注:“齊風毛傳曰,蓺猶樹也。樹種意同。”[8]113又《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段玉裁注:“邑國也。引申為技術。”[8]78從《說文》的解釋以及對《說文》的注解來看,兩者都與技術有關。“藝”的技術比較明確,就是種植;“術”引申為技術。這也就不難理解《魏書》為何設《術藝列傳》。那么,我們看看《術藝列傳》包含的那些內容。《魏書·術藝列傳》小序云:“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圣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廣聞見也。”[9]1943這應該是《魏書·術藝列傳》對“術藝”的范圍選定。首先《魏書·術藝列傳》認定“術藝”是“小道”,而“小道必有可觀”的出處為《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那么“小道”究竟是什么呢?接著下面子夏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10]200顯然,子夏說的“小道”就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技術。這句話來自《考工記》。其云: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11]2-8
當然,《魏書·術藝列傳》包括的內容遠遠超過了《考工記》所說的“百工”內容,還有卜筮、占候等技術,并且這些都是“往圣標歷數之術”,故列于篇流傳于世。我們還要注意的是李賢所注釋“藝術”實際上分了兩個不同層面并隱含了層次的高低。“藝”包含的是“書、數、射、御”,前面我們提到這部分與《周禮》有關系,實際上也是儒家文化教育體系中要求掌握的必不可少的內容;“術”則包括的是“醫、方、卜、筮”,實際是“方技”的內容,雖然不被納入形而上的儒家文化體系中,但從圣王到庶民都離不開這些技術,前面我們引用了《魏書·術藝列傳》小序所說的“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同樣前面我們也引用了《后漢書·方術列傳》開篇所說:“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矣”,都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往圣先王對“術”也是很重視的。
從《魏書·術藝列傳》可以看出,“術藝”既包括了“書、數、射、御”的內容,也包含了“醫、方、卜、筮”的內容。也就是說,“書、數、射、御”和“醫、方、卜、筮”這兩大部分構成了“術藝”或“藝術”的全部內容。《魏書·術藝列傳》最后的總括把“術”與“藝”二者的關系闡釋得非常清楚: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于是者不能無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伎巧而必蹈于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9]1972
《魏書·術藝列傳》從“詩書禮樂”與“方術伎巧”兩個維度指出以往的得失,認為“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伎巧而必蹈于禮者,幾于大雅君子。”并列舉了“術藝”之士如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他們的能力主要是“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還有醫術高妙者如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等人,也贏得一時美名。唯有蔣少游雖有一些雕蟲小技,卻埋沒了學思,技藝是有了,但地位低下。從《魏書·術藝列傳》對蔣少游的批評而對其他多數人的褒揚,可以看到“方技列傳”向“術藝列傳”變遷的一個內在邏輯,這個邏輯體現了從單純的“技巧”向具有“學思”技術層面的“術藝”邁進。
三、從“術藝列傳”到“藝術列傳”
《魏書·術藝列傳》到《晉書·藝術列傳》同樣也體現了一個內涵邏輯演進。盡管我們前面認為“術藝”與“藝術”的前后置換是行得通的,“藝”與“術”是兩個并列關系的語詞。但是二十四史中《魏書》與《晉書》在立傳時這種微妙調整,并不是毫無意義的隨意性的置換,它的演變同樣體現了一個內涵連接的邏輯關系。《晉書·藝術列傳》小序云:“圣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后,史不絕書。”[12]2467這段話應該說越來越向著具有智慧內涵的理性方向演進,它體現的是《魏書·術藝列傳》與《晉書·藝術列傳》二者之間向更深層的內涵邏輯關系的演變。不僅如此,從“方技”“術藝”到“藝術”概念的演變,實際上是將“方技”到“術藝”所指內涵的具體化,由此使“藝術”或“藝術列傳”的內涵走向變成豐富且具有擴展延續性的空間。
前面我們講到了《后漢書》將“藝”與“術”二字合并為“藝術”使用,是我國古代“正史”中首先使用“藝術”這個概念的文獻,“藝術”這個概念中的“藝”“術”二字,實則是并列關系的兩個詞,是非偏正詞組。也因此,李賢在注釋時是分別進行闡明其含義的,說明了“藝”“術”是各有所指的。《魏書》用“術藝”這個概念立傳,而《晉書》《周書》《隋書》《北史》時,“術藝列傳”變遷到“藝術列傳”,就是說回到了《后漢書》所使用的“藝術”這個概念,這其中到底是有著本質的變遷還是隨意性的變化?這一變遷是我們要探討的問題。
前面我們引用了《魏書·術藝列傳》的小序,它明確地指出了“術藝”所包含的內容以及內容所指向的功能。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首先《魏書·術藝列傳》小序中所說的“往圣標歷數之術”,“數”在古代泛指“技術”,因而有時稱為“術數”(“數術”);有時專指“占卜”一類,《漢書·藝文志》將“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個方面列入“術數”范疇。從這一點上看,《魏書·術藝列傳》顯然接承了《漢書·藝文志》的路徑。《魏書·術藝列傳》把有關“數”的技術,即數之“術”放在了首位,也許作《術藝列傳》的魏收等人認為,天文歷法、龜策陰陽等是頭等重要的技術;“工藝”則是“百工”與“技藝”的合稱。《考工記》說的“百工之事”乃是造物范疇,主要是“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11]2,關于百工之事的技術,《魏書》置于后面“分論”,不難看出《魏書·術藝列傳》對“術”與“藝”的內涵有著特殊的指向,也就是說,“術”所指的是“數術”一類技術,“藝”所指的是“百工”一類的技術。《魏書·術藝列傳》把天文歷法、占候龜策等“數之術”相對看得更重要一些,因為這些技術關系到國家大事,“陰陽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而“百工之事”的技術幾乎不關乎國家大事,只是人類一般生活的造物技術,恐泥致遠,“故往哲輕其藝”。事實上,《魏書·術藝列傳》最后的概括中非常有意思,前面我們已經引用過。在《術藝列傳》最后的概括中,首先提到的就是“陰陽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這是將“數”之“術”置于首位的原因之一;其次,“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重德乃自古訓,“三不朽”中“德”在首位,書禮樂的目的皆為德,故“先王重德”;至于“方術伎巧”等要“不詭于俗”,“習伎巧而必蹈于禮者”,才是“大雅君子”所為,但“伎巧”難以致禮,“故往哲輕其藝”。總而言之,“術”為“數之術”,“藝”為“百工之藝”,這就是《魏書·術藝列傳》用“術藝”立傳的真正原因。
那么為何《魏書》中的《術藝列傳》到了《晉書》中就變遷為《藝術列傳》了呢?我們在前面探討“方術”“術藝”到“藝術”概念的形成時,其實已經涉及到這個層面的問題。我們先看《晉書·藝術列傳》小序所云: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兇,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眾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于此。然而詭托近于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圣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后,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
詳觀眾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于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12]2467
我們可以看到,《晉書·藝術列傳》實際上與《后漢書·方術列傳》所闡釋的內容相一致。我們將二者比較一下。《后漢書·方術列傳》小序云: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于明靈之府,封縢于瑤壇之上者,靡得而窺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乃望云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圣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1825
我們可以看到《后漢書·方術列傳》與《晉書·藝術列傳》在內容上的陳述基本一致,二者開篇講的便是“定吉兇”(定禍福),“決猶豫”(決嫌疑),“審存亡,省禍福”,或“曰神與智,藏往知來”(知來物者),等等,幾乎沒有區別。同時《后漢書·方術列傳》和《晉書·藝術列傳》都提到孔子。《后漢書·方術列傳》小序云:“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5]1825。《晉書·藝術列傳》小序云:“圣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后,史不絕書。”[12]2467實際上以孔子作為將這些“小道”
納入正史的理由。孔子整理《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所謂“編六經”,漢代又是“獨尊儒術”的思想占主導地位,且唯有通經學才能治史學,即“出經”才能“入史”,不難看出,古代史家們借孔子的種種言行把這些“小道”納入正史恐怕是他們的一種策略。當然從這些規定的“內容”中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藝術列傳”是由“方術列傳”演變出來的。
但為何《晉書·藝術列傳》小序一開始用的是“藝術”的概念,而不是用的《魏書·術藝列傳》中的“術藝”概念?這個問題前面我們在探討“概念”的變遷時已經作了闡述,《魏書·術藝列傳》后面的“總括”也講得非常清楚,不再贅述。總覽二十四史,自《晉書》的《藝術列傳》以后,《周書》《北史》《隋書》都是以“藝術”的概念為“藝術”立傳的。
《周書·藝術列傳》小序云: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雋、蔣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克定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于隋。自余紀于此篇,以備遺闕云爾。[13]837
《周書·藝術列傳》依然認為“藝術”屬于“小道”即“曲藝末技”,這種認識是對前面“方術”“方技”“術藝”“藝術”等認識的一脈相承,只是這里所描述的是為何要傳承這些“小道”。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學術之士蓋寡”“史失其傳”等,需要整理、記錄與編纂,同時還對那些“曲藝末技”進行多方位的“咸見引納”,當然也有流傳的“方藥特妙”的入編,對這些“一時之美”的各種技藝“紀于此篇,以備遺闕云爾”。最后《周書·藝術列傳》“總括”云:
史臣曰:仁義之于教,大矣,術藝之于用,博矣。狥于是者,不能無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技巧而必蹈于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于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于是信矣。[13]851
從《周書·藝術列傳》的總括這里我們還能看到由“術藝”至“藝術”的這一路徑,在描述時用的還是“術藝”的概念,印證了前面我們所說的“術”與“藝”是并列關系,二者可以前后并置而不影響對其意義的理解。但我們更要看到《周書·藝術列傳》總括對“術藝”或“藝術”的闡釋和定位:“仁義之于教,大矣,術藝之于用,博矣”。將“仁義”與“術藝”進行比較,在《周書·藝術列傳》中顯然認為“術藝”比“仁義”層次低得多,“仁義”在于教化人,因而是“大”義,故謂“大道”;“術藝”在于滿足人們的一般生活之用,故此用途“博”廣,故是“小道”。所以,“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這就如同《論語》中所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方技這些“小道”乃有小“用”,所以《周書》再次強調,盡管“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技巧而必蹈于禮者”,但“豈非大雅君子乎”。因此,我們看到《周書·藝術列傳》對“藝術”的定位是“小道”,但“小道”是對“大道”的密切配合,是對“大道”的有益的并非可有可無的補充。這個邏輯傳承路徑在《隋書·藝術列傳》里依然可見。
《隋書·藝術列傳》小序云: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御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圣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
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
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后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采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14]1763-1764
我們從《隋書·藝術列傳》中依然可以看到沿續的是前面的《藝術列傳》的脈絡而咸相祖述,但是比以往的祖述更為具體一些。除了卜筮一類的決嫌疑之外,明確地提到了“醫巫”。“醫”和“巫”分別屬于“養性命”與“御妖邪”,把原來卜筮和巫混在一起的提法分開了,并明確了各自的功能。更需要注意的是,《隋書·藝術列傳》首次將“音律”納入,其功能是“和人神,節哀樂”,即正式把音樂列入《藝術列傳》中。另外,把“辨貴賤”的“相術”也從“巫術”中獨立出來,細化了不同術藝、方術或方技的分類,“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也因此,《隋書·藝術列傳》沿襲祖述,將不同藝術或方術領域中的名人列于小序中,以強調他們在不同領域的技術或藝術。
最后我們再看看《北史·藝術列傳》的小序: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御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圣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
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后來作者,咸相祖述。[15]2921-2922
《北史·藝術列傳》與《隋書·藝術列傳》的內容有著驚人的相似,前者幾乎就是對后者的復制。也由此我們看到二十四史中從《后漢書》的“藝術”概念到《魏書·術藝列傳》再到《晉書·藝術列傳》《周書·藝術列傳》《隋書·藝術列傳》《北史·藝術列傳》,“藝術”從概念到內涵就此確立,它是從“經史百家之言”中所“存夫藝術”而逐漸獨立出來形成“藝術列傳”,盡管此后有過“斷層”并一直到《清史稿》才再次出現,在“斷層”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的“藝術列傳”的內容化散在其他各個“列傳”中,然而二十四史中的“藝術列傳”為以后《通志》《四庫全書》《清史稿》等有關的藝術概念、范疇與內涵框定了路徑與文化意義上的脈絡。
結語
總體來講,“方術”“方技”“術藝”和“藝術”這些概念的變動,隱存著一個最基本的也是形而上的統領者——《易》。《后漢書·方術列傳》小序開篇就是“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5]1825,便揭橥了這個統領者。李賢注云:“易系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5]1825前面我們用了很大的篇幅引用了《后漢書·方術列傳》開篇之序,此文遵從《易·系辭》所說的邏輯而推論出“方技”的全部內涵與內容。而《后漢書·方術列傳》的全部內容又奠定了以后演變為二十四史“藝術列傳”的內涵與內容。《魏書》《晉書》《周書》《北史》《隋書》的《術藝列傳》或《藝術列傳》的小序,其開端就相同于《后漢書·方術列傳》以《易》為邏輯起點而統領全部內容。所以,中國傳統中的所有的藝術形態和內涵都可逆推到形而上的“道”,這個形而上的“道”便是《易》所洞開演繹的“大道”,并由這個“大道”統領各種形而下的“小道”。正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也是中國傳統藝術的文化特征。
《北史·藝術列傳》小序從《魏書·術藝列傳》到《齊書·方伎列傳》再到《周書·藝術列傳》《隋書·藝術列傳》,最后到《北史·藝術列傳》描述得非常清楚: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于游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敘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游,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俊、蔣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俊、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藝術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茍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15]2922-2923
綜觀二十四史,《后漢書》立《方術列傳》,《魏書》立《術藝列傳》,《晉書》《周書》《隋書》《北史》立《藝術列傳》以及后來的《清史稿》立《藝術列傳》,繼《后漢書·方術列傳》后,更名為“方技列傳”,立傳的有《北齊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從“方術列傳”到“藝術列傳”再到“方技列傳”,最后復歸“藝術列傳”。當然,這不是簡單地“復歸”,而是“藝術列傳”的變遷歷史,其中的內容復進復出,但都是在“方術”基礎上進行的,在某種意義上講,“方術”概念或“方術列傳”是“藝術”概念或“藝術列傳”的源頭,而二十四史中的“藝術列傳”是后來以及當今中國藝術及其藝術理論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