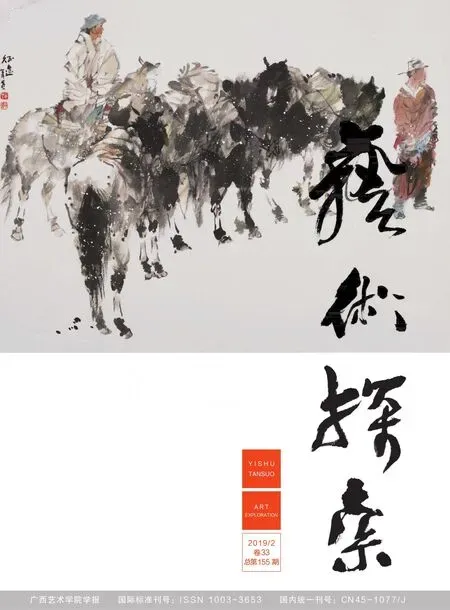虛擬美學視域下關于電影現實主義的理論思考
任 艷
(遼寧大學 廣播影視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新時代,現實主義再次被提出來,弘揚現實主義精神,加強現實題材文藝創作成為當前文藝界的重要任務。現實主義曾經占據著我國文藝創作體系的中樞地位,但是卻在社會和時代的發展過程中一度淡出,退守邊緣,這對于中國文藝創作與理論體系建構來說,都是一種疏忽或者說失誤。[1]153-162新時代對現實主義的重提無疑是對曾經的疏忽和失誤的糾正。從創作實踐的角度來看,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也呈復興之態,這些創作仍然需要理論的總結和指導,繼續推進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建設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時代和社會環境畢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味地固守和重復曾經的現實主義理論和方法是行不通的,只有真正地從現實出發,從創作實踐出發,才能找到現實主義理論研究的突破口,也才能真正地回答當下的現實主義創作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才能真正地推進理論研究和建設的發展。本文以電影為文本,從數字技術的角度思考現實主義的問題,未嘗不是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一、數字虛擬技術與現實主義電影創作
數字技術的發展最初引起的是電影理論的緊張,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和辨析電影美學的新動向,虛擬美學成為數字電影技術時代的重要語境。以“攝影影像本體論”為核心的電影現實主義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沖擊,一度走向了被否定的邊緣,然而最終還是在這場藝術與技術的博弈中堅守了下來。
數字虛擬影像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指向想象世界的,其優勢和獨特魅力也體現在“非現實”的影像創造上,幻想題材的電影似乎更適合于數字技術的運用與發揮,而“現實主義電影相對較難發揮數字技術的憑空創造性”[2]99。但這一疑問的產生只是被技術效果的一時蒙蔽而已,現實主義是一種藝術創作的方法和風格,屬于一種藝術思想和觀念,并不是由電影技術決定的。任何技術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電影數字技術也是一樣。雖然數字影像更需要藝術的想象力,或者說奇幻題材的故事才更能體現出數字影像的獨特魅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數字影像與現實主義電影是完全絕緣的。
電影創作的事實證明,數字電影技術完全可以在現實主義影片中使用。有一些場景或情境無法實際重現,而搭景又耗資巨大,在這種情況下數字技術便能夠發揮“創造現實”的作用,逼真地展現那些具有現實藍本的對象的全部或細節。對于同樣的現實場景的呈現,數字影像可能比攝影影像更真切、更接近于生活的原貌。在一定意義上說,數字技術大大拓展了電影紀錄現實和再現現實的功能,因此數字技術完全可以成為電影現實主義創作的有力手段。導演大衛·林奇2007年拍攝影片《十二宮》時為了重現故事中的真實場景,利用電腦特效精確再現了1969和1970年“十二宮謀殺案”發生地的原貌,而這些早已不存在的歷史面貌是僅靠傳統的攝影方式難以呈現的,正是數字技術使影片取得了一種更理想的再現現實的效果。再比如中國的影片《唐山大地震》正是利用數字技術逼真地呈現了地震發生時那具有毀滅性的情景。運用得當,數字技術同樣可以成為進行現實主義真實性表達的有力手段。
所以,將電影數字技術看作是豐富和發展電影現實主義的手段更合理一些。美國學者普林斯便認為數字美學的發展有可能取消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分立,促使理論研究從另外的角度去認識現實主義創作[3]221。技術的發展絕不意味著對傳統理論的完全顛覆,更可能的是帶來理論的革新與進步。
二、影像與現實的關系:從“鏡子說”到“假定說”
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第一原則是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真實地再現生活,“力求準確地、完全地、真實地再現當代世界的社會環境”[4]35。早期的現實主義作家們有非常著名的“鏡子理論”,巴爾扎克就曾說過:“作家應該熟悉一切現象,一切感情。他心中應有一面難以明言的把事物集中的鏡子,變化無常的宇宙就在這面鏡子上反映出來。”左拉曾用鏡子的比喻對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進行比較分析,他認為古典主義是“放大屏幕”,浪漫主義的屏幕是一個三棱鏡,而“現實主義屏幕是一個簡單的平面鏡,很薄,很清楚,它力求自己完全透明、圖象可以透過它,重現它們的現實。”[4]39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被認為是對生活現實的再現和還原,而不是創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拒絕創造。現實主義藝術是“一種觀察的藝術,代替了想象的藝術”[4]43,主張作家和藝術家通過觀察和比較來認識世界,忠實而精確地將現實表現出來。這正是一直以來現實主義留給大家的印象:再現生活,摹寫現實,而不進行創造。
我國電影藝術的現實主義創作也一直遵循著這一原則,將電影與現實理解為一種同構關系,即用電影創造一個現實的“鏡像”,電影像鏡子一樣不加改變地將現實的影像呈現在銀幕上,“現實效果表示觀影者依據假設足夠強烈的真實效果,對于再現形象歸納出來的一個‘存在的判斷',為這些形象確定一個現實中的參照物。易言之,他相信,他看到的不是現實本身,但是他看到的是曾在現實中存在的事物”[5]78。現實主義影片應該植根于現實生活和社會歷史,從人物到環境都需要與客觀現實一致,電影畫面上的一切都需要有現實的依據或者直接就是照搬現實,一旦有與現實不相符的地方便會受到“虛假”或“脫離現實”的批評,所以創作者也都小心地進行自我規避,在藝術表現上極為謹慎。相比較而言,現實主義的影片往往比其他類型的影片更樸素、更嚴謹,缺少藝術創作的自由灑脫之感。一直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巴贊提出“攝影影像本體論”的觀點,在“還原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更進一步,影像風格從樸素走向了粗糲,去除一切藝術的修飾和裝點,最大程度上保持現實的“原生態”。
然而,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電影與現實進行高度對應的觀念似乎難以為繼。數字技術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無中生有”。比如計算機成像技術(CGI),可以完全憑空創造根本不存在的形象,而且能夠使其非常逼真。傳統的攝影技術需要攝影機前“實有其物”,而數字技術則完全不需要如此。除此之外,拍攝過程中的計算機控制技術、后期剪輯中的數字調色技術、影像合成技術、數字聲音技術等都具有非常強大的創造功能,在數字技術參與下獲得的影視畫面遠比傳統攝影技術獲得畫面更具有藝術創造的空間和可能,數字技術使得影視創作具有了更強大的創造功能和美化功能。這些似乎與現實主義拒絕創造的原則恰恰相反。但數字技術的魅力是創作者們難以拒絕的,缺少視覺吸引力的電影作品在當下的電影市場上也是難以存活的。不管是出于自覺,還是被迫,數字影像技術也開始被大量地應用于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比如電影《孔雀》中大雨打爛剛拓好的蜂窩煤的情景便是借助數字技術完成的,電影《云水謠》《三峽好人》中的“華麗版”長鏡頭也是利用數字控制技術拍攝制作出來的。
新的創作實踐,新的生存語境使研究者們不得不去思考:數字技術時代電影影像和現實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生活的本來面目”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現實主義是否意味著完全拒絕“想象”和“創造”?
電影理論界因此又提出了“假定性”的概念,與傳統的“現實性”進行辨析。學者們進行的這種理論上的爭議,其目的在于打破“電影與現實同構”的傳統認識,改變將電影與現實進行簡單對應的創作思想和批評方式。
傳統的“現實性”強調的是電影同現實之間的相通性、相似性,電影創作只有遵循社會現實的基本原則,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講述故事,才能實現對社會現實的真實完整的再現,才能建立起電影的現實主義敘事。但對這一點的過分強調容易引發“電影等同于現實”的誤解。“假定性”強調的是電影同現實的非同一性。因為任何藝術創作的過程都必然伴隨著選擇、刪減和改造,任何來源于現實生活的故事和場景,都只是藝術創作的“原材料”,不可能原封不動地進入藝術作品。任何進入了藝術的生活現實都已經是“一種特殊的形態,是從現實生活中抽象出來的、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形態” 。[6]107-115正是“假定性”賦予了藝術創作的獨立性,使藝術作品成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自我世界”,具有“與日常現實完全不同的性質”。[7]430“假定性”的提出將現實主義創作同生活現實拉開了距離,能夠填充這段距離的正是藝術的創造性。至此,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總結:現實主義創作中所展示的“生活的本來面目”并不意味著要與現實生活絲毫不差,而是可以有藝術化的改寫,可以利用藝術修辭將其放大或強化,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變形,現實主義除了要讓觀眾理解、看得懂之外,還需要具有藝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比如2018年7月上映的《我不是藥神》,這部號稱“可以改變國家的電影”毫無疑問是現實主義的,然而這部現實主義電影并不是完全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來講述故事的,現實中身患白血病的當事人變成了電影中販賣印度神油的落魄商販,一個“自救”的故事被改寫成了“救他”的故事,其中融入的酒吧艷舞、印度街景、飆車對決等場景又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現實的日常情境,利用近景、特寫等拍攝方式將拍攝對象從環境中突顯出來,制造出非同尋常的視覺沖擊力。可以說這部影片的基調是現實主義的,但是又從傳統現實主義的那種“現實對應”的做法中跳脫出來,運用了更適合市場需求的方法進行“娛樂化”的講述,使得這部影片既具有強烈的關注現實、反映現實的價值意義,又具有很強的觀賞性,贏得了市場的關注與成功。這種成功不得不說得益于導演“不想把《我不是藥神》拍成一個經常見得到的中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樣子”,而是“保持現實主義的基調”又“盡量從現實主義中抽離出來”的自覺嘗試。[8]45
對于現實主義電影創作來說,“現實性”與“假定性”并不矛盾,是現實主義創作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現實是基礎、是來源,“假定性”是藝術創造的可能。通過改造現實的藝術手段創造出現實生活的“幻象”,只要能夠喚起觀眾頭腦中的那個現實,有助于增加觀眾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解,便可以認定為是合格的現實主義創作。忽視現實性或忽視假定性,都不利于現實主義藝術創作。重要的是正視兩者的悖論性,把握好兩者的界限,才能更好地認識現實主義,才能創作出更好的現實主義電影作品。
三、 數字技術的“虛擬性”與現實主義的“真實性”
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影像和現實的關系,當銀幕上呈現出的“視覺奇觀”更多地依賴藝術的想象和創造,當數字技術的虛擬美學大行其道,現實主義的真實美學又當如何自處?又該如何認識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問題?
曾經中國電影界有一句戲言,好萊塢電影把假的拍得像真的,而中國電影把真的拍得像假的。看似戲言,卻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一個現實:好萊塢的許多純虛構的影片,如《侏羅紀公園》《真實的謊言》《阿凡達》《高手玩家》等,讓人看得如癡如醉,而我們的許多以真人真事為基礎改編的現實主義影片,如《最愛》《張思德》《百團大戰》《高考1977》等,卻似乎沒有取得讓人信服的效果。這不得不讓人重新思考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問題,甚至有人開始懷疑電影現實主義的“真實性”標準。有學者曾明確提出,真實不應該再被視為電影創作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藝術準則。[9]174-177初看起來,似乎合理,但細究起來就不難發現,這里面其實存在著概念的混淆與誤讀。“把假的拍得像真的”與“把真的拍得像假的”這里面包含著兩種“真實”的含義。一種是經典現實主義中所指的“真實性”,一種則是數字技術電影追求的“真實感”。
經典現實主義所指的真實性,是從作品與世界的關系角度定義的真實性,以唯物主義認識論為基礎,認為藝術創作(包括電影創作)都是對客觀的物質現實的反映和表現,“社會生活的物質存在性亦即客觀物質性為第一性根據,文學寫作實踐是第一性根據的正確反映及藝術表述”[10]149。也就是說,藝術作品的真實性是以物質現實的真實性為標準的,這其中又包含著兩層遞進的意義:一是要求作品所描繪的對象講述的內容符合現實的真實、生活的真實和事物自身的真實;二是這一現實生活的真實又反映著生活的本質、規律及歷史必然性,能夠揭示社會現象背后的相對恒定的規律性的東西。所以,從根本上來說,經典現實主義所指的真實性是社會本質性的真實。
而真實感是從電影與觀眾的關系維度對電影的一種考察,是接受心理角度定義的“真實”,即觀眾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獲得的“真實”的心理感受。觀眾清楚地知道這些故事不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的,甚至是不可能在現實中存在的,純粹是虛構出來的,但是觀眾仍然能獲得一種真實的感受和體驗,覺得影片發生的一切就像真的一樣。應該說是電影創造了一種“感覺上的真實”,這也就是所謂的“把假的拍得像真的”。
數字技術的虛擬美學追求的是一種影像上、視覺上的真實感,要求看起來符合物理學、力學、運動科學、生物學等的基本規律,符合一般觀眾對于世界認知的基本常識,從而在觀眾心中喚起一種“真實”的感受。事實上真實感的建立仍舊需要以現實的真實性為基礎。美國學者S .普林斯在對斯皮爾伯格的影片《侏羅紀公園》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之后得出一個結論:“較為接近真實的形象都與它們的參照實物具有在索引性與外貌上的同一性。它們與其參照物十分相似,而這些參照物則反過來正是形成這些形象的源泉與實物聯系”[3]221。這就是說虛擬形象的背后仍然有一個現實的參照物作為想象的基礎,以現實參照為基礎的想象和虛構才能夠喚起觀眾現實的生活經驗和感受,才會讓觀眾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真實感。就像《侏羅紀公園》中的恐龍,首先是因為它的形象、動作、情態符合現實中動物的一般性特征,所以才會在觀眾心中喚起一種真實的感覺。真實存在的生物特征是電影里虛假的恐龍形象讓人感覺真實的根源所在。“真實感”存在于影片和觀眾之間,但“真實感”的產生仍然離不開現實的“真實性”。
推及故事層面仍然存在“真實性”與“真實感”的問題。電影現實主義追求的社會意義上的“真實性”同樣需要在觀眾心中喚起“真實感”才能最終得以實現。像北京大學教授陳宇在談到影片《高考1977》時說過的一樣,“影片中故事發展的邏輯和假定人物的情感邏輯,符合觀眾的心理邏輯。兩層邏輯的重合,意味著觀眾對于影片中事件發展的因果關系的認同與情感認同”[11]83。觀眾只有認同了影片中的故事邏輯和人物情感邏輯才可能相信影片所表現的“真實性”。就像影片《高考1977》因為講述的故事不符合那個特定時代的情感邏輯,無法讓人相信,也就很難說反映和表現了那個時代的“真實性”。
“真實性”和“真實感”是真實的兩個維度,“現實”是其共同的基礎,兩者不應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否定的,而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四、數字美學時代電影現實主義的形式問題:影像呈現
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從賈樟柯的《三峽好人》說起。影片開頭是一個極具藝術性的長鏡頭,鏡頭緩緩地從船頭平移到船尾,一一展示著船上的乘客,直到一個人安靜地坐在船尾的主人公進入成為畫面的主體。這個鏡頭也是利用了現代的影像合成技術才有了現在的效果。這個具有藝術震撼力的鏡頭竟然受到了“炫技”的批評。批評者認為這樣的鏡頭雖然看起來很美、藝術性很強,但是對現實主義影片是一種損害。提出這種批評是基于一種傳統的認識:現實主義電影的鏡頭應該是一種真實的紀錄,而不是技巧的展示。數字影像的最大優勢恰恰在于利用技術手段產生的超強的修飾功能。這是數字技術時代現實主義電影理論必須回答的又一個問題:現實主義電影的影像風格應該是什么樣的?
對于現實主義來說,“真實”始終是其不可更改的藝術內核,那么現實主義電影的影像呈現問題也就是“什么樣的影像語言更具有真實性”的問題。按照法國學者雅克·奧蒙和米歇爾·瑪利在其《電影理論與批評辭典》指出了電影影像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影像的雙重實在”,意指影像天生具有一種雙重性:一是影像所呈現的內容,指向現實世界中實際存在的情景(真實發生或摹擬搬演的);一是影像本身,指向攝影、剪輯、構圖、色彩等電影技巧和電影手法。由此,也就產生了影像的雙重“真實”:第一重“真實”是來自于現實的,受到現實的真實面貌的限制;第二重“真實”則是來自于電影技巧的創造性“真實”,雖然這一真實根本上還是要以現實的真實為參照,但是卻為電影的創造性提供了空間,使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現實加以改變。[5]70這本是電影真實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但是人們對電影這兩重性質的認知并不是同步的,于是便出現了“影像真實”和“邏輯真實”的分野。
以巴贊的長鏡頭理論為代表的是對“影像真實”的肯定,看重的是影像的第一重真實,電影畫面應如實地反映現實場景,不對其進行修飾、不美化,不解釋、不分析,更不對其加以改變,而使電影畫面中的場景與現實場景高度一致,保持時空的統一性和完整性,使電影畫面呈現一種“復制現實”的效果,實現“影像真實”需要的是摒棄技巧,發揮攝影機的紀錄功能。比如在攝影方面拒絕極端角度,多用平視鏡頭,以此來避免畫面的變形和戲劇性效果,在色彩、構圖、光線、鏡頭運動、剪輯等方面同樣是盡量減少技巧性和人為的改造,影像風格往往簡單、樸素、平實,通常不具有強烈的視覺效果。比如影片《路邊野餐》里使用的鏡頭便是如此,看起來毫無技巧,意義的產生似乎完全依靠鏡頭里的內容本身,而不是景別、構圖、角度、剪輯等鏡頭技巧。其中標志性的鏡頭是一個長達40分鐘的超長鏡頭,展示了主人公從一個地方前往另一個地方的完整過程,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影像與現實的同步和一致性。
以愛森斯坦的“蒙太奇學派”和好萊塢的“經典剪輯”為代表的則是對于“邏輯真實”的偏重,更注重影像的第二重真實,充分發揮電影技巧的創造力,通過對電影畫面的加工、變形、分切、重組來實現對現實場景的藝術化表現,讓攝影機和電影手段更多地介入影像對現實的呈現。但是這種創造并不是任意的,有其特定的心理基礎和邏輯基礎,只要是在這一邏輯范圍內的創造,就仍然會讓電影畫面看起來是真實的。比如,可以利用攝影機角度的變化、鏡頭的運動或是景別的改變來引導觀眾的視點,使其關注的中心隨電影敘事的需求而動,又或者利用光線改變畫面的明暗效果,從而將場景中的戲劇性情境突顯出來。一般來說,追求“邏輯真實”的影片容易產生更強烈的視覺效果,影像風格更炫目多彩,也更具有視覺沖擊力。一般而言,更注重市場效益的商業影片會偏愛此種影像風格,比如《戰狼Ⅱ》,雖然影片中也有所謂“一鏡到底”的鏡頭,導演也在最大程度上追求真實,不用“數字特效”,但更多地仍然需要依靠特寫、剪輯等影像技巧創造出炫目的效果,否則就不可能有現在這種“拳拳到肉”的視覺效果。
在很長時間內“影像真實”被視為現實主義電影應該遵循的基本準則,而“邏輯真實”則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違背了電影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原則。實際上,電影真實應該是“影像真實”和“邏輯真實”共同建構的真實。現實主義影片的“真實性”是對社會本質真實的揭示和表現,必然需要一個“去偽存真”的創造過程,而影像的“邏輯真實”正是有助于實現這一創造過程的有效路徑,所以現實主義電影也不應該完全拒絕影像技巧和數字技術,同樣應該注重視覺上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如何在“影像真實”和“邏輯真實”之間尋求平衡才是關鍵。在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像《我不是藥神》《烈日灼心》《解救吾先生》《紅海行動》等現實主義影片并沒有受到傳統的“影像真實”觀的束縛,沒有局限于長鏡頭的使用,而是借鑒了商業影片的做法,加強了影像的創造性和修辭效果,不僅增強了影片的視覺吸引力,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真實性”的表達。
目前的現實主義創作面臨的是一個新時代,新的社會生活、新的時代精神、新的社會發展,這些都需要得到更好的表現和反映。在新的語境下,只有重新認識和理解現實主義理論,才可能更好地進行適應時代需求的現實主義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