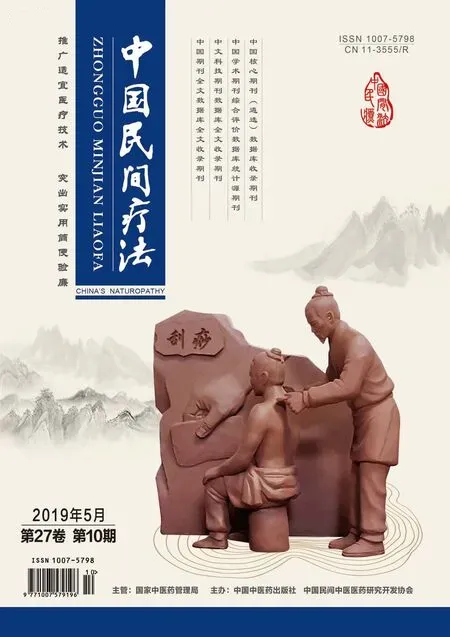中醫藥防治HIV/AIDS無癥狀期皮膚損害的研究進展※
郭婭婭,徐立然,邱 荃,李亮平,宋夕元,馬秀霞,王豪杰,韓迎東,趙正陽,李春燕
(1.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 鄭州450046;2.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河南 鄭州450000)
在各種類型的皮膚病中,艾滋病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的皮膚損害問題較嚴重[1]。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AIDS患者的皮損情況具有發病率較高、不甚典型、較難治、病情嚴重、容易誤診、漏診等常見的臨床問題。相關調查結果顯示,一些發達國家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指南數量很多,且質量較高,涉及臨床范圍較廣;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艾滋病防治指南相對數量少,質量不高,涉及內容較為狹窄。目前,艾滋病患者人數逐年增加,HIV/AIDS引起的皮膚損害問題影響著多數患者的生活質量和自信心。因而,進一步調整和擴展HIV/AIDS防治的研究方向迫在眉睫[2]。
1 HIV/AIDS皮損的中醫淵源
艾滋病屬于中醫“疫病”范疇,《素問·刺法論》記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癥狀相似。”中醫認為,疫病的發病機制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嚴重受損,正氣虛弱,正不勝邪,毒邪余留,久則化毒從肌膚而出[3]。我國傳統中醫理論有關保持健康的中心思想是維持陰陽之間的動態平衡,尤其是五臟內的平衡。中醫基礎理論認為,五臟的功能相生相克,相互聯系。從現代生理學和病理學的角度看,就是保持不同組織和器官、細胞和電生理活動之間相互聯系的動態平衡。植物的天然活性成分具有綠色、安全、溫和的獨特優勢,首先根據中醫基礎理論辨證論治,同時結合HIV/AIDS患者自身體質,為其制訂治療方案。目前,已經大量運用于臨床的有藥浴、面膜、針劑、膏劑等,不但開發出更多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優質產品,還能將我國的中草藥產品推向世界[4]。
2 當前艾滋病皮損治療的研究
在艾滋病患者的窗口期和中晚期一般采用抗病毒治療,但其藥物引起的藥物性皮膚損害影響著患者的生活質量。艾滋病引起的慢性皮疹是一種過敏性炎癥性皮膚病,屬于中醫“濕瘡”范疇,相當于西醫的濕疹,多由皮膚真菌及其他病原體感染引起。參照《艾滋病診療指南》[5]中無癥狀期及艾滋病期的診斷標準,當艾滋病患者感染HIV病毒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皮膚損害,如水皰、皮疹、紅斑等,一般采用抗病毒治療及皮質醇激素或抗組胺類藥物控制,但長久使用此類藥物易產生耐藥性及依賴性,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付立功采用加味四物消風飲治療艾滋病慢性皮疹療效顯著[6]。
王小莉等[7]對1例HIV感染合并重度銀屑病患者進行臨床觀察,分為3個時期治療:①進展期:火毒熾盛,用黃連解毒湯加減;藥用水牛角、漏蘆、黃芩、黃連、梔子、麥冬、麻黃、竹葉、石膏、沙參。②停止期:血熱蘊結,宜清熱涼血,解毒祛斑;藥用黃連、生地黃、重樓、黃芩、五味子、漏蘆、連翹、水牛角、白花蛇舌草。③緩解期:熱毒留戀證;藥用黃連、連翹、五味子、竺黃、重樓、生地黃、金銀花、青黛、水牛角、白花蛇舌草。劉靜靜等[8]以行氣活血、清熱止痛為法,用拔罐和拔罐放血治療AIDS合并帶狀皰疹68例,有效率為97.22%。梁飛立等[9]以清熱鎮痛、活血消毒為法,治療72例老年HIV/AIDS并發帶狀皰疹患者,將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治療組采用痰熱清注射液聯合中藥外洗治療,對照組采用阿昔洛韋軟膏外用,治療后治療組治愈率高于對照組(P<0.05)。劉振威等[10]以祛風止痛、燥濕止癢、祛風濕,止痹痛,強筋骨為法,將60例HIV/AIDS患者隨機平均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采用壯醫藥線點灸法,同時配合圍針輔助手法治療,加用京萬紅燙傷膏外用治療;對照組采用尼美舒利分散片、泛昔洛韋片、維生素B1口服治療,加用利巴韋林軟膏外敷治療,治療后治療組治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1)。李俊巖等[11]對35例AIDS合并肛瘺患者切開掛線療法輔以中藥治療,以破癥散結、健脾寧心、補氣活血、清熱解毒、祛風除濕為法,藥用金銀花、川黃柏、乳香、連翹、蒲公英、樸硝、斑蝥、白術、茯苓、紫花地丁、天花粉、梔子、蜈蚣、僵蠶、全蝎、元參、龍膽草、川黃連、知母、沒藥、黃芪、白芷、皂角刺、大黃,治愈率為90%。
3 小結
臨床數據表明,90%以上的HIV/AIDS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皮損,多數AIDS患者以皮膚損害為首發癥狀,兒童患者尤其明顯[12-13]。HIV感染患者免疫功能進行性下降,皮膚疾病不僅頑固難以治愈,且變證叢生[14]。中藥治療艾滋病皮膚損害應遵循中醫辨證論治的原則,從統一標準進行多中心、大規模研究,以便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