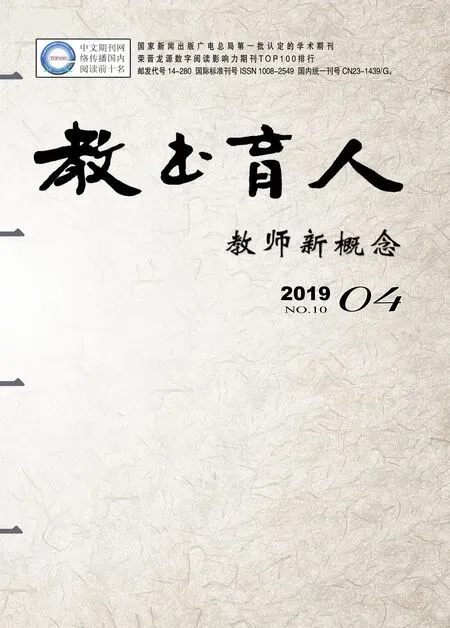凸顯言語形式,設置實踐活動
褚麗萍(江蘇揚州市江都區武堅鎮黃思小學)
一、緊扣文本言語形式,彰顯語言內核價值
文本寫作內容和寫作意圖不同,決定了所選擇的言語形式不同,教學中關注文本的體裁樣式,正確確立教學目標,遴選適切的教學策略,感受不同文體所具備的不同的言語表達形式,展現出文本不同的語言風格。
同一種體裁雖然有諸多共性,但不同的課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獨特價值。這就需要教師就不同的學段、不同的編排、不同的課文來選擇鮮活而突出的語言訓練點,挖掘獨具個性的語言實踐內容。如蘇教版五下編選了《秦兵馬俑》《埃及的金字塔》《音樂之都維也納》這三篇不同類型的說明文,我們除了關注說明文中說明要點、說明方法,感受說明文的一般性特點之外,這三篇說明文有著完全不同的教學側重點:《秦兵馬俑》在介紹各種俑時,運用了大量的四字詞語,緊扣俑的神態和動作進行大膽想象,展現出語言表達的生動性;《埃及的金字塔》除了運用一般性說明方法之外,運用“連鋒利的刀片都插不進去”的夸張性描述,凸顯了語言表達的生動與形象;而《音樂之都維也納》在分版塊陳述維也納作為音樂之都風采時,就大量運用了“大部分”“大多”“幾乎”等表示虛指的詞語,展現了文本語言表達的精準與嚴謹。
正是這些獨特而鮮明的言語形式,將文本所需要表達的內涵進行了完整而深入的詮釋,教師需要在把握一般性文體特征的基礎上,緊扣課文凸顯出來且與其他文本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才能讓教材文本的范例價值最大化。
二、親歷文本語言體驗,體悟言語表達精妙
語言的感知與理解是學生內在的心理行為,需要言語體驗的方式來達成。這就需要在教學過程中創設具體鮮活的言語情境,促進學生對文本語言和內在世界的感知,讓學生在習得語言和體悟語言的過程中,實現言語形式和言語內容的融合。兒童正處于形象化、直觀化思維階段,他們常常會將文本內容積極轉化為鮮活和可感的畫面。為此,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將自己的身心意識浸潤在表達過程中,感受文本語言的內在精妙。學生閱讀文本的過程離不開豐富的情感滲透,這更需要教師調動學生原始儲備的經驗,讓學生的身心與文本的語言產生積極的情感共鳴。
如《維生素C的故事》一文中這樣描寫:“不久,‘海上兇神’就悄悄降臨了”——這句話本身就極具特點,不僅為下文中缺乏維生素C的故事埋下了伏筆,同時也在具體的語言情境下凸顯出海上兇神的可怕。這種在表達上極具特點的語句就需要學生在實踐中有意識地加以運用。為此,教師引導學生緊扣文本的語句展開想象:這句話描寫了一種怎樣的情景?可以利用語句中“悄悄”“降臨”等詞語,描述自己鬧海中的畫面,將其神秘而又咄咄逼人的氣勢展現出來;隨后,教師激活學生內在的認知體驗,進一步感受語言文字背后所蘊藏的豐富內涵,探尋言語表達的內在精妙。
三、強化文本語言運用,促進言語遷移內化
提升學生語言文字運用的能力,就離不開語言文字的訓練,這就意味著教師要創設出讓學生親歷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實踐性平臺,在基于文本語境的基礎上,挖掘文本的語言生長點,在反復訓練過程中發展學生內在的語言能力。
語言文字運用的最高境界不是讓學生進行機械生硬地模仿,而是要讓學生在理解的基礎上再造語言情景,激發學生的情感表達。如學習《月光啟蒙》這篇課文時,學生緊扣文本語言,體悟言語中所流淌出的情感,感受母親濃濃的愛意以及作者對母親的感恩之情。為此,教師就激活多種感官進行表達,為學生呈現出這樣的填空題:每個人都沐浴著自己的母愛成長,母愛好像是……就像是……又像是……還像是……這就是母愛!學生嘗試運用自己的語言描述心中所想到的母愛。
在積極倡導語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教師需要從原本關注文本內容的維度轉向關注文本言語形式的維度,改變傳統教學中“教教材”的視角,真正嘗試“用教材教”的方式。這就決定了閱讀教學需要從文本言語形式入手,在凸顯言語形式、品味言語形式、探究言語形式的過程中,感知文本語言表達的秘密,提升學生的語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