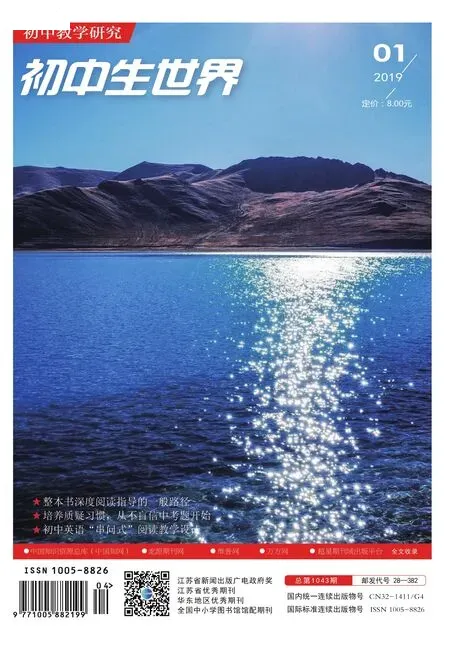語文課堂情境創設的誤區及對策
■韓靈靈黃志濤
(作者單位:①江蘇省海門市東洲中學;②江蘇省海門市東洲國際學校)
一、問題提出的背景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建議“課程目標從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方面設計。三者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目標的設計著眼于語文素養的整體提高”。三維目標的達成不僅需要教師詳細掌握學生的個體特征,而且需要教師對學生在群體中表現出來的新特征有所了解。
作為群體,他們會形成一種新的群體心理。“群體心理一旦形成,它就會獲得一些暫時的然而又十分明確的普遍特征。”[1]其中一個較為顯著的標志就是“自覺的個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轉向一個不同的方向”。[2]這種感情和思想上的轉向使課堂教學存在一定的隱患,它很可能變成一種強加的因素滲入學生思維。個體意識的覺醒能夠觸發獨具個性的表達。“為了使一個青年能夠成為明智的人,就必須培養他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不能硬是要他采取我們的看法。”[3]這是課堂教學的必備條件,也是新課程背景下的語文教師致力于課程改革的目標指向。
二、群體意識的思維陷阱
群體意識是某一個群體在信息交流和實踐活動中共有的意識。它對于其中個體的影響值得警惕。首先,當個體置身于群體組織當中時,他的個體意識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一切精神結構都包含著各種性格的可能性,環境的突變就會使這種可能性表現出來。”[4]其次,群體的感染性之強足以遮蔽個體意識。“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感染性。”[5]情緒的傳染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個體之間的情感共鳴,這對于學生深入某種情境去感受其中的心理和情感大有裨益。但是,當群體情緒與個體意識產生碰撞,其強大的沖擊力會將個體的獨特感受擊碎并取而代之。再次,“群體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簡單和夸張。”[6]這樣就減少了個體意識呈現的可能,并且會將個體心理中最有價值、最獨特的一面遮蔽,從而使個體性格在群體意識中缺少了表達和伸張的空間。
以蘇教版語文九年級上冊《我的叔叔于勒》為例,學生在課堂上一直對“我”的父母進行批判,說他們自私、虛榮、唯利是圖。這種思想之強大足以對在場所有學生的心理產生影響,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學生的個體意識。“每一個團體都是一個漏勺,會把所有人的個性削減到最普通的形式。”[7]在課堂教學中,聚集在一起的眾多個體在同一情境中所觸發出來的情感和心理容易趨向一致,教師應警惕其對個體的遮蔽和掩蓋。和群體共性相比,個性表達的作用應該更加突出。情境的創設不僅要讓個體沉浸于某一情境中,更重要的是要使個體意識能夠得到有效激發,從而實現“為了每一個學生的發展”的目標。
三、張揚個體意識的情境創設
個體意識是一種個體本位的思維模式。在群體意識的遮蔽下,尤其是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個體意識的表達雖然并非易事,但又迫在眉睫。“在中國文化的符號系統里,外在的社會關系與社會壓力在個人心靈中造成的比重,遠遠地壓倒個人對自我心理狀態的知覺程度,以致必須由個人面對的心理危機轉化為面臨社會的羞恥感。”[8]群體環境對個體意識的遮蔽被逐漸發現,個體的價值在當代文化中的地位被逐漸發掘。這種發掘在教育領域更具緊迫性和可操作性。具體到語文課堂教學中,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嘗試。
1.問題意識先行,激活情境。
問題意識之于學習的價值已經受到廣泛關注。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說的“問題意識”并非教師的問題意識,而是學生在閱讀過程中自發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產生的本身就是思維活躍的表現。學生在這種意識的引導下,自主向文本提問,并且在問題驅動下進一步深入文本追索答案。在問題意識的帶動下,閱讀行為指向文本細節,在激發學生思維的過程中實現了對文本的解讀。
以《我的叔叔于勒》的教學為例,在學生對“我”的父母的“大批判”中,教師引導學生設身處地地站在文中人物的視角,去發掘他們的無奈,并以此透視當時的社會土壤就顯得重要與難得。“難道他們真的一無是處嗎?”教師的問題激發了學生的問題意識。在這一問題的驅動下,學生開始對自己之前的想法產生疑問、審視自己的想法,并且嘗試從新的角度去認識文中的人物。隨著思考的深入,學生心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更加豐滿。問題意識驅動下的文本解讀不僅是對文本的深入理解,也有利于解讀的多元化。尤其難得的是,在問題驅動下,學生的思維變得空前活躍。這不僅能夠激活教學情境,而且為接下來的學生之間的思維碰撞提供了前提。
2.學習方式側重探究,深入情境。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指出:“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語文課程必須根據學生身心發展和語文學習的特點,愛護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勵自主閱讀、自由表達,充分激發他們的問題意識和進取精神,關注個體差異和不同的學習需求,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在新課程標準的倡導下,探究式學習已成為課堂教學的顯性要素。
在《我的叔叔于勒》的教學中,在問題意識的帶動下,學生們分組探究這一問題。在對這一問題的課堂討論中,學生紛紛從正面去發掘“我”的父母這種做法的現實出發點,即他們害怕當年于勒和他們生活的情景的再次出現,擔心于勒的出現擾亂他們現有的生活。他們也有生活處境上的尷尬和無奈。這樣的探究結果不僅豐富了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而且將學生的思考引向深入。更為難得的是,學生在探究過程中逐漸深入文本的情境之中,走進了人物的內心世界,設身處地地體悟人物的心理和情感。這種過程性的體驗已經超越了內容理解和方法習得等教學目標,指向情感態度價值觀這一較高層次的教學目標,而且這一目標的實現是在文本解讀過程中自然生成的。由此可見,無論是對文本解讀的實現,還是三維目標的達成,能夠深入文本情境的探究式學習都是行之有效的學習途徑。
3.教學評價趨于多元,反思情境。
新課程標準極力倡導評價的多元化。其關于閱讀的評價建議為“閱讀的評價,要綜合考查學生閱讀過程中的感受、體驗和理解,要關注其閱讀興趣與價值取向、閱讀方法與習慣,也要關注其閱讀面和閱讀量,以及選擇閱讀材料的能力。重視對學生多角度、有創意閱讀的評價”。可見,新課程標準提倡的評價方式已經遠非對結果的評價。它更加關注學生的理解和感受,更加側重閱讀方法的習得和習慣的養成,更加重視閱讀的“多角度”和“創意”。而這些無不指向學生的閱讀過程,即側重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的個體意識。杜威的一個比喻值得我們深思,他說:“如果家長或教師提出他們‘自己的’目的,作為兒童生長的正當目標,這和農民不顧環境情況提出一個農事理想一樣,是荒謬可笑的。”[9]雖然這個比喻是針對學習目標而言的,但其對教學評價同樣適用。即使是來自教師的評價,也應該將學生的個體意識作為重要的因素來考量。在這個意義上,教學評價的多元化有助于我們反思教學情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為我們審視教學情境并且針對現時的學情對其進行及時而適當的調整提供了重要依據。
四、情境創設的落腳點
基于以上大眾心理學的考量,教學過程中的課堂情境創設一方面要結合文本內容和實際問題進行設計;另一方面還需在對學生群體與個體之間關系的考察上有所警惕。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是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起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使自身認知結構得到發展。”而課堂情境的創設則需要關注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建構主義心理學背景中的最近發展區是介于現實與潛在的發展水平之間的區域,他們的發展區是時間性的。而大眾心理學背景下的最近發展區則是介于群體和個體之間的潛在發展區域,是空間性的。也就是說,教學情境的創設方式是多樣化的,但是其落腳點應該是介于群體氛圍與個體意識之間的最近發展區。理想的效果是將不同的個體聚合為一個群體,并使群體活動作為觸發個體表達的土壤,成為張揚個性的平臺,這樣的群體才能和而不同,相促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