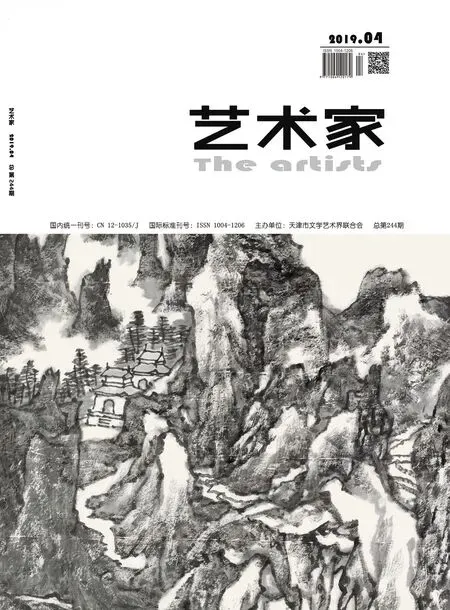中西繪畫構圖比較研究
□林佳琦 哈爾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文化傳播和社會發展的不同,在繪畫的藝術形式、表現手段、藝術風格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通過比較研究中西方繪畫的構圖,不僅能深入探索繪畫構圖中存在差異的原因,還能使我們意識到它們之間因為差異形成的互補性特點,從兩者中汲取營養,挖掘其潛在的價值。
一、中國畫的構圖
中國畫可以分為山水畫、花鳥畫、人物畫三大類,它的空間構圖講究虛實相生、疏密繁簡、縱橫開闔、脈絡氣勢。常見的構圖形式有“之字形”“三角形”“十字形”“工字型”“對角線”等。畫家的創作目的在于將繪畫技藝與精神進行傳承,抑或用來送人,有時也是為了對場景進行裝飾。例如,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它的構圖就極具代表性。整幅畫面打破了時間的概念,把不同時間中發生的事件安排在了同一個畫面中。其用屏風分隔出來五個場面,分別是聽樂、觀舞、歇息、清吹、散宴,每段場景都可以是獨立存在的,但又不失協調地統一在了整個畫面中。
二、西方繪畫的構圖
畫家喜歡臨摹事物的真實形象,因為非常注重寫實,所以在處理畫面空間時都是運用了一些固定、靜止的對象來構建,可以說是一種照相式的構圖。畫面構圖也非常講究科學原理,其利用點、線、面來展示空間上的節奏變化。一般畫面都是定出視平線,再定出透視線,所有物體在畫面中向后延伸都集中到了一個點上,用背景來襯托畫面,以此表現出畫面的三維空間。西方的繪畫構圖一般能表現出畫家的主題思想,其是創作者情感表達和藝術表現形式的統一。
在達·芬奇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中,畫面的水平線是桌子和桌子周圍延展開來所形成的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通過各個人物的動態起伏變化表現出了畫面中的緊張氛圍,運用輻射線構圖使耶穌這個人物形象置身于畫面的中心位置。正是輻射線的軸心在視覺感官上能給人以集中的作用,在感官上能讓欣賞者的目光都集中在耶穌身上。
三、中西方繪畫構圖形成差異的原因
(一)社會背景思想的不同
中國人的感性思想和西方的理性世界觀是相對立的。中國人講究天人合一,莊子說過,“天地與我并存,萬物于我合一”,其以天為本,將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因而造就了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因此,中國人在創作時面對真山真水,往往會淡化對畫面自然景物的外在表達,而更多地寄托在了情感的升華上。如果說西方美術尚形,那么中國美術則尚意。中國繪畫構圖是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的,繪畫中多用散點透視、移步換景,西方繪畫構圖則嚴格遵守空間和時間的界限,這種鮮明差異構成了世界美術領域中的兩大體系。
畢加索說過:“世上的一切都是在某種物象中出現,不能與自然背道而馳,我們面前必須要有現實的生活,畫家必須從一切地方——從天空,從大地,從一頁紙片,從匆匆過往的行人,從小小的蜘蛛身上吸收他獲取的印象。”很顯然,西方人在畫面構圖上很注重對事物真實形象的處理,追求的是由“實”取材。
(二)畫家身份的不同
中國的繪畫藝術家大多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他們常常通過繪畫來消遣打發平日里沉悶、無聊的時間,抒發內心的情感。一些“專業人士”往往是畫工,其創作出的藝術品只是為了賺錢和養家糊口。為了生計,他們的作品大多留于廟宇中, 很多人甚至是社會的最底層,他們寄情于藝術創作之中來抒發內在的思想情感。中國畫講究“一氣呵成”,因此作品多是一次性完成的。而西方的油畫畫家一般都有很強的職業性,只有經過手工作坊式的長期嚴格訓練,才能學會繪畫技術。油畫必須經過多次修改后才能達到效果,所以畫面構圖追求理性、嚴謹的態度。
(三)象征文化的不同
與西方的繪畫作品進行對比,中國繪畫中的象征內容及象征性意境是存在明顯差異的。西方繪畫對于人內心世界的表露往往都是通過繪畫進行直觀表達的。而在中國繪畫作品中,畫家尤為重視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如東晉顧愷之“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的傳神論。畫家往往運用象征手法,借用比喻、暗喻的手段來進行繪畫。象征藝術委婉、含蓄、簡潔,其表現的題材大多是自然景觀、花鳥蟲魚、動物怪獸、古典詩文、神話典故、歷史故事等。西方藝術自文學思潮開展以來,給藝術創作注入了新鮮的活力。西方繪畫是一種再現藝術,所以西方繪畫的藝術創作是透過外在揭示本質,直觀露骨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及意圖,展現出的是一種直觀的內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