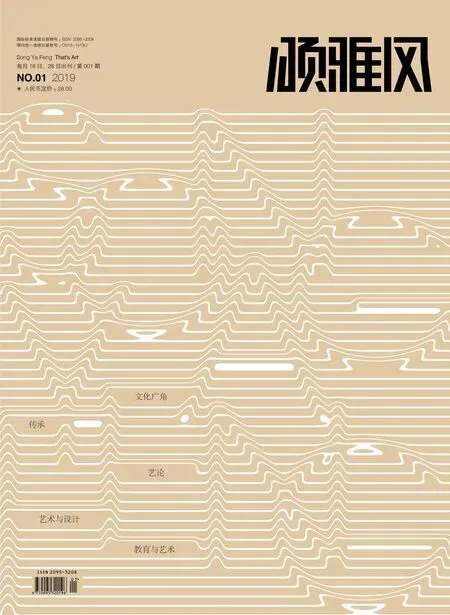關于“藏書票文化研究”的兩個問題
◎劉永麗
從藏書票文化發展史來看,藏書票不僅是一種版畫藝術表現形式,還是一件蘊含豐富文化內涵的藝術作品。這種藝術作品沒有宏大的畫面,但卻用方寸之間展現了東西方文化、古今書趣、人物愛書的心跡、圖書館藏書的源流,是人文和藝術深度融合和升華的產物。
一、藏書票表現內容與價值觀
所謂的價值一詞,梵文為Wal,意為“掩蓋,加固”;在拉丁文中為Vallo,意為“用堤圍住,加固,保護”;后演化產生英語中的Value,法語中的valeur,以及德語中的Wert 等詞。在西方有專門的價值學(Axiology),來探討人類價值問題。
西方藏書票的產生與發展伴隨西方印刷史、書籍史,歷經幾個世紀的傳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這樣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并稱頌希臘藝術“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西方藏書票的緣起與傳承是一致的:它緣起于西方的印刷業依附于西方版畫技術。西方藝術家從未放棄過他們的傳統,這在藏書票創作中特別得到了有力的體現。
在大量的西方藏書票中,我們看到西方的審美、文化、價值觀的彰顯,看到西方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看到方寸之間表現出來的氣勢磅礴的西方文化題材:從圣經故事到希臘神話,從但丁到塞萬提斯……看到中外藏書票收藏家熱衷的各種主題藏書票:如唐吉訶德主題藏書票,如號稱幾百年未曾畫夠的“麗達與天鵝”藏書票,等等。這些藏書票的魅力在于立刻讓人產生會心的審美共鳴,如同中國文化中對已知典故的理解。
學習不等于照搬,東西方有不同的價值觀、審美追求和文化傳統。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和”就是學習和吸收,學習他人優秀的文化為我所用,但非全盤西化,因為最終要“不同”,這樣才能發展。
一部分藏書票藝術家將創作眼光聚焦于中國文化并關注精神層面深層次表達,對于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藏書票文化研究是一個重要方向。
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遭遇的巨大變革對藏書票藝術的影響
藏書票作為一種具有深層次文化精神的藝術創作,自上世紀初流傳到中國,就經歷著一系列中國文化上的變動。那么這些變動對藏書票這種極具人文內涵的藝術是否會造成某些影響呢?
(一)中國近代以來的書籍形制巨變對藏書票創作者的影響
對母體文化的依戀是讀書人隱秘的內心需求。中國書文化源遠流長,從書籍裝幀形式看,有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等,直至最后線裝書出現和完善,一直在世界書裝文化史上獨領風騷,具有崇高的地位。但這種典雅的書裝藝術卻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戛然而止,在歷史的變革中一度被更具有科學與先進技術性的西式書裝形式所替代。形式上的斷裂、崩潰,摧毀的僅僅是書籍的裝幀形式嗎?傳統書裝形式感的丟失,在文化人的內心深處會有遺憾嗎?是否波及藏書票創作?
(二)文化斷層帶來的“文化身份糾結”及文化自卑對藏書票創作的影響
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以及八國聯軍圍攻北京等一系列事件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落后在文人中形成一種文化自卑的后遺癥,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被很好地治愈。(沈愛鳳《如何面對當下文化挑戰?如何振興民族藝術?》)“過去的100 年是中國文化在世界舞臺上幾乎失語的100 年,中國人不知不覺地掉進了西方人制定的時空坐標里,陷入到他們的價值體系中,慢慢地習慣在這樣的體系中找差距。然而文化之間只有差異而無差距,試圖在文化的時空里找差距就意味著你以喪失更多的自我為代價。”藏書票本身是文化的產物,而且更特殊——它比其他藝術形式更具有某種標榜的意味和價值觀的宣揚,最終對人的思想產生潛在的影響。
藏書票藝術在中國得到發展與普及的今天,這種極具人文性的藝術形式到底是文人私底下的玩物還是具有深刻文化意義、能產生積極影響的藝術形式?提出具有“中國精神”的藏書票到底有什么必要?的確是應該被重新思考的問題。
最后,筆者認為中國精神的藏書票理念不是指狹隘的民族主義,新時代背景下中國藏書票文化的研究與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要與東西方文化聯系起來進行研究,與書籍裝幀藝術家、與關心文化藝術發展的學者密切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