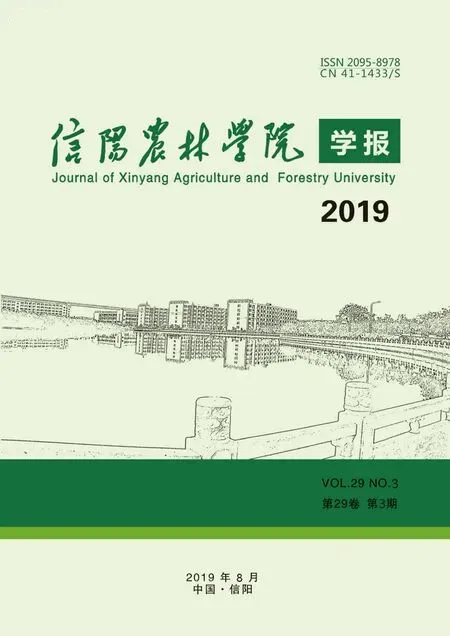先秦儒家語言倫理思想
成璇
(蘇州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蘇州 215100)
1 儒家語言倫理的思想基礎
首先,儒家的倫理思想是其語言倫理思想的基礎,其語言倫理思想受它的倫理思想的指導,是其倫理思想在語言上的反映。儒家歷來把“仁”作為其倫理思想的主旨,創始人孔子把“仁”作為處理人與人、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基本準則,認為人的道德應該是高于外界一切事物的[1]。他提出“仁”的思想,以及“仁者,愛人”[2]、“忠恕”等思想,強調了“仁”在人們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孔子之后,儒家一分為二,由于對“仁”的理解不同而衍生為兩大支派,一支是孟軻學派,一支是荀況學派,闡發了“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等道德規范,創立了第一個較為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
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仁”的學說,認為統治者治理天下應該實行“仁政”。具體內容有:一是“制民之產”,即規劃人民的產業;二是“與民同樂”,與人民休戚與共;三是“謹庠序之教”,即認真規范倫理教育。孟子認為,“仁政”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保民”,只有做到了“以民為本”,統治者才能真正無敵于天下。雖說他的主張在當時并沒有得以施行,但卻為后世的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了基本思路,因此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孟軻學派和荀況學派還立足于人,分別提出了“性善論”和“性惡論”的主張,探討個人道德修養,在強調學習教化的基礎上,著重發展內心反省、以一知道等修養方法。而這些思想反映在語言倫理上則體現為言語合乎仁、禮、德、忠、信、義,在言行上達到君子所做所為的崇高境界,重視個人的言語道德修養。
其次,儒家語言倫理脫胎于其語言思想,與其語言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記載孔子言論的《論語》是儒家典籍中蘊涵語言思想最豐富的一本著作,它全方位展示了孔子的語言觀念。在《論語》中,孔子由內容到形式、從認識到實踐對語言作了比較全面有見地的論述。
儒家繼承孔子衣缽的是孟子,而記載孟子言論的典籍中,孟子也通過對言與辯關系的理解,為自己的“好辯”辯解,揭示了語言的政治功能,他表明自己論辯的心跡:“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波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3]另一方面,孟子也闡釋了言與氣的關系,提出從論辯者的言語行為態度,可以看出一個人品格的高下,言語與一個人的人格修養、精神氣質有著密切的關系。此外,孟子分析了言與意的關系,提出了怎么解讀文本,以及怎么求得語言的意義的途徑,孟子的這些認識對于后來的文學批評,對于中國人的語言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發展到戰國時期,被荀子發揚光大。關于語言方面的認識,荀子認為語言本質上是約定俗成的,且是發展著的,具有時代繼承性。他認為“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重視語言的規范功能,強調語言在治理國家中的教化作用。荀子和孔子一樣,對語言的規范化給予了足夠的重視,提倡用雅言。
語言倫理學是一門以語言學和倫理學為基礎的交叉學科,脫胎于語言學和倫理學,因此先秦典籍語言倫理扎根于先秦典籍語言觀和倫理觀中,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2 先秦儒家語言倫理觀念
言語道德作為語言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公眾在言語交際領域中共同約定的,關于言語道德原則和規范以及言語道德素養、言語道德行為和言語道德評價的特定價值體系。言語道德的核心是言語道德原則和言語道德規范,另外,還包括言語道德評價、言語道德修養、言語道德教育、言語道德最高境界等。
2.1 言語道德原則
2.1.1 言要利國 先秦時期,就有了“國”的觀念,當時的“國”指的是諸侯國,我國自古就有愛國的傳統,諸侯國的國民已經把自己所處“國家”的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而這樣的想法表現在言語道德上就有了一言以“興邦”、“喪邦”的言論。在《論語·子路》篇中有一個孔子與魯定公的討論。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一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2]在這里,孔子對魯定公的問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指出“言以立國”、“言以喪邦”并非是夸大其詞,同時,孔子還勸說定公要施行“仁政”、“禮治”,不能因為自己說話沒人敢違抗就沾沾自喜,作為統治者,一語不當就可能導致國家淪喪。可見,言要利國并不是隨口一說,而是要落實到行動中去。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4]輕薄的樂曲擾亂了宮廷雅樂,誠然令人憎惡,然而更令人憎恨的則是導致喪家亡國的亂言。把語言運用同國家存亡之命運聯系在一起,這是《論語》對言語道德巨大社會作用的深刻理解,主張言語涉及國家的利益時,要謹慎,不能以一己之言而危及國家,而要使一己之言有利于國家,當君主的更應該“慎于言而敏于行”,以“國家”的利益為重,言語要利于國。
2.1.2 語言運用需要利己不損人 “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這是單襄公說的一句話,指出了言談反復和胡亂納言對自己、對國家的危害,稍有疏忽就會使自己和國家遭殃,所以要慎言慎行。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單襄公指出,君子不吹噓自我并不是因為謙讓的美德,而是因為厭惡這種凌駕于他人之上的行為。自我吹噓就會使自己的言行凌駕于他人之上,為君子所不齒,所以言語不能損人。又說:“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指出言語冒犯、談吐繞彎子、自我吹噓都不是君子所為,又提出毫無顧忌地談論別人是引來禍患的根源。前事之鑒,后事之師,因此言談舉止要以利己不損人為要義,才會有另外一番境地。
2.2 言語道德規范
2.2.1 語言運用要合乎仁、禮 “仁”、“禮”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價值理念,也是其語言倫理思想的精華,正如錢穆先生所講,“仁之于禮,一內一外,若相反而相成也”,在先秦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所謂“仁”,就是“愛人”。判斷“仁”的實踐標準就是“忠恕”。“仁”要貫穿于人的言語道德行為的各個方面,一如《荀子·非相》所說:“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5]荀子認為,君子言語行為的內容應該體現“仁”,言語行為的質量應以“仁”為標準進行道德評價。總而言之,言語行為應該合乎“仁”,這是當時的一項言語道德準則。
言語倫理行為中“仁”的具體表現是“慎言”,這可以說是對“言仁”道德規范的一個簡單的總結[6]。《論語·學而》“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論語·里仁》“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等都體現了言要合“仁”的思想,提醒我們說話要謹慎,三思而行,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語言運用的道德價值的深刻思考。而“慎言”就意味著在我們運用語言與人交流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必要的價值判斷,并考量我們的言語行為與其他社會行為之間是否統一,語言運用是否合乎道理。由此可見,所謂“慎言”不僅是當時言語行為的道德要求,也是當時人格道德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時人道德理想在語言運用方面的反映。因此,要做一個“君子”,就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意即“先把要說的話實行了,再說出來,這就夠說是一個君子了”。
錢穆先生曾說:“仁之于禮,一內一外,若相反而相成也。”強調“禮”與“仁”在儒家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孔子認為人們通過語言與人交流時應“約之以禮”。“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是孔子在強調“仁”重在約束自己的言語行為并使之符合“禮”的規范,“仁”是為“禮”服務的。因此孔子強調人們的一言一行莫不遵守“禮”的最高規范,如果沒有遵循“禮”的約束,就會“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思,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綜上所述,我們由儒家語言倫理思想可以得出,言語行為要合乎“仁”、“禮”,才能產生和諧的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只有合乎“仁”、“禮”,才符合社會倫理道德的“中庸之道”。
2.2.2 言忠信,行篤敬 “忠”“信”在先秦時期也是漢民族的言語道德規范之一。《周易》載:“君子近德修業。忠信,所以近德也。”這句話指出了“忠信”與“德”的關系,其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大到一國之君,小到平民百姓,忠信都是至關重要的品格,“信”尤其與人的言語行為有關,重信守諾,說到做到,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基石[7]。“信”落實到言語道德行為中,即是一種言語道德規范,這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言語行為需忠于客觀事實。孟子曾說:“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他闡述了語言運用不遵循客觀事實的后果,指出“言無實”是不好的,我們應該“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廣泛地學習、詳盡地解說客觀事實,才有機會化繁為簡,達到想要的效果。《戰國策》中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那么,什么才是“不智”,“不忠”呢?對不明白的事情卻要發議論,那是“不智”;對明白的事情卻不講,那是“不忠”。“做人臣的不忠應當處死,說話不詳實也應當死”。可見言語“不忠”之危害性,殃及自身性命,言語一定要得當,要忠實。第二,言必及義,言必有中。“言必及義”是孔子教導徒弟的一個重要課程。“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他認為人們說話要合情合理,如果一個人連起碼的道德規范都不能夠實施,那么,這個人將會很難教導。孔子的學生司馬牛就曾因“多言而躁”受到孔子的嚴厲批評。而另一個學生閔子騫在魯國翻修金庫時建議不必翻修而受到了孔子“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夸獎。顯然,孔子將“言必及義,言必有中”,當做儒家語言倫理當中一項重要的準則來要求弟子。
3 先秦儒家語言倫理思想的意義
3.1 奠定了后世言語道德規范的基礎
先秦時期的語言倫理思想,不僅是當時語言運用的參照系,同時也是后世語言倫理思想發展的基礎。先秦時期是我國歷史文化形成與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所奠定的文化基礎,鑄就了中華民族數千年輝煌文明的根基。這一時期所形成的語言倫理規范,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它構成了我國現代言語道德規范的雛形,對后世中華民族語言倫理的發展和完善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們中國現在的言語道德體系中,仍然可以看到當時人關于“言禮”、“言仁”、“言忠”、“言信”的印記,盡管現代人的言語道德體系中“禮”、“仁”、“忠”、“信”的具體內涵有所不同,但所涵蓋的道德層面卻沒有很大的變化。“禮”、“仁”、“忠”、“信”的價值觀依然是人們倡導并要求恪守的言語道德信條。
3.2 對現實的語言交際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先秦時期儒家關于言語行為的道德準則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古人主張言語行為要遵守“禮”、“仁”、“忠”、“信”的原則,盡管古人所主張的“禮”、“仁”、“忠”、“信”的內涵與今人不盡相同,但仍然有一部分有極大的共通性,值得我們借鑒。我們知道,凡規范的東西,它的形成與傳播都需要有語言參與其中。而我們的行為是否符合規范,就會先從語言中反映出來[8]。“言為心聲”、“文以載道”,因此,要衡量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人們的語言習慣及其運用規范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參考標準。
儒家思想中很多言辭諸如“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言必行,行必果”“言而有信”“言必有中”等已經成為至理名言規范我們的行為,所以,先秦儒家的語言倫理思想對我們今天規范語言行為、構建和諧社會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