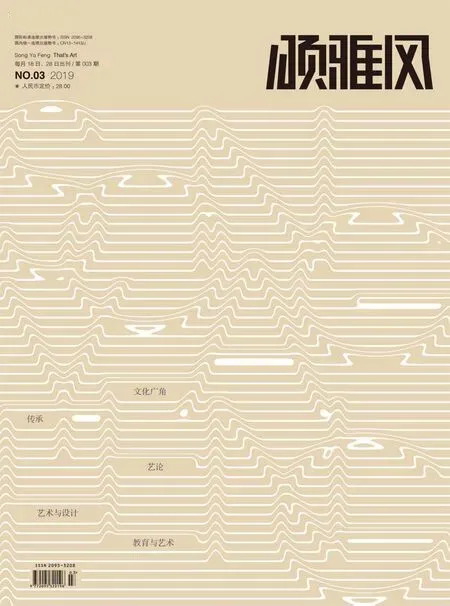從《論語》中的詩教看孔門幾點道德追求
◎陳德林 王甜甜
《論語》是一部不能逾越的中華文化經典,書中的道德認知和追求已浸透到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文化、民間習俗、行為方式和心理習慣里去。《詩》在《論語》中地位非同一般,《論語》一書涉及孔子引《詩》論詩,行詩教者多達十六條,引用之多是其他典籍難以企及的。孔子行教化時,《詩》是重要抓手。《論語》中的詩教承載了孔子的精神理想,管中窺豹可借詩教一窺孔門精神。
《左傳》有曰,“《詩》《書》,義之府也”。《詩》是道義的寶庫,《詩》文字背后的道德判斷的標準在孔子這里受到發揚和重視。在孔門精神中體現為本質上的道義論,追求君子心中之道德,亦或曰“仁”。孔子之后,詩教功用擴大化,由較為單純的政治詞令轉向修身養性,并且趨勢不斷加深。
《論語·述而》中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形而上者謂之道,立志當高遠。德者,人世之道。在天曰道,在人曰德,據于德,即合天道成人德。這種道德追求在《周易》思想中已經非常明顯,而孔子最尊崇周文化,認為其郁郁乎文哉,這種文的內涵下美的是其中的道德追求。善易者不卜,君子問禍不問福,都是因為心中堅持這種道德追求或原則,不因個人利益而進行功利計較。這種道德追求是對于道德本質的拷問,直指于人心深處。孔門稱這種道德為“仁”,盡善盡美的一種道德。而游于藝是依于仁的外在表現,一種形式,同時也是可以借助來走進仁這一道德的通道。
具體而言,詩教中體現的孔門精神有具體以下幾種。
一、雅正中庸,溫良敦厚
這是詩教的標準,也是孔門精神的標準配置。刪詩說中,孔子“放鄭聲,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過度、無節制的事物,違反了孔門對于雅正的追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南宋朱熹《論語集注》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楊伯峻則認為這是評價《詩經》“思想純正”。就思想觀念而論,孔子認為《詩經》是純正的、中和的。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中庸平淡寓于生活中主要體現為溫良敦厚,在文藝追求上體現為追求中和美。《八佾篇》中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記·經解》亦有,“溫柔敦厚,《詩》教也。”《關雎》中的發乎情,止乎禮,樂與哀都把握尺度,就是孔門精神追求。
二、繪事后素,文質彬彬
《論語·八佾》中“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有了白色的底子,然后繪出美麗的畫。在儒家精神中,盡美在盡善盡誠之后,這種更高的境界追求是起源于原始的好底子。
君子,是從質樸開始的。從某些方面看,文和質可以是形式和內容的類比。形式背后的內容,詩教是傳承精神的抓手,但是以精神內涵為第一要義,如同質樸的內涵一樣,不能越過精神而只談論形式。這種類比,在禮儀和學習中均有體現。在禮儀的追求中已有類似的描述,孔子重視喪禮,但認為可以節儉而不可以不發自內心悲痛。《論語·學而》中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對于學習亦是追求樸素為先、行動為先,在有了這種質樸的底子之后,在追求文,達到文質彬彬。子路質樸而少文,夫子對他的愛和批評都是源于此,愛他質樸的精神。
先道而后文,后世文以貫道、文以載道,都是先有好的底子,再進行文采的追求。這種繪事后素,文質彬彬的精神是孔子文化中很有特色也很重要的一部分。
三、潔凈精微,精益求精
質樸為美的基礎上,孔子非常關注文采,文質彬彬,不斷精進以盡善盡美。子路為孔子所批評的,多半都源于子路質樸而偏野,精進處不足。詩為雅言,是貴族交際用語,必然是要求非常精致的。《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不學詩,如同面墻而立,一無所見。“不學詩,無以言”,《詩》不只是交際詞令,更是一種貴族最求精致的精神態度,不夠雅不夠精致的語言是貴族交際中所鄙夷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亦是如此。
《論語·學而》,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切磋琢磨,就是不斷精進,精益求精的過程,懂得這些可以學《詩》,《詩》教便是不斷打磨使自己更追求精微的一種教育,這是孔門精神的更高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