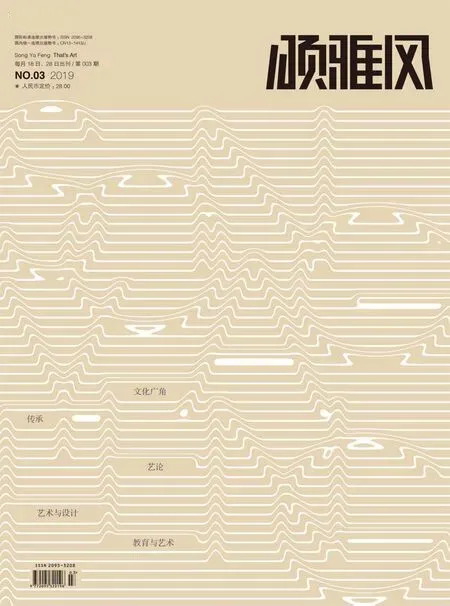淺談陳子昂詩學理論對唐代詩歌發展的影響
◎張津玲
一、陳子昂詩學理論簡述
在初盛唐的文學革命中,陳子昂身擔重任。其早年勇于創新、廣泛交友的俠士心態與所學的儒釋道等多種思想相互交織融合,使詩歌呈現出英豪雄秀之風與超群拔俗之骨。
陳子昂從審美角度出發,對晉宋以來彩麗競繁、逶迤頹靡的柔弱詩風進行批判,并主張恢復有金石聲、音情頓挫的漢魏古音,以建安風骨來取代初唐時期盛行的六朝脂粉與江左玄風,要求以風雅之作、正始之音、漢魏之篇作為學詩的主要內容,以“興寄”來要求用詩歌來反映現實社會,通過寓意于物來抒發情感與理想。如此一來,感懷遙深的風雅興寄與豪邁雄健的建安風骨實現了水乳交融,為唐代詩歌的發展建立起了理想范式。
陳子昂現存詩共有127 首,可劃分為三類:感遇詩、近體詩和同暉上人諸作,其詩氣格高峻、風骨盎然,展現了漢魏時期質樸、雄勁的詩風,善用比興而情緒豐富,語言質樸但寄意深遠,深刻地踐行了“興寄”“風骨”的理論美學。陳子昂的詩學理論一掃六代的纖弱詩風,首倡高雅沖淡之音,在復古的基礎上實現了詩學的創新,對唐代詩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陳子昂詩學理論對唐代詩歌發展產生的影響
(一)李白詩中的“風骨”
詩仙李白較為全面地繼承了陳子昂的詩學理論,并在詩歌創作中踐行滲透,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力,使其成為了盛唐時期的一種審美思潮。朱熹曾提出,李白的五十篇《古風》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陳子昂的《感遇》詩而作,并且“間多有全用他句處”,李白對于陳子昂詩學理論的繼承可見一斑。以李白在《古風五十九首》為例,對于大雅不作、詩道式微的現狀表示了沉重的哀嘆,又以“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表示了對建安風骨的認同和對六朝綺麗風氣的堅決反對,整篇詩表明了風雅比興與建安風骨的是詩歌革新所必經的“古道”,這一思想與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的主張一脈相承。同時李白還極力倡導將“風骨”作為詩歌創作的追求,呈現出剛健豪邁的氣勢,通過“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一句,可以看出李白將建安風骨作為評價詩作的一個重要的審美標準。李白在繼承了陳子昂詩學理論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理解與感悟,形成了豪放俊逸的詩風,成為詩壇中最為璀璨的一顆明星。
(二)杜甫詩中的“興寄”
杜甫對于陳子昂“風骨”和“興寄”進行了結合論述,但在理論成就的發展上較為側重于后者。杜甫從諷喻的角度繼承和發展了“興寄”的詩學理論,并將其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學思想融合了起來。在安史之亂后,杜甫的詩歌創作出現了較為重大的轉折,表現出了關注民生、陳述事實的特點,這也是杜詩被成為“詩史”的原因。杜甫在強調“興寄”中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還強調了主體情感的表達,杜甫在詩歌創作中注重個人情感與現實事物之間的復雜情感交織,將內心情感通過外在景物表現出來,這與其詩作“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聯系。《白雨齋詞話》詳細地指出了“興寄”與杜甫“沉郁頓挫”詩風之間的聯系,認為詩歌創作過程中,只有用曲折深婉的興寄手法,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復雜、深刻的情感。杜甫在詩中對于不便明言的地方,以寄托的手法處理,以形成“沉郁”的詩風。
(三)白居易詩中的“比興”
隨著時代的發展,詩論家們逐漸以“比興”的說法來代替“興寄”。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此處提到的“比興”與“興寄”在意義上是一樣的。白居易首次將“風雅比興”作為詩歌創作的本質,認為失去這一特點的詩歌只能是“空文”。因此,白居易對于包括李白、杜甫在內的諸多詩人都提出了一定的批判。白居易對于齊梁間詩風持否定態度,這一點與陳子昂的態度是相同的。
結語
文學的發展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詩歌的變革也不會一蹴而就。在初唐時期,六朝以來的詩風盛行已久,因此陳子昂的詩學理論也有一定的不足,但與他對于唐代詩歌發展做出的貢獻相比瑕不掩瑜。陳子昂的詩學理論影響了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著名詩人,為唐代詩歌指明了發展的方向,在我國詩學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