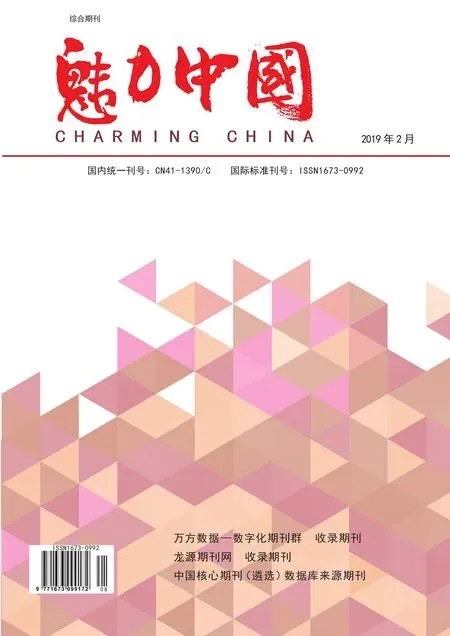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蹈創(chuàng)作思考
——《身份、模態(tài)與話語——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反思》書評
李琛
(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舞蹈學(xué)院,廣西 南寧 530022)
《身份、模態(tài)與話語——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反思》這本書闡述了當(dāng)下中國民間舞的景觀,界定了“民間藝人”、“二老藝人”、“職業(yè)舞者”的身份群體的劃分,闡述了職業(yè)民間舞群體舞臺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素材“被內(nèi)容”、內(nèi)容“被素材”的現(xiàn)狀,并從敘事學(xué)的意義上將中國職業(yè)民間舞語篇進(jìn)行了分類,追求更好地把握民間舞蹈的主體及其關(guān)系。就如書的副標(biāo)題“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的反思”一樣,作者并沒有在民間舞蹈的發(fā)展上直接的給出建議,而是給了很多不同的方向,從中給予編創(chuàng)者們不同角度的思考。
“人之所以不同于動物,在于能表達(dá)自己。”豐富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形成了多彩的民間舞蹈藝術(shù),不同身份群體的人也有著與他人不同角度與多元的表達(dá)方式。在學(xué)習(xí)民間舞蹈的編創(chuàng)中,筆者常有一些疑問,在尊重民族信仰文化的基礎(chǔ)上,如何與現(xiàn)代審美相融合?在民間舞蹈舞臺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路上,我們?nèi)绾谓缍▌?chuàng)作民間舞蹈作品的類別?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下,追求什么樣的民間舞蹈創(chuàng)作?
在書中第四篇章中作者將職業(yè)民間舞舞語篇大致分為宏大敘事、私人敘事、訴說鄉(xiāng)土、戲說鄉(xiāng)土,從敘事學(xué)的意義上將現(xiàn)下民間舞蹈作品類別清晰地劃分開來。對于編創(chuàng)者來說能根據(jù)這樣的劃分能擴(kuò)展在創(chuàng)作中選材的思路,更清晰地表達(dá)創(chuàng)作作品。近年來,國家大力支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發(fā)展,職業(yè)民間舞蹈群體也越來越關(guān)注非遺舞蹈,以“尋根、回歸、傳承”為文化導(dǎo)向形成了一系列的“非遺舞蹈進(jìn)校園”、“沉香”、“大美不言”等活動,《尼西情舞》《彝族打歌》等便是這些活動的產(chǎn)物。這一類作品隸屬于“述說鄉(xiāng)土”中對民間舞蹈的加工,是以中國56個民族舞蹈的風(fēng)格性來言說的。在11月份北京舞蹈學(xué)院舉辦的《中國首屆舞蹈創(chuàng)作講壇》中就提到,在80年代的民間舞作品編創(chuàng)中這樣表現(xiàn)民族風(fēng)格作品有很多并且成為經(jīng)典,為什么到現(xiàn)今編創(chuàng)民間舞蹈仍然還是一樣的,民間舞蹈的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新在何處呢?在田野中所看到的東西前人早已看過,若是大家都是把所見的民間傳統(tǒng)舞蹈搬上舞臺,那前人所做的舞臺作品的區(qū)別在哪里?與他人的創(chuàng)作豈不是大同小異,那是否在此時個人的表達(dá)尤為重要。但當(dāng)民間素材被“內(nèi)容”時,又是否會缺少了鄉(xiāng)土氣息?
作者在談到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的困境和發(fā)展方向時,也提到以上問題,提出在社會轉(zhuǎn)型的當(dāng)口創(chuàng)作者們就應(yīng)該重返民間,因為在起步之時當(dāng)代民間舞的建設(shè)就處在這樣矛盾的“圍城”之中,編創(chuàng)中也缺乏了“把閱讀置于寫作之上”的尊敬和積累,所以此時我們需要重訪民間,也是羅爾斯說說的反思的均衡。老子所謂的“道出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歸一。其實就能解答編創(chuàng)者的問題,鄉(xiāng)土語境中的民間舞便是這其中的“一”,再由此衍生出多元化的民間舞蹈作品。再看中國舞蹈家協(xié)會這兩年所舉辦的《天域舞風(fēng)》、《藍(lán)藍(lán)的天空》兩場原創(chuàng)西藏、內(nèi)蒙古題材舞蹈作品專題晚會獲得成功,組織國內(nèi)優(yōu)秀編導(dǎo)深入到民族生活中,其中創(chuàng)作了一些緊跟時代、貼近生活又打動人心的民間舞蹈舞臺藝術(shù)作品,例如《國家的孩子》、《戰(zhàn)馬》、《轉(zhuǎn)山》、《玄音鼓舞》等。現(xiàn)今民間舞蹈創(chuàng)作多元化,某種語篇或許與“民間”有了一定的距離,但個人認(rèn)為所出現(xiàn)一切創(chuàng)作的展現(xiàn)必定有其存在的意義。同時在閱讀之中筆者也試圖劃分中探尋民間舞創(chuàng)作的方向。
一切事物都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可能響應(yīng)國家政治的要求、也可能跟隨社會的變遷需求,每個編創(chuàng)者的創(chuàng)作背景、初衷、目的等也不盡相同,因此也沒有比較之處,都在各自不同的語境中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從專業(yè)主流的角度上看,《印象》系列在民間舞中屬于遠(yuǎn)遠(yuǎn)外層的商業(yè)產(chǎn)物,雖打著民族文化的招牌,但其根本卻與民族文化相差甚遠(yuǎn),但在商業(yè)旅游中帶來了一定的經(jīng)濟(jì)效益。不過也因為其本身為脫離文化的產(chǎn)物,所以總會被社會所淘汰,《印象.劉三姐》從首演年賺億元到去年的破產(chǎn)倒閉就是社會進(jìn)展的過程,社會的快速進(jìn)展中,“掛羊皮賣狗肉”的地方逐漸減少,雖地方的文化旅游項目的建設(shè)可能仍然帶有一定的商業(yè)性質(zhì),但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也將越貼近民族文化其本身,民間舞創(chuàng)作中始終要把握住民族的根。
劉建老師和趙鐵春老師的《身份、模態(tài)與話語--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反思》這本書也試圖在思辨與具體事例中展開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的畫卷。最令人感嘆的是,作者靈活巧妙地將理論與實踐的例子相結(jié)合,在每一篇章每一小節(jié)都舉出大量的實例,包括舞蹈先驅(qū)的珍貴口述史、生平事跡介紹…例如說到二老藝人身份群體時講到張蔭松老師,再例如說職業(yè)民間舞者時提到很多田露老師、王枚老師、高鍍老師的創(chuàng)作思考,使整本書變得通俗易懂、有趣生動,便于深入學(xué)習(xí)思考、舉一反三。
或許對于創(chuàng)作者來說,在創(chuàng)作之中并不用去考慮創(chuàng)作的類別,學(xué)會運用不同現(xiàn)代的意識、現(xiàn)代的視角進(jìn)行創(chuàng)作,不管是宏大的還是私人的敘事,創(chuàng)作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要始終圍繞著這個“一”去發(fā)展,真誠地表達(dá)民間的話語,就能在在當(dāng)代的中國民間舞舞臺上增添一筆艷麗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