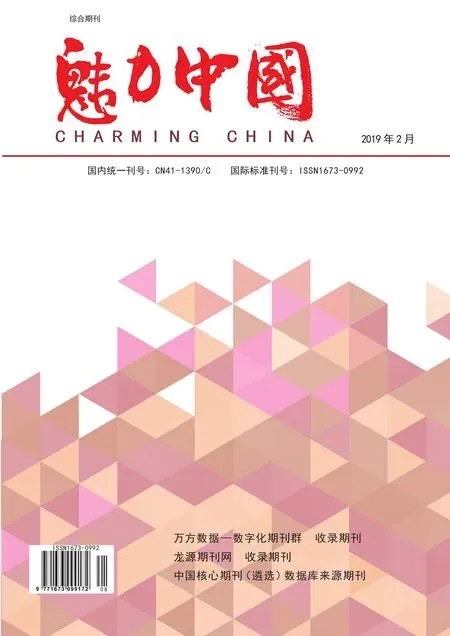漢語詞匯中的文化內涵
張凱潞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語言與文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語言是社會文化的符號載體,文化推動了語言產生和發展。漢語詞匯中包含著大量的文化內涵。漢語詞匯的構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復音詞。除了結構外,漢語詞匯化的語義中更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一些漢語詞匯也體現了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一、漢語詞匯構造中的文化因素
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決定了它不僅要反映人們的審美情趣,而且要受使用者審美觀念的制約和影響。古代漢語詞匯的特點是以單音詞為主,有一部分復音詞,復音詞處于凝固過程中。現代漢語則是以雙音節詞為主的。從古代到現代,詞匯的復音化是漢語發展的一個總體趨勢。漢語詞匯復音化(以雙音化為主)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相互制約,平衡的結果。其中漢民族文化心理的推動作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華夏民族自古以來就對成對成雙的現象具有強烈的崇尚和追求。例如,送禮要送雙,《儀禮·聘禮》:“凡獻,執一雙”,直到今天送雙不送單的觀念依然十分流行。這種觀念表現在語言上,就是講究成雙成對的語言片段和節奏。如在六朝極致繁榮的駢體文的一大特點就是辭藻華麗,極求對偶工整。除了成雙成對的追求之外,還有對立統一的樸素的辯證思想,老子《道德經》中:“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反映在語言中就是一些反義并列雙音詞的出現,如“消息”、“利害”、“取舍”、“優劣”、“舍得”等等。
等級觀念是儒家倫理的首要表征。儒家“三綱五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維護以君權、父權、夫權為核心的等級制度,而儒家用來維護社會秩序的“禮”強調的也是“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等級觀念。《論語·顏淵》中就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傳統社會中,等級觀念已經深入在社會人際交往和價值觀念當中,成為社會傳統心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詞語的形構中也影射著森嚴的封建等級觀念,如“君臣、主仆、官兵、男耕女織”等詞的構造就是以尊卑為序,“父子、兄弟、子孫、母慈兒孝”等詞是以長幼為序,而“主次、城鄉、妻妾、綱舉目張”等詞則是以主從為序。復合詞中語素的排列次序也深受傳統社會等級觀念的制約。
二、漢語詞義內容中的文化內涵
詞義是語言文化內蘊的顯著表征,申小龍先生曾說: “一種語言的詞義系統蘊涵著該民族對世界的系統認識和價值評定,蘊涵著該民族的全部文化和歷史。”
在漢語史上,一些常用詞的替換中也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內涵。以“橋”和“梁”為例,在古漢語中表“橋梁”這個概念的有“橋”和“梁”兩個詞,戰國以前用“梁”,戰國中后期始見“橋”,到了漢代,“橋”基本取代了“梁”,漢以后到現代,表達“橋梁”這一概念主要用單音詞“橋”和雙音詞“橋梁”。“橋”取代“梁”的過程中隱藏著當時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在甲骨文中還沒有“橋”、“梁”二字,因為遠古人類認知水平和生產力的落后,人們還不會架橋,通常是淺處踏水而過,深處繞道而行。后來,人們在水中壘石阻斷水流,創造出了“梁”,類似今天所說的水堤,人們可以從“梁”上渡水。《詩經·衛風·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傳》:“石絕水曰梁。”戰國時代社會急劇變動,南北接觸增多,要求有更多更好的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早期的“梁”多數只能修建在地勢平坦、河身不寬、水流平緩的地段,受形制的影響,“梁”下不便行船、不利漕運,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戰國初期,我國在冶煉技術方面發明了生鐵和冶煉鐵,出現了鐵器。鐵的出現和應用大大推進了建筑方面對石料的多方面的利用,為大量建造石橋提供了物質條件,也促進了施工技術的進步。因此以高和曲拱為特點的“橋”就出現了。(《說文解字》:“喬,高而曲也。”“橋”的語源是“喬”,說明了“橋”的特點是高大而且有拱形彎曲的結構。)到了漢代,這種技術逐漸成熟,于是“橋”基本取代了“梁”。
由“梁”到“橋”是中國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大飛躍,體現了古代社會科技水平的一大提高。隨著石梁橋和石拱橋的普遍應用,以平直為特點的梁逐漸退出生活舞臺,反映在語言的詞匯中,就是“橋”對“梁”的替代。
三、外來文化對漢語詞匯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外來文化對漢族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從先秦至清代各個時期,或多或少都摻雜著外族文化。在文化交流傳播的中間,漢語也受到了許多外來文化的影響,產生了很多新的詞匯,這些詞很多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基本詞匯。
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兼容并包,漢民族文化對于外來文化具有非常強大的改造能力。漢語中的外來詞的吸收也很能體現中國文化的這一特點,很多外來詞被漢化,逐漸取得了和漢語固有的詞語相同或相近的形式,使人們已經察覺不出是一個外來詞了。比如梵文的音譯詞“比丘尼”,指已經受足戒的女性。后來又簡稱“尼”,由于表意不明,所以人們又加上類名“姑”,成為“尼姑”,這個名稱一直用到了現在。還有“芝麻",原稱“胡麻”。沈括《夢溪筆談·藥議》:“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為直麻,無實為集麻,又日麻牡。張審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為大麻也。”后來種植既久,就去掉“胡”字,但要和中國本有的“麻”區別,因其有油,就改稱“脂麻”。后來俗稱“芝麻”。李時珍《本草綱目·谷一·胡麻):“巨勝、方莖、狗虱、油麻、脂麻,俗作芝麻,非。”
以上,我們簡單說明了一些漢語詞匯中的文化現象。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符號背后卻往往蘊藏著深刻的文化內涵。語言與文化互相佐證,探索漢語詞匯中的文化內涵,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刻的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