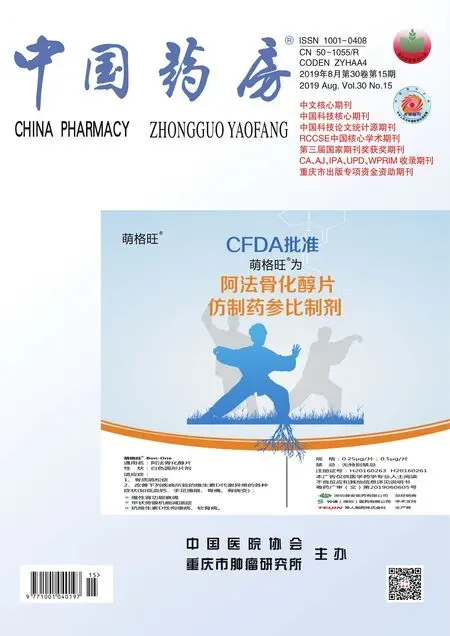《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中的中藥制劑質量標準的分析與探討Δ
劉瀟瀟,隆穎,戴忠,李華,馬雙成,羅卓雅#
(1.廣東省藥品檢驗所,廣州510633;2.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北京 100050)
醫療機構制劑(以下簡稱“醫院制劑”)是指醫療機構根據本單位臨床需要經批準而配制、自用的固定處方制劑[1],醫院制劑通過醫療機構的醫師對患者進行診斷后開具處方,由同一醫療機構的藥劑部門根據醫師處方將該制劑發放給患者,而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流通到醫療機構以外的地方銷售或使用[2]。醫院制劑是我國衛生產業的特色之一,是醫院藥學和藥學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藥品的一種特殊補充形式,長期以來,醫院制劑以其便捷、有效等特點在臨床診療服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在一些特殊疾病的治療上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特別是中藥醫院制劑,從中還誕生了目前醫藥市場的一些大品種,如復方丹參片、三九胃泰膠囊等[3-5]。
1985年,廣東省衛生廳組織出版了首版《廣東省醫院制劑規范》,該規范成為廣東省衛生行政部門、藥品檢驗所進行質量監督檢驗的依據。2010年,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啟動《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再版的編撰工作。《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目前出版了第一~五冊[6-10],共收載897個中藥制劑品種,按照“安全、科學、實用、規范”的指導原則對其質量標準進行了提高,進一步完善了有效性檢驗項目、安全性控制項目,采用了色譜分析、光譜分析等現代分析技術,與1985年版收載的以化學分析法為主的醫院制劑標準相比,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隨著我國中醫藥學事業的蓬勃發展,中藥制劑的質量控制水平快速提升,形成整體質量控制模式,進入儀器客觀檢驗的量化控制時代。與2010年版、2015年版《中國藥典》(一部)[11-12]的中成藥質量標準相比,《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的中藥制劑質量標準項目設置相對簡單、質量控制指標單一、有效性評價不足、安全性控制有待提高[13-16]。另一方面,醫院制劑是作為藥品市場的補充來定位的,在整個藥品銷售市場中占很低的份額。因此,其生產投入、檢驗設備、物流管理等都相對簡單粗糙[17-22]。基于此,如何在醫院制劑質量標準中平衡目前已高速發展的藥品質控手段和醫院制劑非標準化生產的現狀,成為醫院制劑質量標準提高的瓶頸。本文對《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的中藥制劑進行整理,分析其質量標準的現狀,探討中藥醫院制劑質量標準控制的關鍵點,為醫院制劑的質量標準提高提供建議,促進醫療機構為公眾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醫院制劑。
1 《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的歷史沿革
首版《廣東省醫院制劑規范》于1985年頒布,全冊收載了中藥、化學藥制劑共283種,通則、通用檢測方法及指導原則等附篇22類,作為全省各級醫療單位生產和控制制劑的質量標準使用了30余年。2010年,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委托廣東省藥品檢驗所對全省醫院制劑進行梳理,啟動《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再版的編撰工作。《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第一冊)于2014年12月頒布實施。在第一冊的基礎上,根據廣東省內醫療機構制劑質量標準提高工作的推進情況,分別于2015年9月、2015年12月、2016年10月、2017年5月頒布了第二冊、第三冊、第四冊和第五冊[6-10]。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共收載中藥制劑品種897個,劑型包括片劑、膠囊劑、顆粒劑、眼用制劑、鼻用制劑、丸劑、軟膏劑、乳膏劑、噴霧劑、散劑、糖漿劑、搽劑、涂劑、酊劑、耳用制劑、洗劑、合劑、酒劑、茶劑等。檢測方法包括顯微鑒別法、薄層色譜鑒別法、紫外-可見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譜法、氣相色譜法等。再版的《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與1985年版相比,除未收載安全風險大的中藥注射劑外,收載制劑類型更為全面、檢測方法更為先進、質量控制更為準確,能更有效地保證醫院制劑的安全和內在質量。
2 《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的中藥制劑質量標準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整體質量控制有待提高
整體質量控制是符合我國傳統中醫藥理論的質量評價方法,國家藥典委員會在2010年版、2015年版《中國藥典》中[11-12]均強調中藥整體質量控制的重要性,采用適當的藥物分析方法對制劑進行多組分的同時檢測,從而制訂合理的控制指標,以達到控制制劑內在質量的目的[23]。中藥醫院制劑多是老中醫多年臨床使用的經驗方,對其進行整體質量控制最能體現傳統中醫藥復雜體系的特點[24]。在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10]標準中,整體質量控制方法尚未應用其中,一般僅有1~3個薄層色譜鑒別。其中,收載藥味大于10味的大處方制劑有374個,占中藥制劑總品種數的42%。這些大處方制劑的質量標準中,僅有1~2個或不含薄層色譜鑒別的品種213個(一般標準中要求對1/3的藥味進行控制),約占大處方制劑的55%。近一半大處方制劑的質量標準難以保證制劑處方組成的真實、完整與有效性。
2.2 指標性成分的量化控制有待加強
單一的指標性成分含量高低并不能代表制劑的療效優劣,但是對制劑關鍵工藝參數的控制卻起著重要作用。從藥材、中間體到成品,指標性成分控制貫穿始終,對其進行監測從而對生產工藝的關鍵參數進行優化控制,制劑的有效、穩定得以保證。以指標性成分或活性成分為對照的含量測定在2015年版《中國藥典》(一部)[12]收載的中成藥標準中基本全覆蓋,使對中藥制劑的評價更客觀準確。縱觀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10],有浸出物或總固體測定的品種有90個,占總品種數的10%;而有含量測定項的品種僅有25個,僅占總品種數的3%。量化控制的不足難以保證醫院制劑處方藥材的質量和生產過程關鍵步驟控制,是醫院制劑標準可以著重加強的方面。
2.3 部分檢測項目可考慮專屬性更佳的方法
在《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10]的中藥制劑標準中,鑒別項多采用傳統經典的顯微鑒別法、薄層色譜鑒別法,但仍有28個品種使用了對大類化學成分進行鑒別的化學反應法。檢查項除了制劑通用檢查項目[25]外,特殊成分的安全性檢查多采用薄層色譜鑒別法。以處方中含有制川烏藥材的品種為例,2010年版、2015年版《中國藥典》(一部)[11-12]制川烏檢查項均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對雙酯型生物堿(烏頭堿、次烏頭堿和新烏頭堿總量)進行定量控制,在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10]的26個品種中,僅1個品種采用與2015年版《中國藥典》(四部)[25]一致的高效液相色譜法對以上3個成分的總量進行定量控制,4個品種采用薄層色譜法對以上3個成分分別進行定性控制,19個品種采用薄層色譜法僅對單一成分烏頭堿進行定性控制,2個品種未對毒性生物堿進行控制。含量測定項除了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仍有近一半的品種(11個)采用陰性干擾不易排除的滴定法、紫外光譜法進行檢測。檢測指標和檢測方法的不合理和不完善難以保證質量標準的可控性,從而影響制劑安全風險和內在質量。
2.4 制劑處方中易混用、誤用藥材的源頭控制有待加強
藥材的真偽優劣直接影響制劑的功效。目前藥材市場部分藥材品種混亂,非主觀和故意的摻偽使假均存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多年持續組織起草藥品補充檢驗方法以打擊以盈利為目的的故意摻偽使假行為。在2015年版《中國藥典》(一部)及第一增補本收載品種大黃[12]、血竭[26]的質量標準中,分別規定對土大黃苷和松香酸進行檢測,而阿膠、鹿角膠、龜甲膠、乳香、沒藥等均有其摻偽品的補充檢驗方法[27-28]。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10]收載含大黃藥材的制劑168個,僅1個品種有土大黃苷的薄層色譜檢查;收載含乳香、沒藥、血竭類藥材的制劑56個,僅1個品種有松香的化學反應檢查。建議從源頭加強對易混用、誤用、貴細藥材的真偽檢查控制,確保投料藥材的真實可靠。
2.5 制劑處方中非藥典收載藥材的控制有待加強
醫院制劑由固定醫療機構生產,使用當地習用藥材較多。在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10]的中藥制劑中,處方中有非藥典收載藥材的品種有222個,占中藥制劑總品種數的25%,其中多含有2~3個非藥典收載藥材,這些藥材有的收載在省級標準中,有些甚至無質量標準。由于這些藥材的對照物質無法獲得,因此,醫院制劑標準對這些藥材的控制尚處于空白狀態。
2.6 部分同方系列品種質量標準不統一
在全五冊《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6]中,有同方系列制劑品種6個,三芪丹丸(散)、三威跌打風濕霜(貼)、金翹熱毒清顆粒(有糖型、無糖型)、復方廣東土牛膝合劑(含片、顆粒)分別為同一醫院生產品種,大黃膠囊(散)、加味雙柏散(酊、消炎散)分別為不同醫院生產品種,其標準中質控項目相差較大。以單味藥制劑大黃膠囊(散)為例,兩者標準中均有大黃薄層鑒別,但大黃膠囊另有大黃素和大黃酚的含量測定項,而大黃散另有土大黃苷的檢查項。統一同方系列制劑標準,能有效提高該品種的質量。
3 中藥醫院制劑質量標準起草和提高的建議
質量標準是反映制劑質量特性的技術參數和指標,執行標準是控制醫院制劑質量的有效手段。質量標準的設置主要是為了控制影響制劑質量的關鍵生產參數,尋找生產參數(包括原、輔料與工藝參數)和制劑質量的關系,建立能控制關鍵生產參數的項目,以保證制劑質量的穩定可控。中藥醫院制劑的質量與投料原藥材、生產工藝密切相關,建議其質量標準可從【性狀】、【鑒別】、【檢查】、【特征圖譜】、【含量測定】等檢驗項目著眼入手,結合每個制劑的特異性,設置有針對性的項目。考慮到目前中藥醫院制劑標準存在的問題和醫院制劑的定位,建議其質量標準不能要求過高,兼顧先進性和適用性,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重點控制。
3.1 加強對中藥醫院制劑的整體質量控制
醫院制劑的定位是臨床藥品的補充,其生產投入、管理、檢驗等等方面都難以達到藥品生產企業的要求。因此,用上市藥品質量控制的標準來要求醫院制劑質量控制是不現實的。但醫院制劑畢竟是臨床用于治療的藥品,必須保證其有效、安全、質量可控。因此,建議醫院制劑標準采用整體質量控制思路,建立特征圖譜、指紋圖譜是有效的途徑。醫院制劑僅限于同一醫院藥房,來源單一,原料藥材的采集、過程工藝參數的控制相對固定,與由多個企業生產的藥品相比,是極大的優勢,建立特征圖譜、指紋圖譜相對容易。特征圖譜、指紋圖譜的建立,可解決目前醫院制劑質控指標單一的問題,也會縮短與藥品質量標準的差距,實現對原料藥材和生產過程關鍵工藝參數的雙重控制。
3.2 適當更新專屬性好、重現性強的檢測方法
檢測方法的更新換代與檢測儀器的高速發展密不可分,液質聯用、氣質聯用及核磁檢測已逐步被應用到中藥的質量控制中,但唯高靈敏度論的檢測方法不適宜用于所有場合或情況。專屬性強、準確度高的檢測方法與中藥特點結合才能達到精準質控的目的。對于中藥醫院制劑標準,經典的顯微鑒別法、薄層色譜鑒別法應繼續保留,建議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進行含量測定,已足以達到中藥醫院制劑量化控制的目的。采用昂貴的高靈敏度的液質、氣質法既增加醫院藥房的負擔,也增加標準執行的難度,且不是一定必要的。
3.3 加強對處方中地方藥材的質量控制
中藥醫院制劑多是地方醫院臨床長期使用的驗方,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因此,地方醫院制劑多收載地方習用藥材,比如現行《廣東省醫院制劑規范》收載制劑處方中有崗梅、五指毛桃、廣海桐皮、廣東土牛膝、溪黃草、雞骨香、火炭母、鳳尾草、千斤拔、毛冬青等,絕大部分收載于《廣東省地方藥材標準》中,但由于無法獲得這些地方藥材的對照藥材,因此,在制劑中對這些藥材基本沒有進行控制。建議加大這些地方藥材的化學成分研究,建立對照藥材或對照品,規范進行控制。
3.4 加強對處方中毒性藥材的質量控制
目前中藥中毒事件常有發生,對于含毒性藥材制劑,特別是治療一些慢性病需要長期使用的制劑,應建立毒性成分的控制項目。例如治療關節痛的龍鱉膠囊處方有10味藥,其中含毒性藥材6味(有毒:蘄蛇、土鱉蟲、全蝎、制川烏、蜈蚣;小毒:仙茅),按日劑量一日3次,一次4粒計,日服相當于有毒藥材6.4 g,而質量標準僅有烏頭堿類成分的薄層限量檢查。該制劑經過水提醇沉提取后,這些毒性成分的轉移率如何,建議建立指標性成分的含量測定對藥材毒性成分轉移率進行評價。有毒藥材的用量務必謹慎,過少或過量均不適宜,如玉龍散等8個制劑的處方中均含有生川烏、生馬錢子類藥材,烏頭堿、士的寧類成分是其物質基礎,但其質量標準中僅規定了烏頭堿、士的寧的上限,對其有效性控制不足,故建議毒性藥材指標性成分的限度宜制訂高低限的合理區間,以保證制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5 加強對生產工藝中關鍵參數的控制
生產工藝關鍵參數的穩定是保證制劑批間質量一致性的重要條件。根據制劑的不同工藝制法,在質量標準中應設置項目加以控制。首先,根據劑型的特點應設置相應的檢驗項目,2015年版《中國藥典》(四部)制劑通則[25]列出了各種劑型的一些通用檢查項目,應根據各品種的具體特點有所增減,設置具有品種特色的合理項目,比如原粉入藥的顆粒劑可不再進行溶化性檢查。其次,根據制法工藝設置合理的項目和限度。《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的中藥制劑多采用水提醇沉提取,其出膏率應重點控制,建議建立指標性成分的含量測定方法,通過轉移率設置合理限度,以控制制劑的出膏率。最后,對于同方系列品種制劑,建議按照高標準進行填平補齊,并根據各劑型制法的特點制訂限度,以對生產工藝關鍵點進行控制,保證系列品種的質量一致性。
4 結語
自《廣東省醫療機構制劑規范》再版以來,按照“安全、科學、實用、規范”的要求制定指導原則,收載897個中藥制劑品種,其質量標準進一步完善了有效性檢驗項目、安全性控制項目,采用了色譜分析、光譜分析等現代分析技術,并參照2015年版《中國藥典》標準格式書寫,與1985年版收載的以化學分析法為主的醫院制劑標準相比,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目前快速發展的中藥質量控制模式和方法相比,醫院制劑標準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本文為平衡好醫院制劑的定位和質量標準制修訂的思路,兼顧好先進性和適用性,建立切實可行的制劑標準規范提供了一些標準修訂的參考意見,從質量源于設計的標準控制角度進一步提高我國醫療機構制劑的質量,為公眾提供更加安全、有效、質量可控的制劑產品,并以期從質量穩定、療效可靠的制劑產品中開發出更多優質的上市藥品。